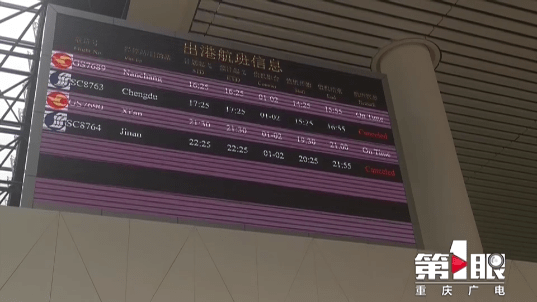冯春明
界湖不是湖,它是一个县城驻地的名字。我出生在这里,后来又工作生活在这里,对这里已经够熟悉的了。
然而, “界湖”这两个字于我而言,又是一个既熟悉又朦胧的存在。它如同时光隧道中的一束光,常常以一种神秘的象征型的寓意,把我拽进一个梦幻般的“湖泊”。以至于,让我在精神上跳出现有的框子,发现了许多本然的、永住的东西。
记得母亲告诉我,她生我的时候,正处在一个“大跃进”过后的饥荒年代。我生下来时只有五斤。当时,我们的家就在界湖西面的那条渠道边上的一个工厂的简易棚内。那是一处集小型水力发电和面粉加工为一体的工厂。它负责小城的电力供给和面粉供应。其时,工厂刚刚建立,职工住宿都成问题。
母亲时常提到界湖那条渠道里的鱼。那时,发电站水轮下面有很多鲶鱼,关闸放水后,一次能逮很多,都足够厂里吃好几天的。母亲说,那时我时常在床上做逮鱼的游戏,“从被窝里逮出鱼来,用手做锅,咕嘟嘟蒸熟,捧给母亲吃。”多少年来,那是母亲最喜欢提及的事。
后来,随着父亲的调动,我们全家离开了界湖。直到十几年后,我参加了工作,又来到了这里。不知为什么,多年以来,“界湖”这两个字,于我的脑海中常常充盈着湿润和波光的记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内心,往往被一些似有似无的事物所撼动。随之而来的,是一些莫名的惊奇感和神秘感……它们在这些过往的事物里,以某种意象的形式呈现于我的心灵。
我工作的第一站是公安系统。县公安局旧址就在界湖的那棵大银杏树下。银杏树的西南角,有一大汪。有天,一老公安神秘兮兮的告诉我说,古代,界湖曾经是一个很大的湖泊。那个有两个篮球场大小的大汪,很可能就是古界湖的遗迹。
老公安的这个说法,我信。界湖现在虽然没有湖泊,但不一定没有过。界湖在沂汶河之间,它依山傍水,位于平原。那些黑色的黏土,分明是冲积而成的。界湖的民谣里,就有“界湖街有两多,泥多、蚊子多”之说。尽管没有更多的史料佐证,但我还是相信老公安这个假设的。
自那以后,我喜欢悄悄地潜入那片心灵的水域,让自己的灵魂于幽静之处反观自照……一个“湖光秋月两相和”、“船动湖光滟滟秋”的界湖,时常在我的眼前闪现。
前些年,沂南曾经有过几次严重干旱,干旱之后,下过几场雨。界湖的雨下得很大,周围却很小。这是否是一种“湖泊效应”呢?当然,这种想法近乎荒唐,但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的思绪却无法跳出那一湾湿淋淋的存在。
后来,界湖村民施工时,从地下挖出了许多鹅卵石。那些鹅卵石,显然是由于水的冲刷而形成的。记得,前些年,在县城一家酒店,我与一位老先生聚餐时,曾涉及界湖的话题。先生是一位十分严谨的老中医。他告诉我说,鲁庄河曾于铜井镇大张庄那个地方改过道。他曾多次去大张庄公路桥下考察过,发现桥下河道两则的岩石上,有人工火烧开凿的痕迹。他说,那是古人在冬季通过火烧,利用温差破石开凿的一种方法。过去,鲁庄河是与界湖相连的,由于水的落差太大,时常造成灾害,因而改道,向东直奔沂河了。
后来,我也注意观察过鲁庄河至界湖一带的情况,却未能发现相关的痕迹。但是,界湖地下的鹅卵石与鲁庄河床的鹅卵石形状是一致的。鲁庄河落差很大,留不住沙子,整个河床布满了鹅卵石。从这个方面而言,鲁庄河与界湖的确是有关联性的。
“界湖”假如曾经存在,水的来源是个关键,后来,我又想到了界湖那条水渠,那应该是建国后人工开凿,水是从汶河引过来的。之前,汶河与界湖是否有水的通道,尚无定论。
但是,无论如何讲,界湖这个名字应当还是与湖泊有关联的。尽管我们也习惯地把大片平展的土地称为“湖地”,但“界湖”不同。看一下界湖附近村庄的名字,就可见一斑了。界湖西面的村庄是水浒套,东面是前湖埠、后湖埠,东南面是东平湖。“水浒”意为水边,“湖埠”的埠,意为停船的码头或靠近水的地方。这样,一个由“界湖”与“东平湖”串联在一起的湖泊轮廓,就清晰的显现出来了。
以上这些,也许仅是一种臆想,但自第一眼望见界湖的那个大汪,我就被一种充满湿润的苍凉打懵了,直至现在,我依然感到脚下有一股宛如洪荒初音的涌动。
“界湖”给予了我生命中最温馨且又最疼痛的记忆,自那时起,在人间所有的场地,大树之下,那一汪孤独深沉的“眼睛”,总在以一种勾魂摄魄的力量注视着我。那一湾潮湿,时远时近,时喜时悲,让我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