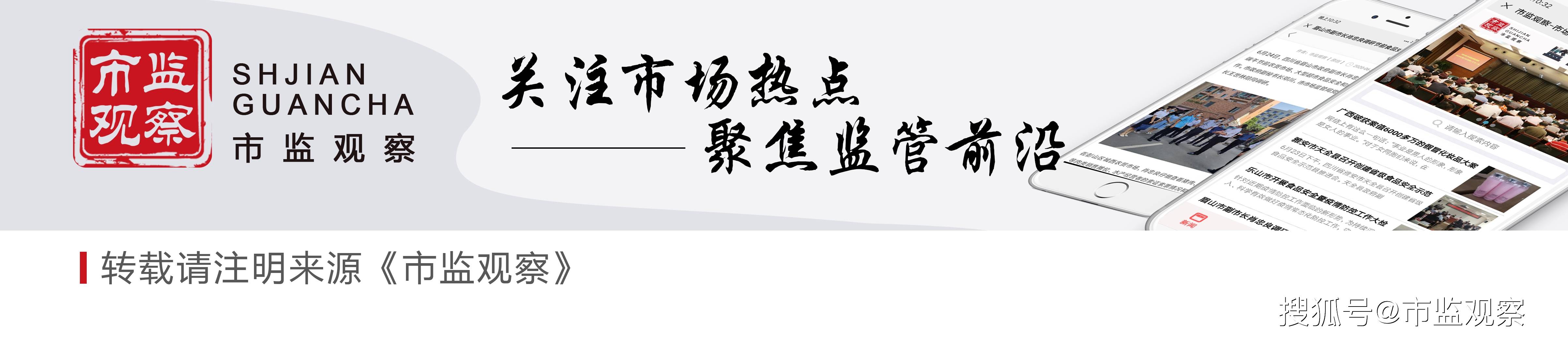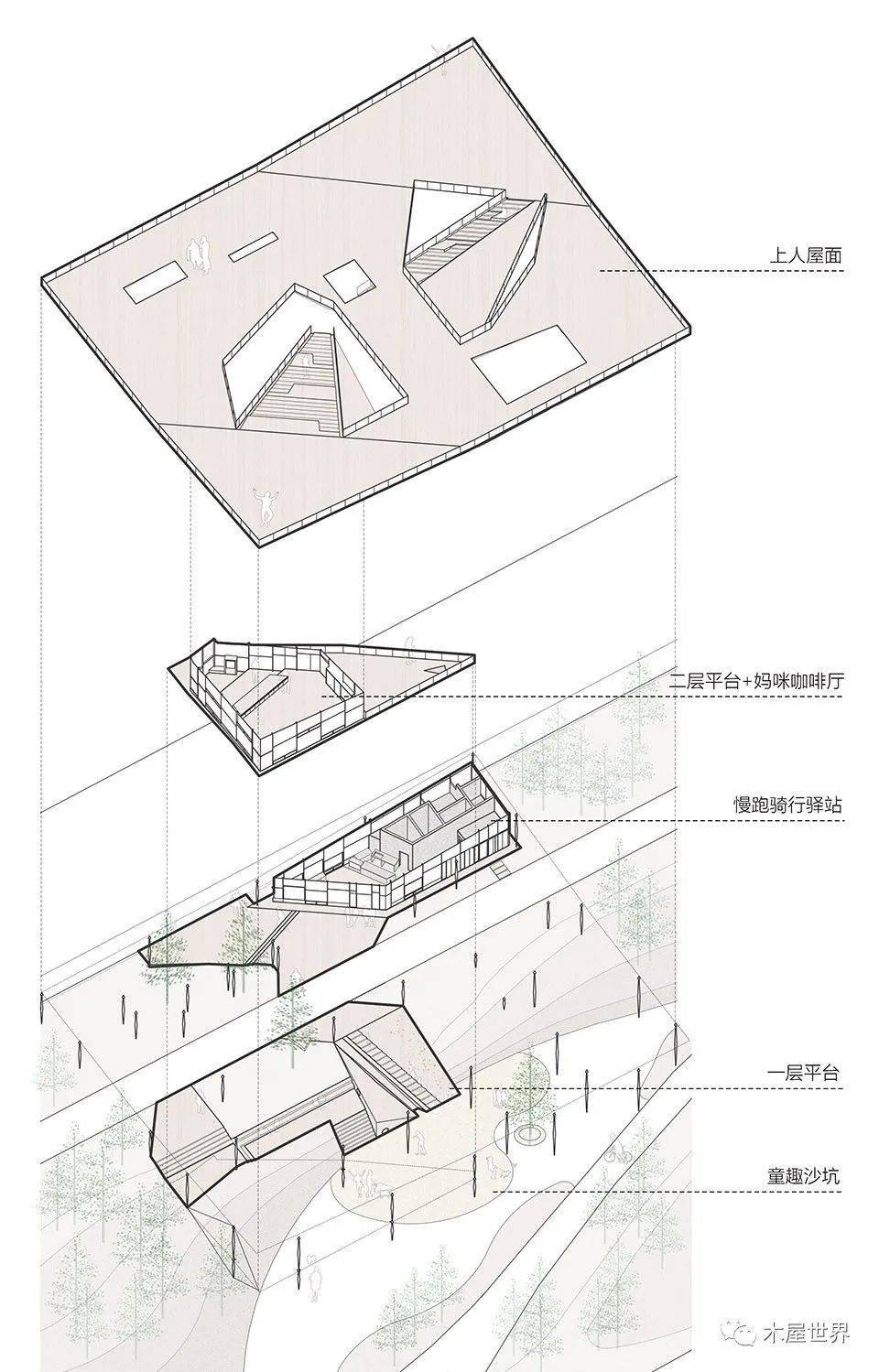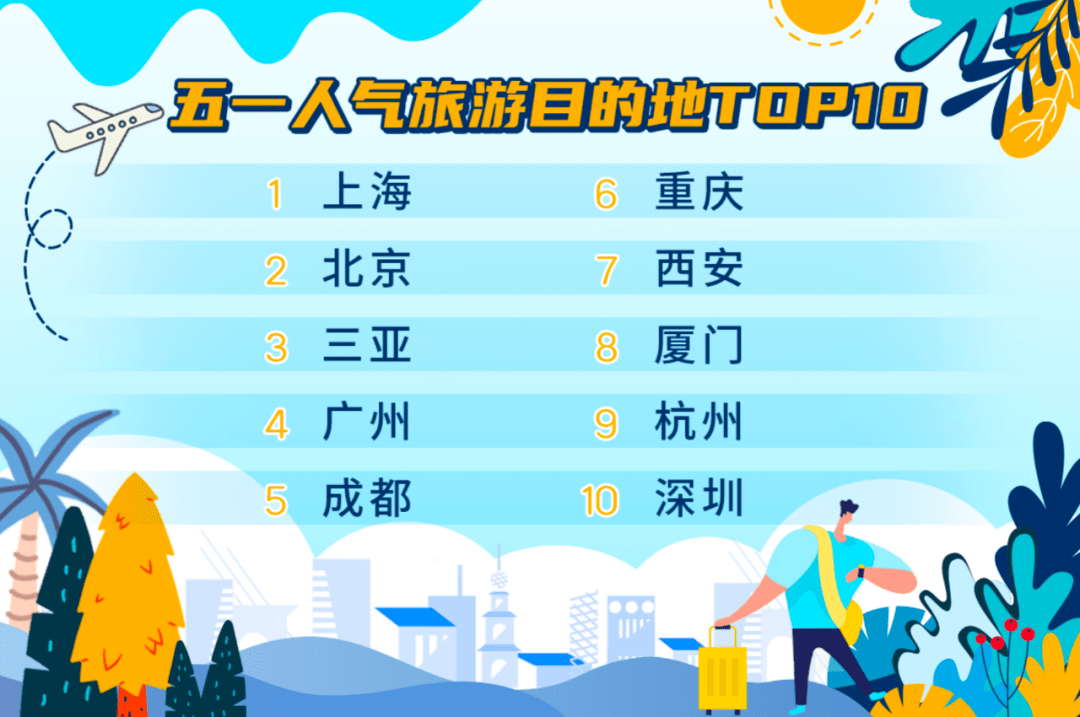冯春明
莒县,我更愿意把它称为莒地,因为无论它的方言,还是它的民风,以及它所依托的历史种种,都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这次来莒地,我与朋友在浮来山东门外的一个村庄做短暂停留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左转省道,而是右转乡道,沿着浮来山北段东面山坡下的一条勉强可以会开车的水泥路向北行驶。转弯时,手握方向盘的我,几乎是不加思索地打过方向来的,朋友说:“我觉得也该右转”。
浮来山北段不长。论山势,它与南段相比更显平缓。它整个的呈一种宽大但却不高的坐椅形状。车子转过几个不大的弯后,前方,路的右侧,紧靠道路有一小山包样的土丘,朋友说:“那可能是莒子墓。”车子靠近后,在土丘南坡有两块大理石碑出现在我们眼前,它们相隔不远,一东一西立在那里。待我们过去看时,果然是莒子墓!
石碑是山东省政府和日照市政府所立。两块刻有“莒子墓”的石碑尽管时间不长,但这足以让我相信眼前的这座土丘就是莒子墓了。莒子墓为层层夯土筑成,有三个层级,每个层级都很陡。我和朋友从南面上去时,相互搀扶了一下。
莒子墓的上方,不知是何原因,被人从中间挖了一道南北向的沟,沟的东边有一直径2米多的盗洞。尽管这样,站在墓顶时,依然能够感觉到墓的完整和宏大。尤其面向远方的平原、村庄和县城时,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然而,有所不同的是,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不是傲慢,亦非压抑,那是一种不分彼此的,亲和的,难分难舍的生命体验。尤其不远处那些活泼散步的鸭子;广阔田野里安静劳作的农人;成片成片白的红的花朵;远处鳞次栉比的楼群;天上缓缓运动着的云彩;它们共同搅起了阵阵反复盘旋着的暖风……那风让身后座椅样的山,让山包样的莒子墓,让墓周围所有的阳光和空气,在一种莫名的恻隐中,萌生出一种之于人间大爱的宽厚。
莒国有多个莒子,《汉书•地理志》记载说:莒传三十世,为楚所灭。可见莒子之多了。目前,谁也说不清这座山包样的坟墓里,到底葬的是哪个莒子了。 莒子国由西周所封,出至嬴姓。公元前11世纪,周起兵伐纣后,封兹舆期为莒国国君,这是周朝建立后,少有的几个非王室成员任国君的诸侯国之一。
莒国初立胶州一带,春秋时期,迁至莒县。其间,莒国的版图时大时小,但却持续绵延了600余年。莒国作为一个诸侯小国,在春秋诸国相互攻伐中,能够顽强生存下来,这与它的宽容和包容是分不开的。如齐桓公身为齐国公子时,与鲍叔牙到莒国避难留下的“勿忘在莒”的典故,就是重要的证据之一。
然而,历史的过往毕竟是模糊的,许多当时看似深刻的事情,早已无影无踪。只有静下心来,沿着它们曾经走过的路线,努力展开回忆的翅膀时,才有可能窥见它们的行踪。为了能够找到更多充分的感受,我与朋友驾车,沿着水泥路由南向北,然后向西,绕到浮来山的西北方。乡村道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沿途多有流水的河沟、汪塘和陡峭的土坎、石堰,以及盖着红瓦的村庄出现在眼前,我试图让自己的思路,沿着历史的和现实的路径,在同一土地上,让我的印象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双重关注。这时我的眼前一闪,那是一道被夕阳照射的,一条小溪的光泽,我因而想到了《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句,继而想到去年见到的,一位学者有关《诗经》中《车舝》《关雎》《蒹葭》及《鼓钟》与莒子和向姜爱情有关的论文。莒子和向姜的爱情故事是有据可考的,春秋《左传》记载:隐公二年(公元前721年)二年春,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论者认为:对比《左传》的记载和《诗经》的部分篇章,他发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认证关系。他认为:《车舝》《关雎》《蒹葭》是莒子因向姜所作;《鼓钟》系莒子逝后,向姜怀念莒子而作。
不过在我看来,论者尽管是在握有众多论据的基础上,对莒子和向姜与《诗经》的关系进行论证的,但论者的结论是否符合史实,还是有待于考古学地实证的。当然,这不妨碍我们对莒子和向姜爱情的猜想。人世间的生生死死,起起落落,与自然界的生发荣枯原本相通。虽然,过往的一切,在时光地磨擦下,已经飞灰湮灭,但成双的雎鸠还在;窈窕美丽的女子还在;爱情还在;思念还在;人间所有的酸甜苦辣咸都在。因为,这一切都贯穿于生命的整体之中,说不定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它会穿越历史的时空,突然向人扑来!
是的,人有时偶尔进入一个路口时,便有可能重遇曾经的自己,并于懵懂之中,捡回前世拥有过的简洁和清澈。莒地,我又来了。百年,千年,多少聚散,多少善恶……如今,能够在这个温润的初春,和着一缕清风遥看,内心几多感叹!
莒地属于古代“东夷”的范围,是“海上日出,曙光先照”的地方 。考古学家曾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四十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千万年来,这里的原始先民在海边狩猎、捕鱼,繁衍生息。漫长的史前阶段,莒地人靠着他们聪颖智慧的心灵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制造出了实用精美的石器、骨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烧出了薄如纸、黑如漆、面如镜的蛋壳陶;编织出了布纹细、密度高的纺织品;发明了冶铜术、原始历法和最古老的文字;兴起了家禽饲养和酿酒业……陵阳河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大口尊上刻的那些让人眼熟的花纹,第一眼看到它时,就有一种亲近感。以后,每一次走近它,它的上方那个貌似太阳的圆圈,中间那簇好似火苗的半圆,以及下边连绵如同峰峦的五个山尖,每每散发出一种鸿蒙之气。浮来山定林寺院内,那棵有着4000多年树龄的银杏树,至今依然根深叶茂。每一次走近它,我都能找到一种穿越感和一种伴随而来的非同寻常的感受。
莒地方言,是我所听到的方言当中最具亲和力的方言。学生时期,我在浮来山以西的沂南十二中读书时,第一次听到来自浮来山下同学的“莒县腔”。那声音不紧不慢,不慌不忙;那声音,语调温和而柔软;那声音,甚至让人在一段情景里不知转醒,直至随着岁月走远……
在方言的区域比较中,莒县方言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就我的感觉而言,莒县方言纯度很高,它的每一个发音里,都有着一种让人似曾相识地穿越千年的原始意味。或许正因为这些,我结交了许多莒地的朋友。在这些朋友当中,有许多画家和书法家,他们以及那些众多的真心喜好字画的普通百姓,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深刻。我想,这种健康的文化艺术氛围,绝非是一时兴起而形成的,它的内里一定有一种历史文化形成地深入到骨子里的传统架构。
莒地像一部厚厚的无法辨认它的年龄的书卷,那些隐藏在书页里的故事,沉静而安然。今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一直绕着莒地转,绕着莒子墓转。继而,绕着浮来山转,绕着写出旷世巨著《文心雕龙》的刘勰转,绕着那棵天下第一银杏树转……今天,浮来山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今天,有一朵祥瑞之云,自东向西而来……它一会浓郁似雾,一会散淡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