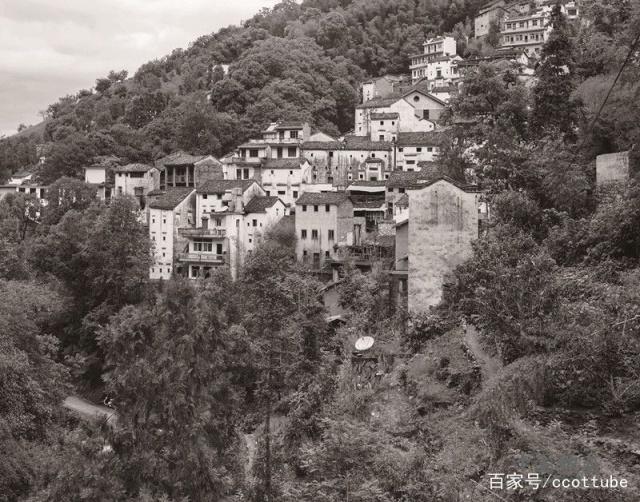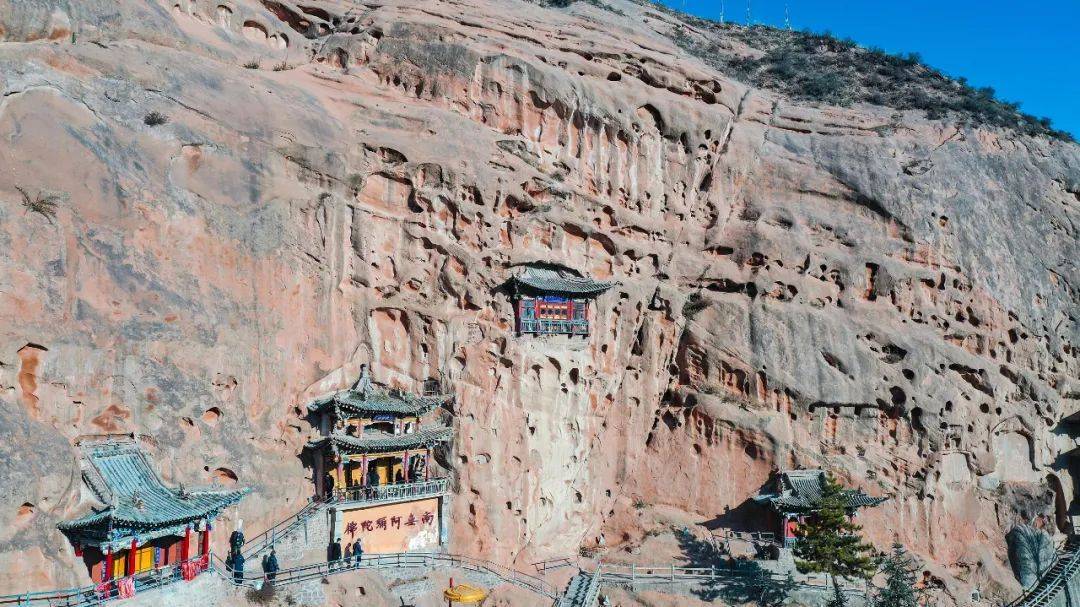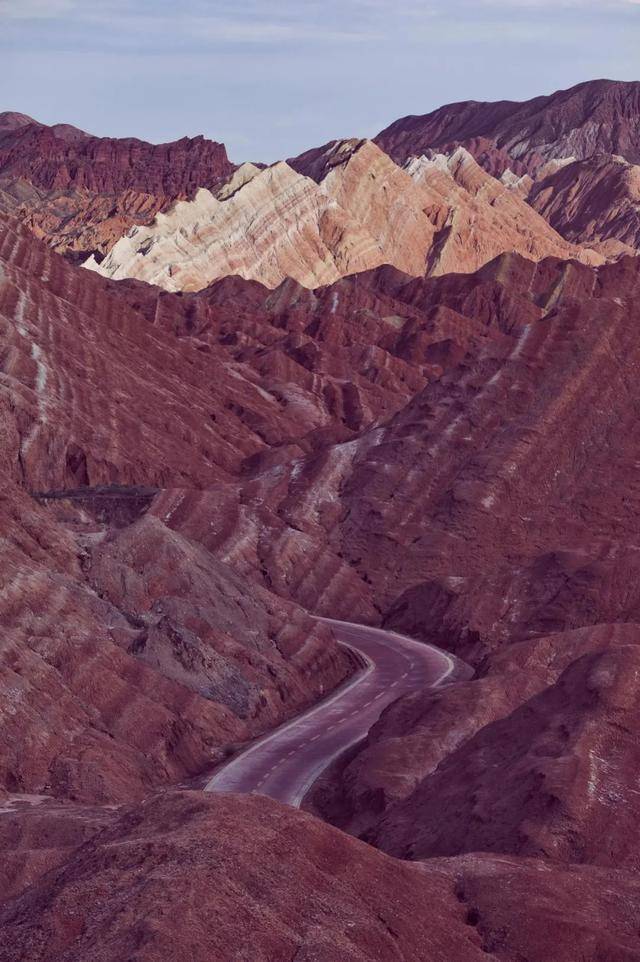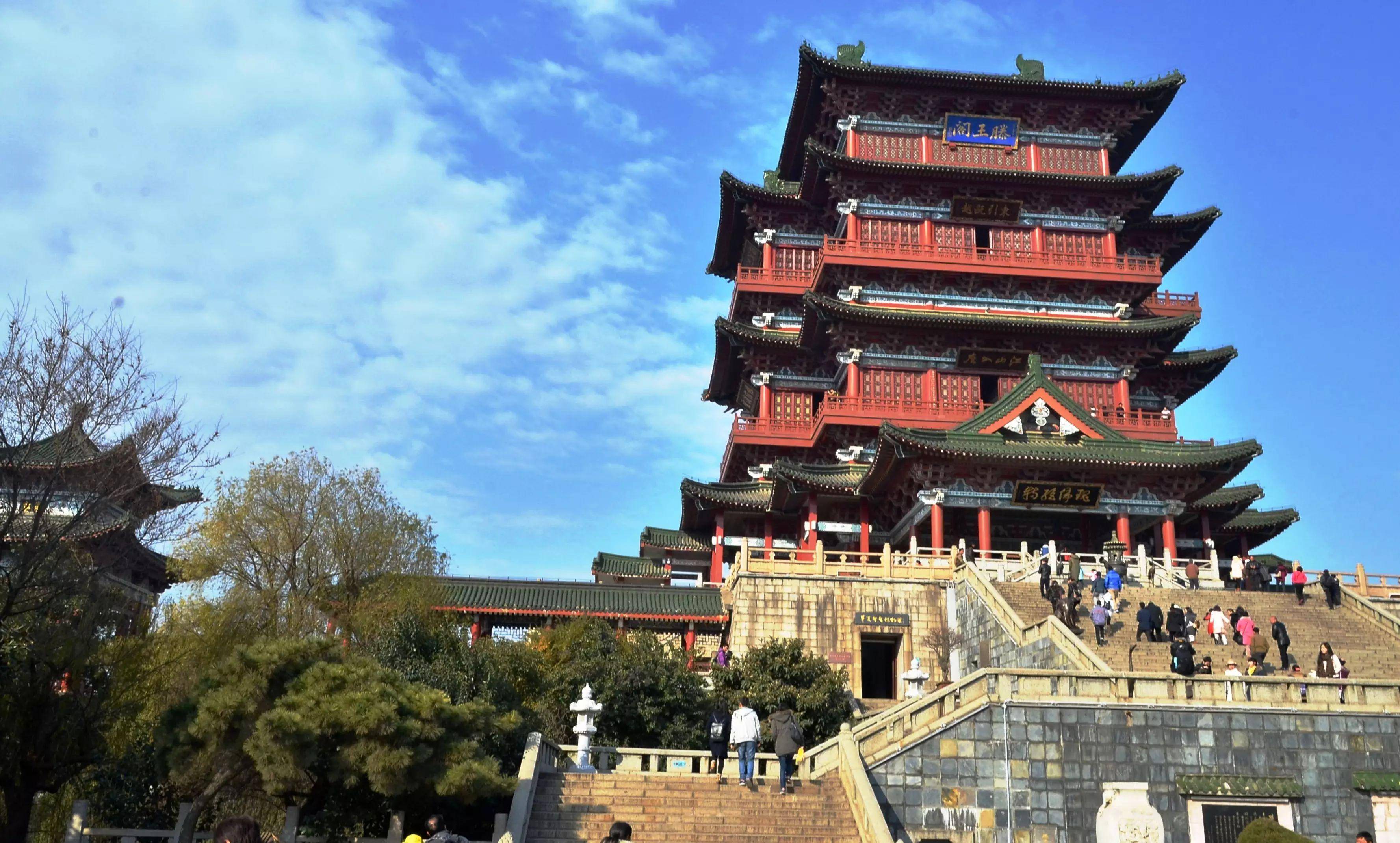从我居住的小区出来,右拐走百余米,沿着南沙河西行不多远,就能走到一条小巷的出入口处。
小巷为东西走向,长度似乎不足三百米,唯一的出入口在西端,与东岗路相接,可谓喧嚣城市中一条僻静又普通的巷子,却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书墨巷”。
以前我每天顺着南沙河河岸散步时,并不曾注意到这条小巷,至少没有往小巷里面走进去过。
为什么叫“书墨巷”呢?这样雅致的名字在太原的街巷中是极少见的,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是小巷紧挨着油墨厂的缘故吗?一定是的,而油墨又和书籍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给小巷命名的人自然就想到了“书墨”二字。
这是多么富有文化气息的名字啊,透着一种浓厚的书卷气,散发着一缕翰墨的芬芳。这样的名字,总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书籍,想到人生中那些不可或缺的精神伴侣。
一个人,如果每天都徜徉在书海中,抚卷、捧读、吟诵、涵咏,让心灵和神奇的汉字、优美的语言缠绵在一起,远离了世俗的纷扰,远离了人性的丑陋,远离了利益的争夺,那该是多么快乐、惬意、幸福的人生。
今天,当我再次走到这条小巷的出入口处时,望着那块写有小巷名称的路牌,心里隐隐有些受到触动的感觉。这个好听的巷名在我的心湖中荡起的涟漪,层层叠叠的,很长时间都不能消散,归于平静。
但是,转而又觉得这名字对我来说,似乎有一种宿命的味道:这充满书卷气的名字,莫不是在对我的身体现状进行一番无情的嘲讽吗?
眼下,读书对我来说已经是难以为继的事情了,尽管该做的手术都已经做过,但日益恶化的不可逆的眼疾,还是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我读书的权利。纵使我放弃一切,时时刻刻都愿意浸泡在书海中,也再不会有尽情畅游的可能了。而这,对于一个把书籍视作生命去热爱的人来说,又是多么的痛苦和无奈。即便是此时此刻正在写作的这篇文章,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太艰难、太吃力了。
现在,我不仅已经告别了站立三十七年的讲台,告别了曾经激情澎湃、幽默诙谐的讲课,而且渐渐告别了自己钟爱的一卷卷书籍。书柜里静静排列着的千余本书,仿佛变成了千余只眼,圆睁着,怒视着我,好像在斥责我为什么不去翻动它们,为什么不去捧读它们,为什么要无情地抛弃它们。
我无语凝噎。
曾经,我是那样激动地把这千余卷书一本一本地买回来,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书柜里,每天都去抚摸它们,亲近它们,阅读它们,是多么的快乐。可是,现在我却不能再把它们捧在手中畅快地阅读,无法去感受书中每一句话背后的思想和情感,又是多么的痛苦。我甚至觉得,一个人,不读书,毋宁死。
过去,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史铁生在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为什么总是要每天摇了轮椅到地坛那儿去。他自己说是“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但这样简单的原因,我却是在自己的眼睛残疾后,才真正理解。
所不同的是,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的母亲是怎样地为他有可能在地坛做出傻事而提心吊胆,可他都不曾去好好想过,因为那时他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却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而我,早已没有了父母,成为一个孤儿,所以并不会犯他当年由于年轻不懂事而从不为母亲着想的错,而且我也没有被命运击昏了头。我曾经多次想,如果有一天真的完全被黑暗吞没,我也不抱怨命运,平静接受好了。我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也不奢望他人的理解。一个人,如果学会了自己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便是学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一项生活技能,何况医生早就告诉过我,黑暗将我彻底吞没的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既然如此,我暴跳如雷、万分恐惧或者怨天怨地、自卑自怜,又能怎么样呢?我唯一感到痛苦的,是不能再捧读那些心爱的书籍,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了。每当我想到这些,我都会潸然落泪,心如寒冬……
站在书墨巷口的路牌下,我就这样静静地沉思着,偶尔有擦身而过的行人扭头看我一眼,却不理解我为什么傻站在这里,脸上还有没有拭去的泪水。
我想,眼睛的状况已经是这样了,连医生都束手无策,我又何必一味地絮聒这事呢?我没完没了地唠叨这些,会不会被别人看作很矫情或者很怯懦呢?会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呢?
不记得哪位名人曾说过:“大悲时不发声,大怒时不争辩,大喜时不许诺,就是最为明智的人。”
虽然我已经跌入大悲的门槛里,但在黑暗尚未把我彻底吞没时,我何不趁着这个空当,纵身跃入温暖的书海中,胡乱抓起一本我喜爱的书,朗声吟咏、大声诵读呢。尽管书上的文字在我眼前都已散乱,模糊不清,我也要能看见多少就诵读多少,总比向隅而泣、黯然神伤要好得多。
我这样想着,脑海里涌出了鲁迅先生说的名言:“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于是,我折转身走回家去,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在自己的那部新著《站在街的起点》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四个大字:光明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