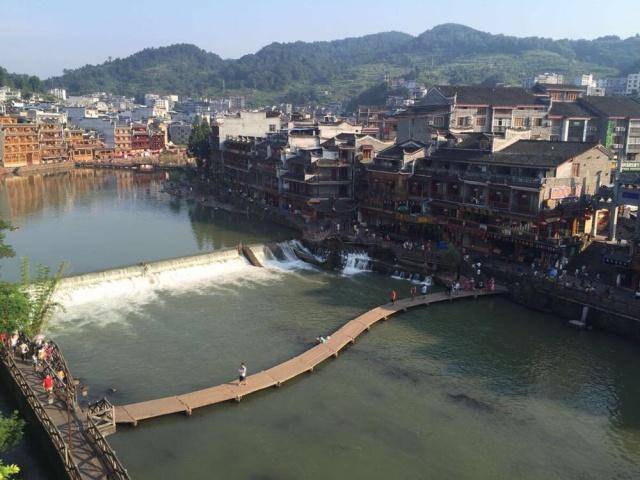冯春明
十年前的一天下午,我来到了一座很有名气的水库。那水库很大,水位很高,它尽管被群山环抱,但却开阔似海。
我是来这儿拍照的。当时,蓝天之下,长而宽的堤坝上空无一人。抬头望去,偌大的水面上,有一群野鸭临空盘旋。我的镜头开始缓慢地由水面逆向反转,当镜头移向大堤外侧的坝下时,出现了两位老人。镜头中,两位老人鹤骨白须,荦荦确确。他们互相搀扶,几乎是同步地一步一步的从坝下向坝顶攀爬。
在他们的身后有两辆老式弯把自行车,并排放在那里。我抓拍了这瞬间的影像,并待他们登上堤坝后,给他们留下一张合影。看到我为他们拍照,两位老人很是高兴,他俩告诉我,他们是从四十里外的一个村庄赶来的。我注意到他们手中的布包里装有煎饼、咸菜和大葱。看来,来这座大堤之前,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其中一位老人告诉我,修这座大坝时,他们还是小青年。当时,他们俩在同一个突击队里,大坝修好后,很少来过。如今老了,突然想起这坝,今天老哥俩早饭后相约,一起骑着自行车赶了过来。
望着眼前的两位老人,望着眼前这座宏大的堤坝,我的内心产生一种由衷的感动和敬意。此刻,大坝的沉寂被两位老人的脚步和声音一下打破了。我的视野里仿佛有一朵巨大的云团,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缓缓飘来,那云团带着一种群体情绪的力量,以一种深厚、浑沉的音调,裹着闪电,带着雷雨,伴着风雪,蓦然而至……
这是一座始建于1959年的大坝,它的年龄和我同岁。这座堤坝,形似山脊。它的坝体总长达1665米,最大坝高29.8米,总库容量7.49亿立方米。堤坝的宏大自不待言,历史的轨迹中,它的最让人感觉得到的震撼之处,在于它的建成几乎是靠肩挑人抬干出来的。
大堤之上,两位老人静静地站在那里,他们默默地直面那片广阔的水域。从两位老人的眼睛里,我发现了一种不易察觉的满足和快乐。我因而猜测,在两位老人的生命里,建设这座大坝时的时光,也许是他们的生命里最难割舍的一段时光了。因而站在这里的他们,让我毫不怀疑他们的心理或精神是靠这座大坝加以支撑和映衬的。他们留在这里的尽管是满身的汗水和疼痛的记忆,但他们的青春甚或人生的意义,却恰恰在这里。在这里,他们的内心世界,应该是在一个带有统一的价值框架中的感性活动中得到慰籍或巩固的。
这座被当时的临沂专署称之为“举全区之力修建”的大型水库,动工之前,有3.87万人移民他乡。当时,工地民工多达6万余人,他们用原始的镢头、铁锨,用营养不良的瘦弱的身体,用一种源于乡野大地的力量,奋力生成了这座大坝。其间,鉴于设备落后,当时的中央水电部考察组,曾经建议停止施工。但大堤还是在他们的手中建成了。
资料记载:“水库1959年11月兴建,1960年5月主坝及输水洞建成蓄水。”从建坝的时间上看,建坝的民工整整经历了一个冬天。此刻,我的大脑中出现了那6万多个身穿空心袄的人们。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不分男女,一个一个的在寒风刺骨的河道里,一镢一镢的刨下去,一锨一锨的端起土来,一筐一筐的抬上坝去……寒冷中,他们是咬着牙的,他们又是唱着歌的……我想,当时寒冷的河道里,绝对不仅是眼前所能看到的这些……因为这些已经是冷凝下来的,物化了的,无声无息的存在了。
是的,那个冬天,河流被雪花照白,“大坝底槽内,开始涌出泉眼,泉眼越来越多,水涌如柱……”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冰天雪地中,一个接一个的披着雪花的男人的影子,像雪花一样纷纷跳进水里,他们异乎寻常的,高度亢奋的,全身心的融入到一个带有史诗性的画面中……我仿佛看见,水潭也被雪花照白了,那里呈现出一湾蒸发着人的热度和信念的深厚的水域……很快,泉涌被堵上了,而我的眼睛却湿透了。
站在大堤之上的我,被那团寒冷中燃烧着的活火烤灸着,我非常不安的发现,以我现有的尺度和视野,是很难理解这股滚滚而去的洪流的。此刻,两位老人还在那里,我要了两位老人的地址,我告诉他们,我为他俩拍的照片洗好后就给他们寄去。两位老人喜出望外,一再表示感谢!
天不早了,两位老人骑上他们的自行车回家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望着被这座水库惠泽的沂蒙大地,我在想,两位老人所处的这个年代的人们,他们的行动绝对不是用制度的绳索或命令的强制所能解释得了的……
这些几乎全靠人工建成的大堤,在长江以北随处可见,它们大多是我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筑起来的,后续的工程也有我的兄嫂那一辈人的参与。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营养不良和身体过度的透支,已经早早离开人世,幸存的也积劳成疾,整日处在痛苦之中……从那之后,我们没有再像我们的前辈那样遭遇缺水之苦,如今,在许多地方,人们把这些前辈们用血汗和生命筑成的大堤冠以“湖”的名字,使之成为水上乐园……
那些筑坝的人大多已经走了,尚在人世的也已很少被人们所注意。如今人们在忙着炒房、买车、喝酒、成名,却很少有人关心他们的存在,很少有人关心我们正在喝着的水是从哪里来的……
对那些用青春和身体筑成大堤的人们,我们至少应当记住他们,对那些尚在人世的他们,至少应当多给一份关照,没有他们,没有我们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