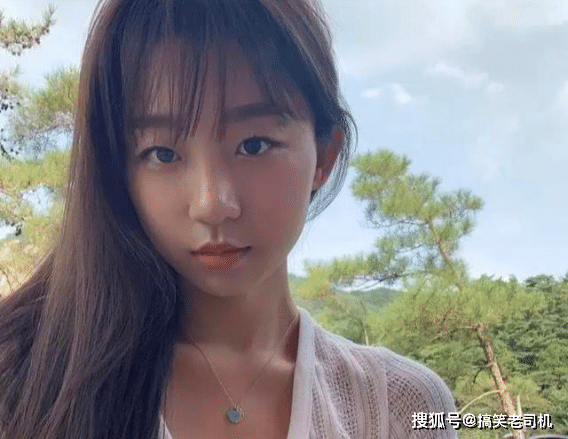有人在道旁路侧喜欢流连于橱窗前面,也有人喜欢仰起头来,观览那些五光十色的店铺招牌和充满古典意味的“布招”。在艺术的观点上,后者较前者似更胜一筹,但除了小城镇中,极少数的店铺以外,这种保持着诗词中“酒帘”风味的布招,已很难看到了。
从前在北方古城读书的时候,课后常常和一些窗友们,到前门一带的老店前,去欣赏那些古色古香的招牌和布招,也喜欢在那些卖零星物件的小摊前走走,在那里每每可以发现一些色彩斑斓的出土古物,有个同学还希望在那里找到一盏桐油灯碗,以伴她读书呢。
我们最喜欢一家小面馆前的“招子”,那是以红、白两色的纸剪成的流苏,那些细细的丝络,在风中云绺似的款款欲飞,我们觉得那是一个象征,一个只应出现在李商隐的《无题》诗中的象征,丝丝的细条,软绵绵的,好似江南春天的长脚雨,自天半扯了下来,将人的心灵都绾住了,使阶前的草间的翠色流动起来,发出奇光……
而那诗意的“招子”下面,是那小面馆里黑黝黝的屋子,充满了暗影和陈酒的香味,屋角一块木板上,是一个灶神像,被烟熏火燎已久了,像前是那枣子似的一点香火,发出青萤一般的幽光,这一点光亮,说明了那一份感人的信心——多少年来维系着纯朴心灵的信心的一点光焰。
那些卖铜盆的,蜡烛台的以及钥匙的老店,有些是自明朝就创业了,有些至少也有百多年的历史了,各家以笨拙古朴的手法,将他们售卖的东西,画在那些临风转动的招牌上——有些招牌,是铜做的,黄澄澄的颜色,迎着日光,显出熔金一般的光灿来,不必走进店里,这些招牌就够使人叹赏的,这是地地道道的民间艺术。
我还记得一家招牌上画的大型的千层底“抓地虎”绿皮靴子,那使人想起了一个在战场上的英雄——每一个招牌上,都有使人联想到一段人海的传奇,再陪衬上招牌下面店伙计们纯朴的脸,和更纯朴的笑声,使人真觉得那时候那地方人们的可爱处——这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古城中,三十年前那份空气也是可爱的。
那里也有一些小摊子,书摊更多,我永远忘不了一个穿深色衫子的老人,默默无言地守在他的那个书摊旁。我曾经有一首小诗,记叙那一带的风光,其中有几行是:
我记得那一地斜阳
还有卖书老人的深色衣裳
我买去了他的书册
却买不去他暮年的悲伤。
斜插在他那几本风渍书的招牌太感人了——一方硬纸剪成的,下面有个小小的木柄,上面以颤抖的手写成欹斜的字迹:每本三角钱!
每本三角钱——在这五个字里我听到那老头儿的呜咽!他的书都是相当不错的,我记得曾在他那小摊上买到过两本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一本冷红生译的《海外轩渠录》,还有一部《历代名人书札》以及其他的一些小册子。
那些书也许是那位老人多少年来自己珍藏的,后来,也许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拿了出来。而因为都不是一些畅销的热门书,他只有削价出售——一本三角钱,这价格,在那时候可以使他付一顿饭钱。我此刻犹能忆起他那双黯淡的眼睛,黯淡的表情。他最珍视的精神财富,竟以那么低的价格让给了别人,这一个悲剧,谁能懂得?而我也还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才理解。
半生以来我看到过不少出售物品的招牌——金碧辉煌的,五彩绚烂的,而只有书摊老人斜插在一堆旧书中的那一块,最使我感动——那是一首五个字的生命悲歌。
张秀亚(1919.11.8-2001.6.29 ) 女,作家。河北沧县人,祖籍河南,笔名陈蓝、张亚蓝。幼年时全家迁居天津。1932年入省立第一女师。1935年开始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国闻周报》发表作品。第一首诗作《夜归》现收入诗集《秋池畔》。1937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大龙河畔》。
1938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次年转入西洋文学系,毕业后入本校研究所史学组,后任助教。1943年到四川重庆任《益世报》副刊编辑。1946年回辅仁大学任教。1948年到台湾,1952年出版到台后第一本散文集《三色堇》。1958年任台中静宜英专教授。1965年辅仁在台复校,回辅仁任中文系和研究所教授。1973年赴美考察,并在西东大学进修。创作风格新颖清丽,意境深远。作品以散文著称。的又一日》、《秋池畔》;其他还有《诗人的小木屋》、《写作是艺术》、《张秀亚选集》、《张秀亚散文集》;另有与法国Lefeuvre合著的《西洋艺术史》著作11册,翻译著作1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