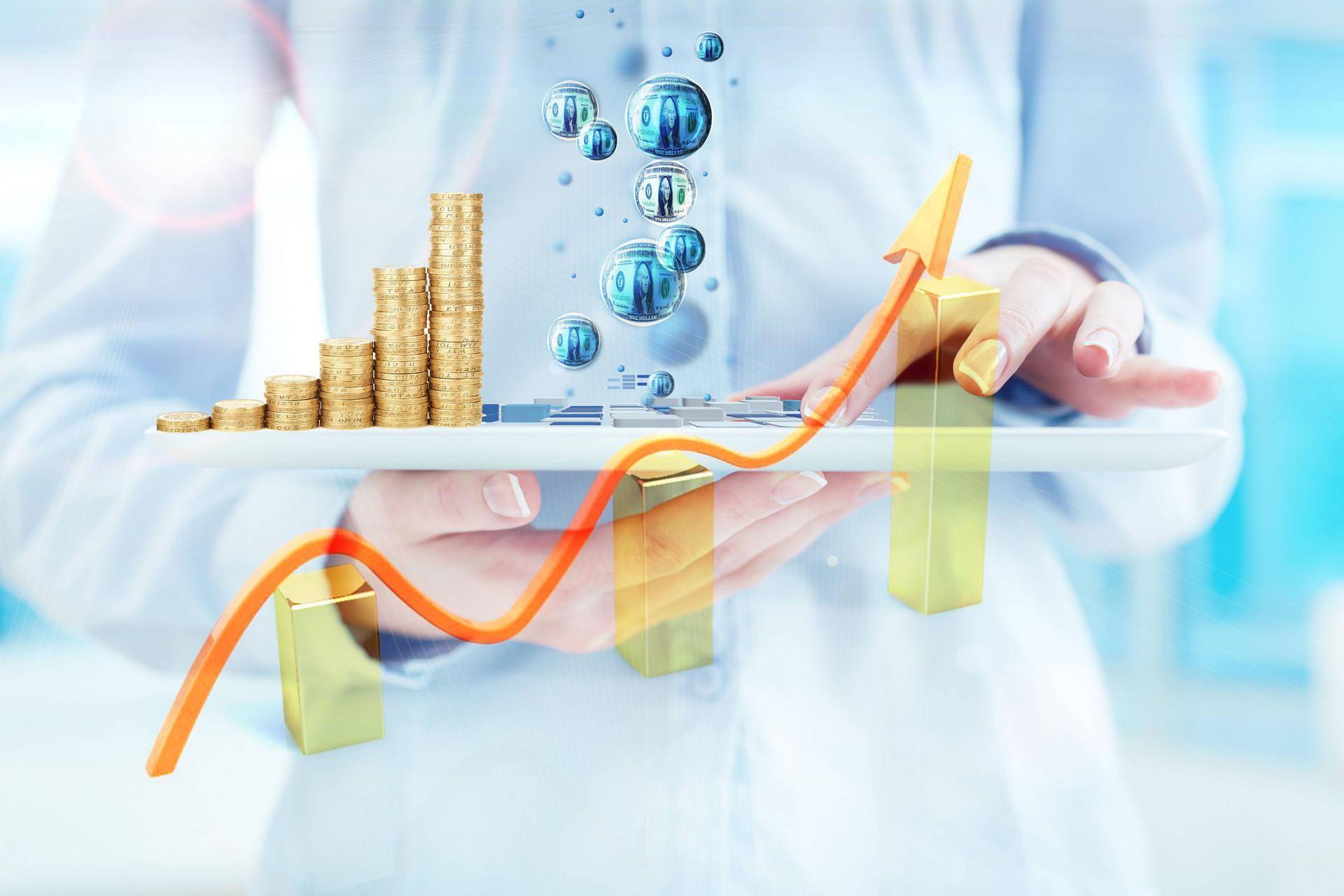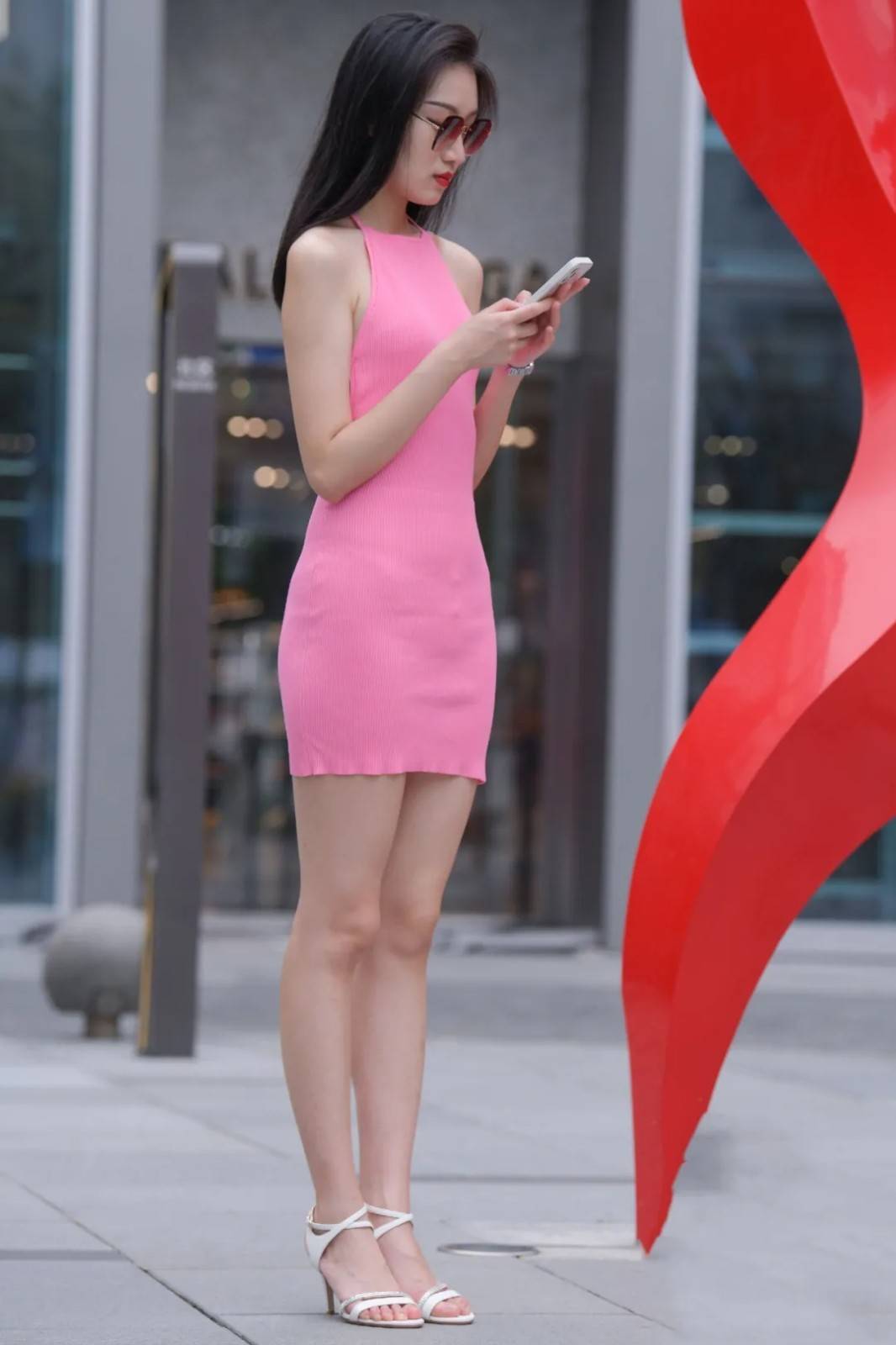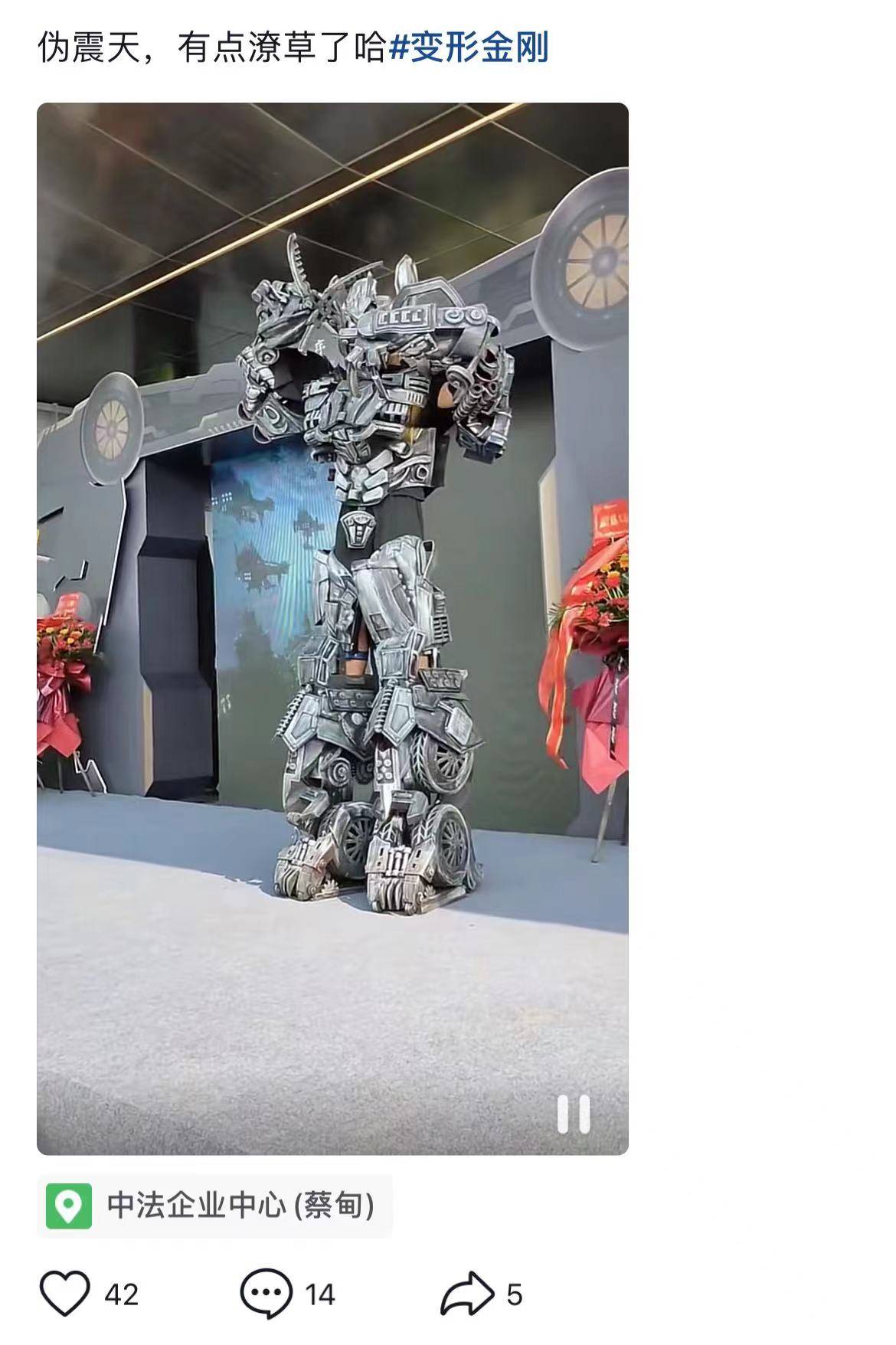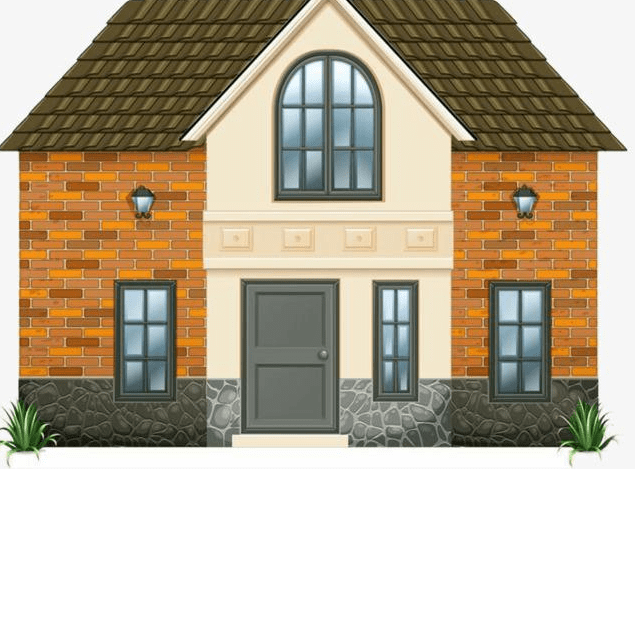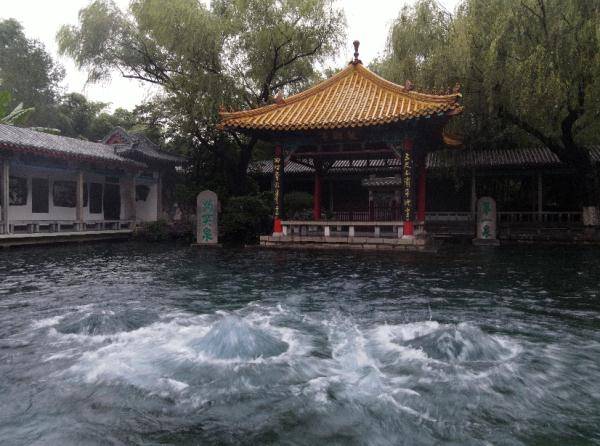故乡那湾“南湖”
我的老家高密尚口,东依青龙山、西傍五龙河,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小村庄。据说祖上是洪武年间从河南省鹿邑县辘轳湾迁徙过来的,到了今天,已经发展到二十左右代了。据说高密周边姓鹿的,无不出自尚口,这话无从考证。却有地方志记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支援边疆”的时候,从尚口迁出了不少人家,至今在东北的镇赉、桦甸等地,还有很多来自“高密尚口”的成编血脉。
我们这个村子全姓鹿,可谓“一鹿阳光”。虽然现在也有他姓零星点缀,但其实都是老鹿家的女婿或者投奔亲属,比例微乎其微。
我不知道尚口是什么时候一分为二的,但我知道,路南是“老尚口”,是老祖宗迁徙过来时候的选择,路北是“新尚口”,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但这还是一个村子,毋庸置疑。虽然在机构精简的过程中,尚口却真的“一分为二”了,但老少爷们们并不在意这些,只是多了套班子而已,大家还是一家人!
还是一家人的时候,路北有一湾水,位居“新尚口”的村最南面,而且至今记着那湾水四季不干,冬季可以冰封,就成了孩子们滑冰放肆的游乐场,夏季来了,就变成了天然的游泳池。据说湾水中间是挺深的,还有淤泥,所以大人总是告诫自己的孩子,可以在湾边玩玩,中间是万万不能去的。
我因为并不喜欢“水中嬉戏”,所以那湾对我来说,只是给生产队洗“喂牛草”的地方而已。我是1965年出生的,可能刚会走路就需要“干活”吧,已经不记得确切年龄了,反正至今,我不记得我还有过什么纵情快乐的童年,有的,只是给家里、给生产队干活。
已经忘记从多大开始了,家里就把每个社员五斤干净喂牛草的工作,安排给了我。我们家当时是六口人,每天需要割30斤青草。至今记着具体的标准是,必须是牛喜欢吃的、必须洗干净了,然后再交到第八生产队的饲养院里。负责收草的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哥鹿钦宝,他可能比我大几岁的样子,人也本分,却无比认真,总是认真的看磅、认真地检查“草质”,稍有不合要求的,便在本子上记下来,让我至今想起来就“胆颤”……
那个时候满河崖、满西岭上,都是我这般大的“割草”少年,也都是大人安排好了的上缴任务。其实我们也不是割草,而是剜草。剜草的工具叫“铲子”,手攥的地方,必须是一个合格的三角树杈,截好之后,一节固定在铁质的铲子上,另一节木把,正好可以用手拿着铲草。草铲足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挎着槐树条提篮,来到那湾,一字排开的开始洗草、甩干,再小心翼翼地装到提篮里,挎着到饲养院里找钦宝堂哥检查、过称,再小心地看着他的记账。
那湾,就这样跟我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个时候,凡是要到我们村子的,都必须从湾边上拐弯,然后或者骑车、或者推车、或者走路到村。也偶有汽车或者拖拉机进村,但那都是稀罕事,一年也进不来几次。
那湾最快乐的时候,当属最热的伏天了,湾里大人孩子们,一起嬉闹避暑。据说村子几个胆大的妇女,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来到湾边,撩起外衣,感受一下湾水的清凉。但我那个时候很小,并非亲眼所见,所以都是道听途说。要说亲眼所见,只是在看电影的时候。那个时候村子来了放电影的,都是在那湾西面的空地上,无论冬夏,雷打不动。于是,天热的时候,不少妇女便会坐在湾边,将腿脚放进湾里解暑。
我虽然只是以洗喂牛草为主,但那湾还是成了我的“训练场”,至今没有进步的狗刨等游泳技术,最先就是从这湾里“自学成才”的!
那湾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有年水涝,村西的“五龙河”泛滥,一片汪洋地一直“荡”到了村边,村里的劳力便在那湾以南造堤挡水,那堤坝绵延看不到边,庄稼已经泡在水里了,我就天天跑到那湾边,看着我爷等劳力划着木排,到水里收庄稼。那是个秋天。另一件就是村子的驻军过来了,整齐地从湾边进去,很是威风。至今不知道过来了多少部队,却跟老少爷们的关系处的很好,一大早上,他们总是争先恐后地给家家户户挑水,不知疲倦。但他们闲下来的时候,也偶有互相“闹”一下。据说有次他们正在闹着,我们村一个回家探亲的团参谋长就听到了,走出门外,啥也没说,几个“调皮”的小兵立即敬礼。写到这里,忽然想起,这个时候已经取消军衔制了,他们是靠什么分辨的职务呢……
如今那湾已经没有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填上的,更不知道为什么要填上她。只是,那湾,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村子的一面南湖,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已经撇不开她。
因为,她已经刻进了我们那代孩子们的记忆。
鹿钦海草于2018年1月20号,于山东东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