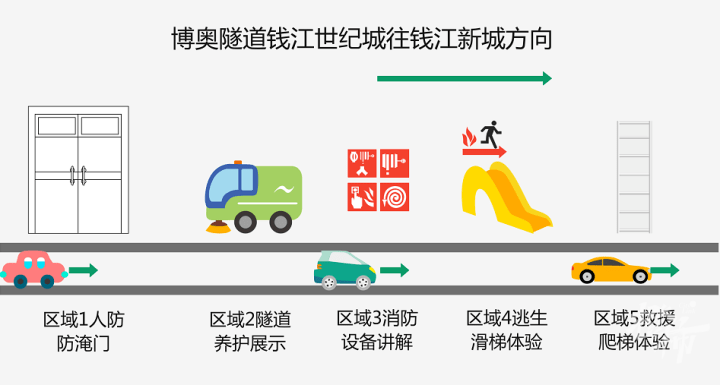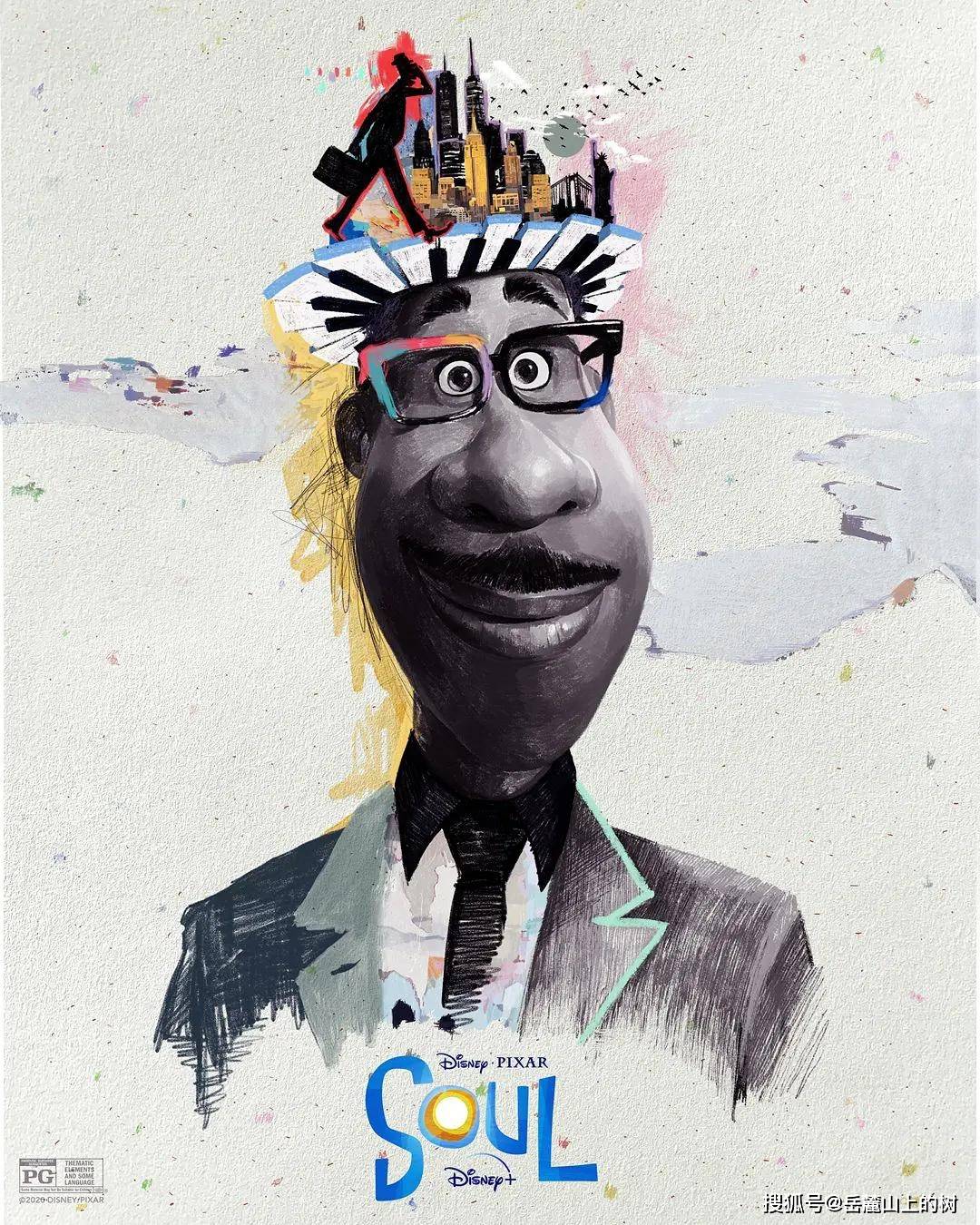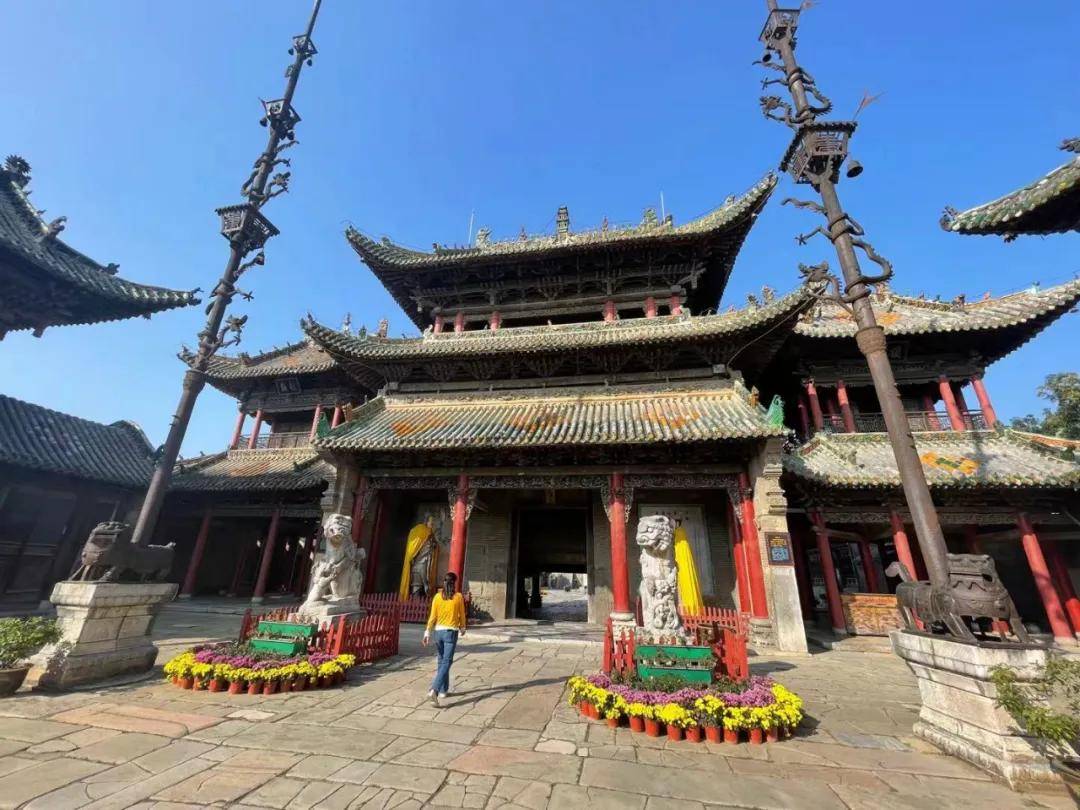语言具备一定的适用性,并不是一种语言放到世界任何地方都能通用的。

在东北讲上海话,会让人听不懂,在陕西讲四川话也让人听不懂,在河北讲新疆话更让人听不懂。一个地域的方言有自己的特征,适用于特定地域的特定人群,超出那个地域或特定人群之后,就不具备适用性了。随着普通话的普及,人们大多都能听懂普通话,但外国人就不一定能听懂了。即便英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到了非洲的部落,人们说英语,他们照样听不懂。可见,语言的适用性普遍存在。俗语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入乡随俗”就是这个道理。
人们到了外地旅游,要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融入当地的风俗习惯,不然只会碰壁,甚至被驱逐。有人说话带脏字,到了一个旅游景点,满嘴脏话,结果被保安听出来了,遭到了驱逐。还有的人对人指手画脚,也造成了一定的误解。于是,很多人到方言区旅游,就要找导游,找翻译,有时候导游就能充当翻译。也就会说,要想达到不同方言的相互理解就要找中间人,而中间人就是翻译。翻译能同时听懂两种不同的语言,甚至能听懂多种不同的语言,以此跨越语言适用性的障碍。就是和外国人对话的时候也要找翻译,毕竟外国人也有方言,也有相互不理解的时候。伦敦英语和苏格兰英语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就好像普通话和四川话的区别一样,需要找翻译。或者说,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四川人能听懂普通话,而北京人却听不懂四川话。虽然北京人占据了一定的文化优势,身份地位也比较高一点,但在语言方面,四川人还是占据了不错的优势,起码可以理解甚至会说普通话,而北京人却不理解四川话,也不会说四川话。即便是四川话也有很多地方的方言,于是邻近的区域可理解程度就会越大,而距离比较远的方言,可理解程度就会变得很小,甚至完全不能沟通。语言的适用性随处都在,而且很多地方还有特定的隐语、行话、黑话等,只有特定的人群知道,而别人却不知道。买卖牲口的时候,人们会知道特定的暗语,而旧社会的土匪会说黑话,外人是不知道的。

就是一些学术领域或宗教领域也具备一定的语言适用性。医学领域、物理学领域、文学领域等都有很多专用词汇,普通人是无法知道那些词汇的真正含义的。除非去查专业词典,能够大致了解一下,但还是不能完全理解。譬如医学领域对很多疾病的命名,对很多社会关系的隐喻性表达都是门外汉们无法真正理解的,比如夏柯三联征、雷诺五联征、细菌性肝脓肿等术语,很多人都听不懂,即便是别的科室的医生也不能完全理解。物理学领域的原子光谱、粒子对撞等,不是物理专业的人只是理解字面意思,却不知道这些术语的真正意思,或得出什么结果。文学领域的行动元、元叙事、民间故事形态学等,非文学专业的人只是理解一个大概,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些名词代表什么规律。宗教内部也有很多名词,佛教、道教、基督教都有很多特定的专用名词,只有信奉同一种宗教的人,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宗教阅历才会听懂一些宗教专业名词,不然只会和那些宗教传播者隔着一层,不存在相互理解的可能性了。尽管佛教有名相之辩,但还是有很多专业名词和书籍作为引导人们信仰佛教的东西存在,而这些东西看多了,人就会变得博学起来,但只是在佛教一种教派方面变得博学了,而在其他教派方面,可能就是一个门外汉。只是,越是懂得多,就越会陷入了一种执着,甚至感觉很多概念存在着冲突,不能自圆其说,以至于自己难以自拔。于是,很多佛教徒就要参与辩论,在辩论中增长见识。而辩论的基本功就是要懂得佛教的一些专用名词,阅读一些佛教的经典。要是不懂一些佛教的专用名词,也不去阅读佛教经典就参与辩论行不行?当然不行,会被参与辩论的佛教徒看不起,认为不懂专用名词的人是门外汉,是没有讨论资格的。即便不懂专用名词的人已经是个了悟之人,也不会获得那些用专用名词去讨论的佛教徒的认可,因为他们只能在佛教的专用名词里打转转了。
语言只是能指,而语言表达的内容才是所指。同一种东西或境界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单单纠缠于一种语言就会陷入一定的偏执,而且不一定会抵达所指的彼岸。也就是说,虽然语言具备一定的适用性,但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所指的东西可能是一致的。超越语言的能指,直接达到所指,就是禅宗所说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了。超越文字的适用性,就能了悟人生,要是把那种境界表达出来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毕竟语言是有一定适用性的,有一定的边界,无法真正表达所指的内容,就像陶渊明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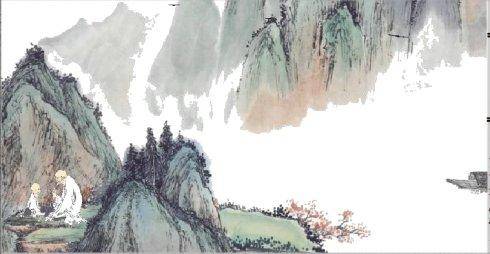
既要看到语言的适用性,又要超越语言的适用性,实现精神的飞跃和自由,这样才是智者的思考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