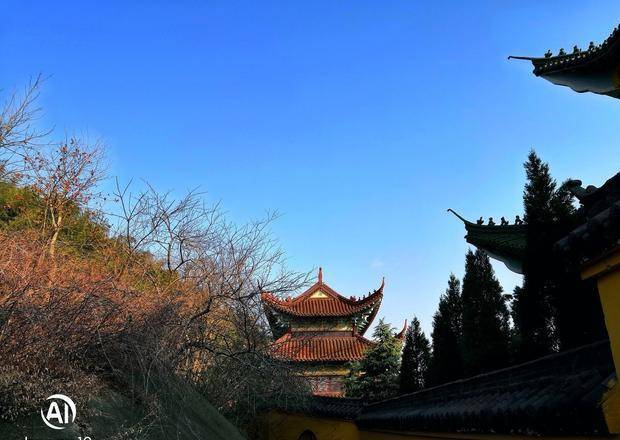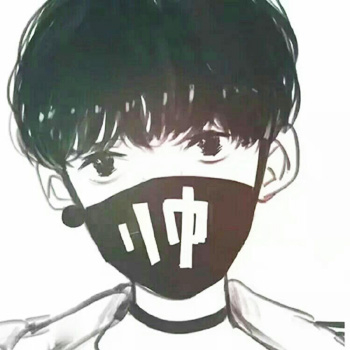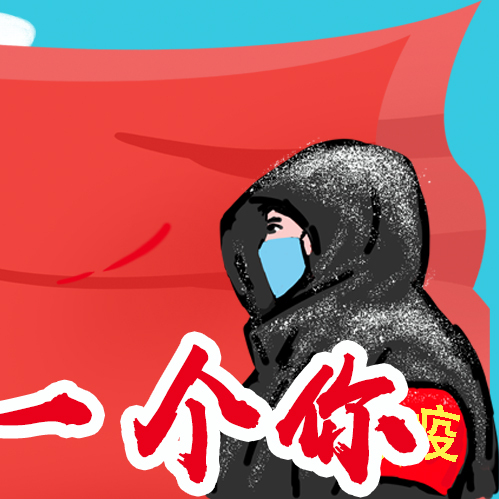《野梨树》 《鸡蛋》
◎张阅
我去过土耳其,看上海艺术电影联盟推出的“土耳其电影周”,有故地重游的亲切感,因为努里·比格·锡兰和塞米赫·卡普兰奥卢这两位大师风格不同的作品,都贴近诗意情感、普通人的生活和人的真实困境,不夸张,不悬浮,又都有些魔幻灵动。
从电影我们发现土耳其青年想追求远方的生活,像中国青年青睐北上广一样,只有首都安卡拉、国际化大都市伊斯坦布尔、略带江湖气的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等几座城市可以选择。年轻人的心思,又能有多少不同呢?
努里·比格·锡兰:凡事理解凡事包容
锡兰的名字按土耳其发音是“杰兰”或“杰伊兰”,习惯英语的国际人士容易唤他做“锡兰”,不知他是否便故意在最近的《野梨树》里为疑似有自我隐喻的男主角取名“锡南”。这故事比锡兰昔日作品更直接地指向他所熟悉和感兴趣的知识中青年。他的《冬眠》是实打实讽刺知识分子,《野梨树》更像是安抚他们在追求文艺理想时无处安置的精神。
锡南有一个愿望,一个困惑,愿望是出版自己第一本散文和故事集,困惑是沉迷赌马的父亲搞得家里一贫如洗,他能不能把父亲挚爱的猎犬卖了换钱出版这本书?影片从开头就暗示他在盘算。锡南一边谋生一边谋梦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青年按导演思路依次幻灭的过程:政府幻灭于虚伪,爱情幻灭于金钱,友情幻灭于情仇,教育幻灭于考试分配制,文学前辈幻灭于自私自保,资本幻灭于骄傲无知,锡南眼看着家庭在辜负背叛、彼此怀疑中勉强维持,两个平日带领乡民祈祷的伊玛目,用懒于思考的世俗态度,杀死了他最后的挣扎,他卖了狗,出了书,为私人梦想卖了良知。出书后是更大的幻灭,人生之问、意义之问横在眼前,他最看不起的父亲,倒成了他世间唯一的读者和知己。
如果说特洛伊原址恰纳卡莱、家乡小镇、乡下祖辈似对应锡南的超我、自我、本我,父亲的本我则一直困于小镇生活,他就是令那位前辈作家烦躁甚至害怕的“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他那些改造乡村的执拗实践,颇似《百年孤独》开篇那位异想天开的父亲),无论养狗、牧羊还是赌马,都源于他与自然界的亲密关系,他是个善良可爱、富有诗心的失败者,甚至原谅儿子的伤害,父子在深过血缘的生存价值层面和解了。
愣头青锡南的一败涂地有导演自嘲的成分,他怼天怼地的刀锋态度是作家得以成才的性格特质,但《小亚细亚往事》里的法医则以更内敛理性的性格包裹了他的刀锋。这个故事有契诃夫式对人物深入内里的嘲讽和揭示,又有托尔斯泰式群像全景描绘和温柔抱慰,甚至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伦理绝境选择,锡兰日后会在《冬眠》中进一步发挥他汲取自俄国经典文学的风格。
小亚细亚发生了一桩命案,警察、检察官、法医等一行十几人随嫌疑人连夜寻找埋尸点,锡兰让我们看的不是命案本身,而是凡尘间的人物心理群像,比如因无法忍受孩子生病而变成工作狂的老警察,自家过得好、村子电力都挂掉的镇长,最牵引观众兴趣的是风流自恋的检察官讲述的“朋友美妻”莫名死亡的故事,随着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检察官的性情和内心折磨也在自述和别人的闲聊中层层剥出。尽管锡兰让乡村女孩以圣女般的美丽照见坐在黑暗中的众人心灵,引发顿悟时刻,但锡兰关心的,仍是如何在世俗世界以妥协的生存方式保存良知,这态度是暧昧而无奈的,这是他与偶尔被拿来比较的阿巴斯之间的差异,阿巴斯用不相信“死后世界”的斩钉截铁之态度,关心如何在世俗世界追求爱、神性和生活的积极意义。医生打断别人议论检察官私生活,是锡兰对凡人的包容态度。
塞米赫·卡普兰奥卢:看不大懂,但深受震撼
塞米赫·卡普兰奥卢的切入点比锡兰更私密,他善用声音和影像而非小说般的精彩台词对观众造成直觉性感染,这会对部分人造成“我看不大懂,但我深受震撼”的心理冲击,也容易让人想起润物细无声的阿巴斯。塞米赫的《鸡蛋》《牛奶》《蜂蜜》三部曲,按倒叙时间分别展现同一个人,即诗人“约瑟”,在中年、青年、童年三个人生阶段的故事,而且他是将三个阶段并置于同一历史时间,即当代。
《鸡蛋》台词不多,我们能直观感受从伊斯坦布尔回伊兹密尔省乡下老家奔丧的约瑟的内在世界,他的疲惫精神、习惯性逃避、对母亲的依恋、深到恐惧的脆弱、梦与现实不分的幻觉、与树木土地毫无隔阂的亲密,使我们困惑又好奇,但导演只是抛砖,引我们走进越来越精彩的《牛奶》和《蜂蜜》,追溯一个人之所以如此的答案,再回头理解并接受导演为这个男人设计的温暖结局。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约瑟看到一个男人来回拉绳子就能突然晕倒,《蜂蜜》会讲他父亲之死与这个动作的关系,也会讲约瑟遗传自父亲的癫痫,这个病使他在《牛奶》中无法服兵役,无法与身强力壮的青年合群,这一尴尬处境加重了他对他人的嫉妒,对爱情的退缩。
《牛奶》的台词更少,不同场景的人物活动,在观众心里产生蒙太奇般的拼贴效果,导演刺激我们在被动感受的同时,主观上企图从信息拼贴里找到多义解读。约瑟看着别的青年搞摇滚,自己却缠着老诗人追求诗歌梦,这是他的不合时宜。锡兰会花大量针锋相对的台词展现文学前辈对青年造成的幻灭感,塞米赫只用约瑟送酒鬼老诗人回到他孤寂萧瑟的家中这一两分钟戏就做到了。他的工人诗友可能高于他的诗才是通过约瑟视线里的人与景、帮忙投稿时的犹豫展现的。为表现约瑟最终面对现实去打工的迷茫悲凉,导演将观众拖入头盔探灯在黑暗中的巨大光芒,我们与约瑟的所感同步。
《蜂蜜》说的是人在山野间最初的纯真状态,因而最受观众欢迎,也是童年经历对成人约瑟的大揭秘,他崇敬的养蜂人硬汉父亲在片头就已出事,观众一直在等待另一只鞋掉下来。童年约瑟望着妈妈脚踝痴笑的恋母本能、对父亲关爱的别人家孩子的嫉妒心早早显出,林间生活赋予他的诗性和梦幻。一切都是自然的,连孩子在苏丹式沙发上的睡眠都是自然的,我们看完后没有想象中悲伤,也是因为自然之美……
两位土耳其大师的影像空间里,意识与潜意识都是互相关联、不分主次的,这就将个人经验与普世慰藉、角色现实与思维活动、土耳其真貌与影像造梦交织为了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