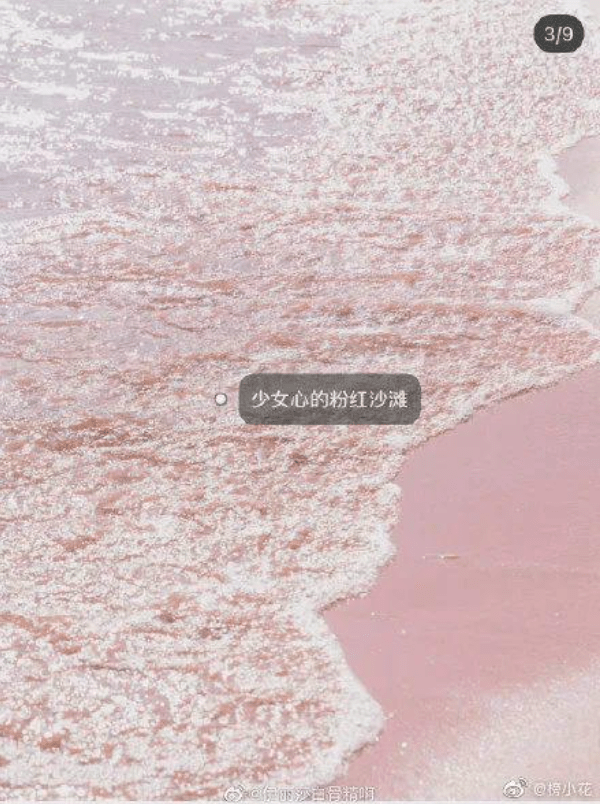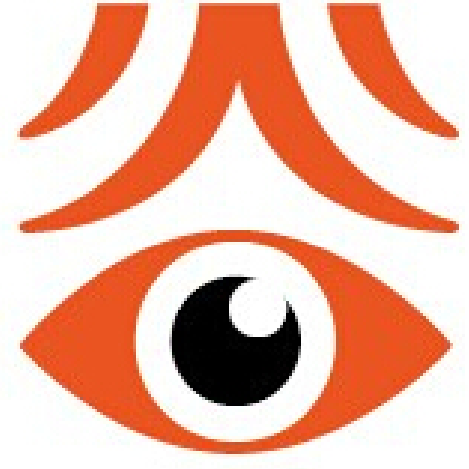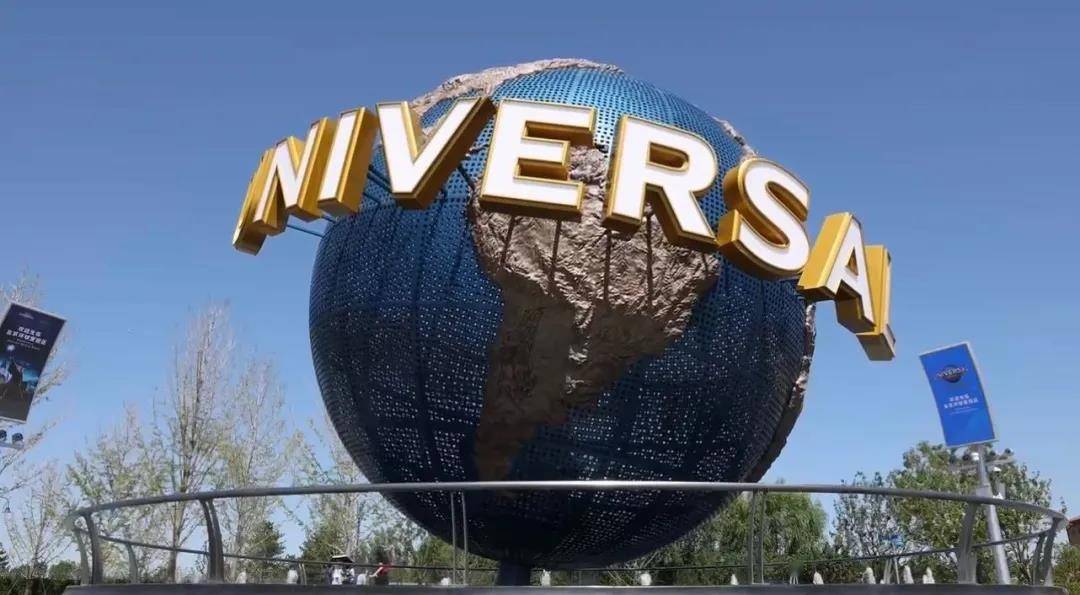冯春明
每次来陕北高原,我的思绪总难以平静。这有着千沟万壑的黄土塬是哪里来的?这些面粉一样细密的黄土,它们堆成岭,长成山,生成壑,抱成团,连成片……它们是怎么形成的?这是何等神奇的造化!
据说,这土是风搬过来的,这风也够任性,够爷们的了!真得是这样吗?这比把神州所有的山脉累加起来还要大的多的高原,难道是那一阵阵称不出任何重量的风所能做到的吗?然而,眼前的事实似乎正是这样。亘古至今,那些看起来虚无缥缈,一年一度的沙尘暴,似乎就是一个明证。当黑风骤起;当天地闭合;当沙尘弥漫;当黄褐色的沙尘卷成庞大的云团,滚滚地从西北天际浩浩荡荡而来的时候,这个答案就有了。
这土是从哪里搬运来的呢?新疆?蒙古?甚或更远?应该是吧。如今,那里好多地方只剩下沙漠了。壮哉!这无影无形,但却感天动地的力量!不得不佩服这风!竟硬生生地吹出一个大漠,筑起一座高原来!
漫漫时光中,这些满天飞舞的黄土,它们自空中来到这里后,大多停了下来。这时,应该是天上的雨出手了。那雨不大不小,恰好把一团团自西北天空而来的黄色的尘烟缠住,它们结成伴,抱成团,一点一滴地,一辈一辈地做大了起来。
这风与雨的默契让人吃惊!雨如果太大,一下就会把那些滚滚而来的烟尘冲走;如果太小,那些烟尘不等落地就被大风卷走。它们只有做得恰到好处,才能成就眼前的这一道道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黄土高坡来。
每次来这里,我的思绪就深陷这片厚土。我在想一个也许被许多人看来难以接受的问题,那就是有关匈奴、氐、羌、羯、蒙等游牧民族南侵的问题。尤其那些曾经生存在西北大漠上的人,当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日见消失的时候,“南侵”就像随风而来的漫天黄土烟尘那样,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些游猎于“天茫茫,地苍苍”的草原民族,他们从远古开始,就像风一样的持续不断地刮着。他们是带着嫁妆来的;他们是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来的;他们是带着粗矿、豪放的歌喉来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像这些黄土一样,与这里的人,与这里的所有紧紧黏连在一起了。他们与这里的一切事物一起构成了一幅新的画图,图画中,越来越分不清你我……
每次从沂南驾车来这里,我都喜欢独自沿着挂满红枣的深沟,踏上黄土高坡那条通向蓝天的路径。走在这个历史上连接着中原农业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通道上,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数千年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奔涌而来的那股毫不示弱的悲壮力量。因而,我更愿意把这里看成一个民族的熔炉!且心存敬畏!我喜欢在这个尚有余温的炉膛里,仰视和倾听在那场灼热的悲情中催生出的竭斯底里的呐喊,以及伴随各种爱恨情仇而来的死亡和再生。 自此,黄土高原有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与滚滚黄河一起奔流不息!历史的镜像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自此,陕北人,不,整个中华民族,是从这里开始,在这个数千年来不断冲突、碰撞、交融的熔炉里,得以从血液、相貌和文化性格上重生的。
公元前1046年,有一股被称为“祖先踩到巨人的脚印,而后感孕而生”的力量从黄土高原出发,他们在中原大地上建立了第一个具有封建制、宗法制、井田制与礼乐制,对以后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周朝;公元前247年,从这里席卷华夏的秦始皇,首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800年后,从这里出生的李渊一举打造了中国历史上光彩照人的盛唐……
每次来黄土高坡,我都能在沟壑间的道路上遇见头戴白毛巾,赶着牛车的陕北人。见到他们以后,我才懂得什么叫土生土长了,他们那些让人听不懂,却能让你看得懂的陕北方言,他们那热情的让你无话可说的真诚……也只有在这里才能长的出来! 这里的农作物主要是谷子和红高粱。尤其是坡底和坡上那一片一片灿黄的谷子非常显眼,很远就能让人看到。那谷子的谷穗又粗又长,谷地里,没有像我们老家种的谷子那样,为防麻雀得用网罩着。这里也没见麻雀,只见不时有野鸡从脚下突然飞了起来。另有三三两两的长着长尾巴的小鸟,不时的在枣树枝上跳来跳去的。也许因为这里的谷地太多了,即使有麻雀也没大碍。
这里的村名大多带有沟、坡、坬、梁、峁、砭、畔、蒱、台、滩、河、湾、坪、川、渠、岔、塌、塬、岭、墕、窑科、窑子、崾、岘、圪塔、圪闇、圪堵、圪唠等,看来都是根据地势起的名字。村庄大多是窑洞,你不用担心它坍塌。这面粉一样的黄土,历经亿万年的沉积,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整体了,它比我们老家房屋的抗震能力还强。
秋天的黄土高坡到处都是枣树,满地是枣。公路上有许多从坡顶上滾下来的大枣,护路员懒得捡,直接把那些大枣扫到路边上去了。我在家时一般不吃枣,因为那枣在枣园生长的过程中,可能喷洒过农药,吃的不踏实。这些枣可就不同了,这里的枣树遍地都是,价钱很低,老农懒得管,哪有功夫打农药,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吃。
在一个名叫郭家圪唠的村庄,我遇到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其实比我还小三岁,但的确是位老太太的样子了。那个下午,嘉鸿兄他们在老太太屋顶上写生,我拍完照后,也过去了。这时嘉鸿兄他们基本画完画了。老太太看到我后,用我听不懂但却看得懂的方言,告诉我捎着几个南瓜。我本来不想拿,一是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再是我脖子上挂着两个相机,确实不方便。但老太太就是不让,硬把我领到她家窗台前,给我捡了两个成色最好的扁圆形的南瓜!我被感动了,尽管挂着相机不方便,我还是用两手把那两个南瓜托了起来。没想到老太太还没完,她又领我到了她的一个小屋前,用手指着小屋顶上两筐大红枣,让我装兜里。看她那么真诚,我又弯下腰来,放下手中的南瓜,抓了一把大枣装在兜里,老太太才算满意。
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很感动,这地方的人太好了,我跟嘉鸿兄说。这次我彻底明白,当年,我们的共产党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地方。
100多年前,来到延安的英国传教士史密斯,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的调查工作渐渐让我产生一种近似敬畏的谦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是有世界性意义。对这个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就与日俱增。不管我们对延安的未来有何贡献,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延安的历史不会从我们开始,它的历史比亚伯拉罕还要古远,我们是永无止息的,各种各样访客中最晚的,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员……”是的,100多年前的史密斯感受到了,每一个有着敏锐直觉的人感受到了。不,在这个沟壑纵横,山高沟深,天高云淡的高原上,每一个走到这里的人,都能从这片厚土和滚滚东流的黄河中,感受到一个民族碰撞交融过程中的史诗级的力量。
可以说,陕北高原流传甚广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地理文化名片和历史文化符号,它有着独一无二的丰富和沉厚。
路上,我举起相机。蓝天厚土之中,猛地有一股尘烟在我的意象中腾起。咚咚咚……那声音越来越大……那是冲锋的鼓点,也是将士征战凯旋的乐曲。这种沉浸于激情的爆发力,深深地根植于陕北这块古老的高原和这个民族的血液里了。站在这里,你会真切的感觉到鼓点内在的旋律,那鼓点于苦痛中呼喊,于激情中宣泄,于诗意中追求着鲜活生命中的永恒精神力量。
在陕北期间,我多次走近黄土高坡下的窑洞,那窑洞历尽沧桑,几经风雨,但却依然站立。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产物,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独立式窑洞。靠崖式是在天然土崖上横向挖洞,宽3~4米,深可达10多米。相关资料记载:陕北建造窑洞,最早应该始于周代,半地穴式。秦汉后发展为全地穴式,就是现在的土窑。眼前的窑洞大多已经废弃了,村民们大多搬进了楼房式的新窑洞。但我还是喜欢在这些已经废弃的窑洞前徘徊。这里更能让我于《兰花花》《信天游》的歌声里,感受到来自遥远历史时空的众多生命的悲欢离合和深藏其中的痛楚、欢乐、激情和眼泪。
今天,站在这里的我,正在接受一场精神的洗礼。我也因而更加真切的感受到这个浴火重生的民族,它的不容置疑的融化在血液里的感性、韧性和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