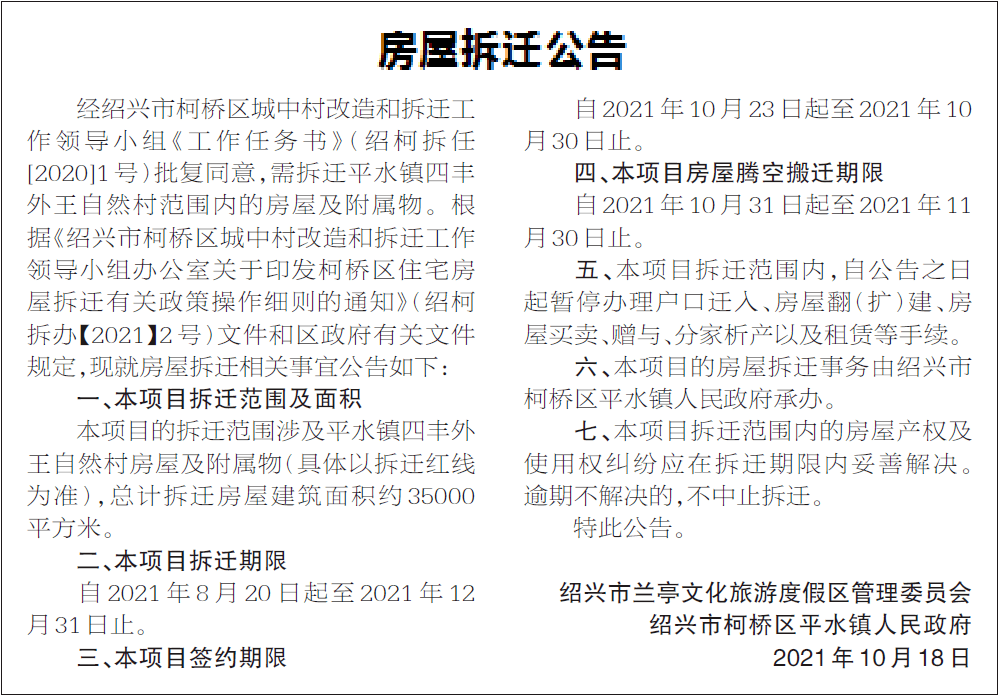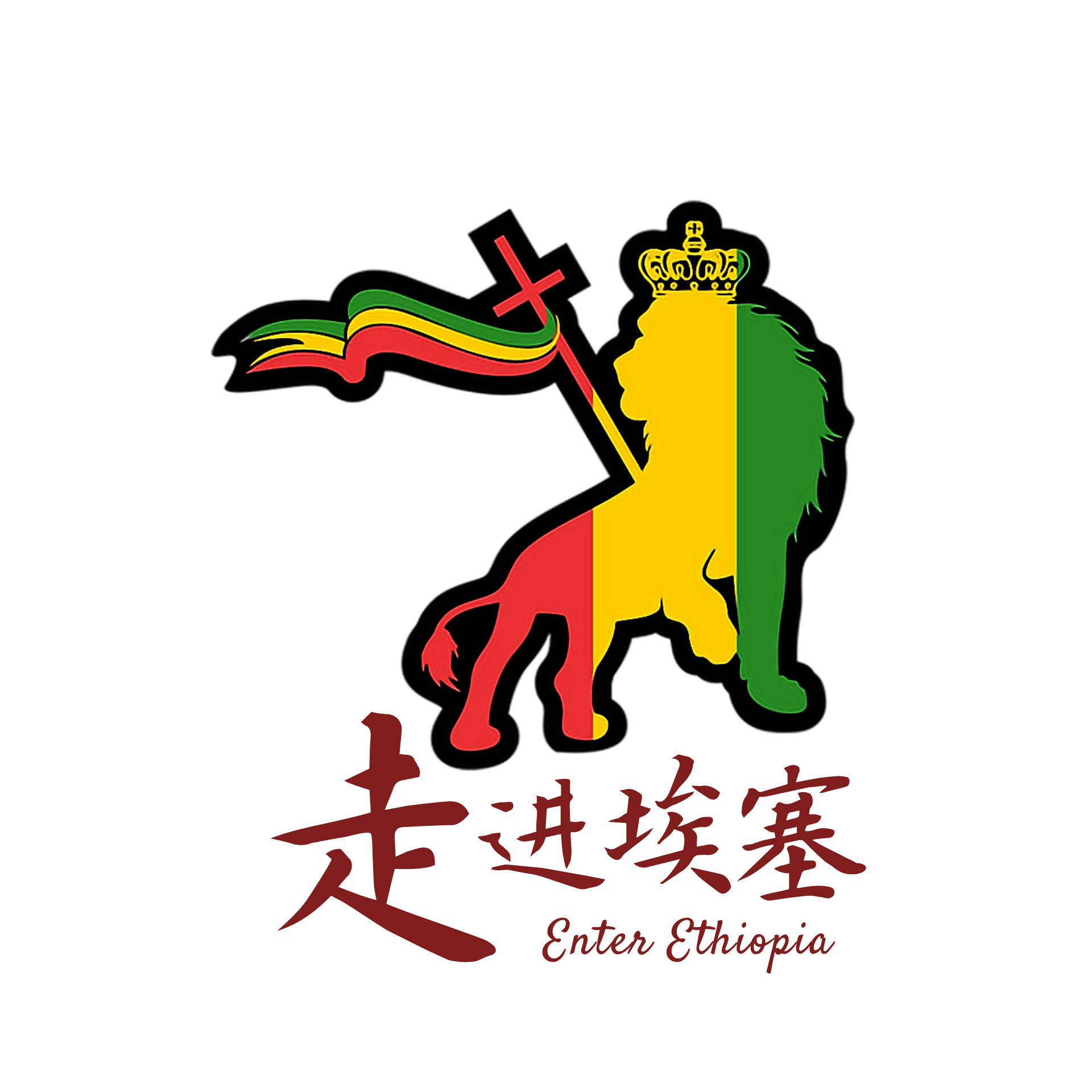太行之巅“榆社”有条浊漳河,浊漳支流有条南屯河,南屯河之畔有个不足三百人的小山村——南沟村。南沟村是我的老家,老家院子里有棵老槐树,那个院子就叫槐树院。据父亲讲,这棵槐树在他小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这棵树很高且树干很粗,五六个人都搂不住,上面的枝叶像一把大伞,遮住了半个小院。
这棵老槐树,不仅伴着儿时的我以及同龄玩伴儿学习、成长、玩耍,还成为小山村春夏秋冬的“晴雨表”。
春天来了,槐树的叶子慢慢绽放出来,不久便会有槐花抢眼,整棵树呈现一片白色,香气逼人。蜜蜂蜂拥而至,鸟儿在树上婉转鸣音,一派令人神往的景致。
夏天来了,天气炎热,邻居们都坐在老槐树下纳荫乘凉。蝉鸣不断,鸟鸣唱和。微风徐来,树枝摇曳,时隐时现。
秋天来了,槐树的叶子开始变黄,碧云天,黄叶地,在石板路上和院中铺了一个崭新的地毯。
冬天,老槐树显得那么孤独,叶子已落尽,光秃秃的像放羊的老汉取了毛巾一样,在寒风中颤抖。但只要一下雪,槐树便穿上了洁白的素衣。雪后天晴,树上雪花融化结成冰挂,不时的跌落,像沧桑的老人老泪纵横,诉说着无限的情思。
那时的孩子,男孩砸油油、滚铁环,打弹弓、跳方格;女孩子跳跳绳、丢沙包、丢手绢;那时的邻里,虽然断不了磕磕碰碰,偶尔也有争吵打架,但总能求大同存小异,化解矛盾,不管谁家有事都能一起上手帮忙。比如在老槐树下会餐时,不论谁家孩子都能端上碗去串门,然后在大槐树下一起吃。
那时上学,兄弟姐妹都是一个班——“复式班”。一至五年级都在一个教室,老师常说:“一三五自学、二四上课。”上学时劳动课多,拾麦子、拾粪、掰玉米、挖药材、上山砍柴……傍晚时,还要到打谷场上帮拉扇车,等着分口粮。
儿时的打谷场美极了,夕阳西下,一缕红光四射到场上,金黄色的玉米堆在场边,成捆的谷秆在两旁,谷穗平铺场中间,劳作的男男女女牵着牛拉碾子碾压,有的人拿着落戈打场,有的人拿着木锨子扬谷子,田园生活气息浓厚,如入仙境。
那时的我处在青春懵懂的时候,不知爱情是什么滋味,男孩起的绰号是“杨宗保”,女孩起的“穆桂英”,觉得男女相处很好就是爱。那一口水井,那条小路,以及山脚下小棚里冒出的袅袅炊烟,都是初恋的地方。青春期泛起的情愫,没有对错,只是真情;只有真情,才会有意无意偷看一下对方的日记本,有意无意地送对方一个小玩具,一旦被说穿还脸红心跳,觉得被人发现……
而这些,老槐树都是见证人。它见证了我们的童年,伴我们度过了青春年少。如今,故乡的老槐树还是老样子,还在默默地继续见证着历史更迭,但它似乎也在祝福着我们,仿佛在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王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