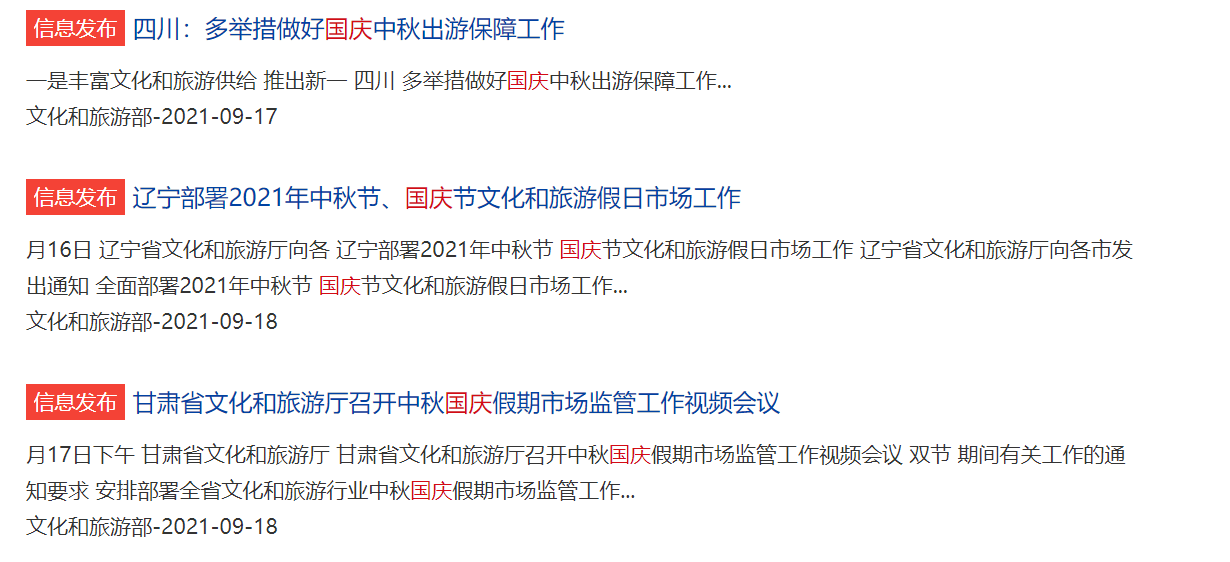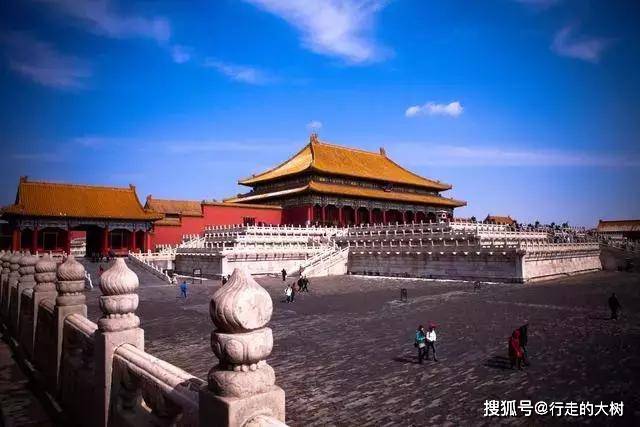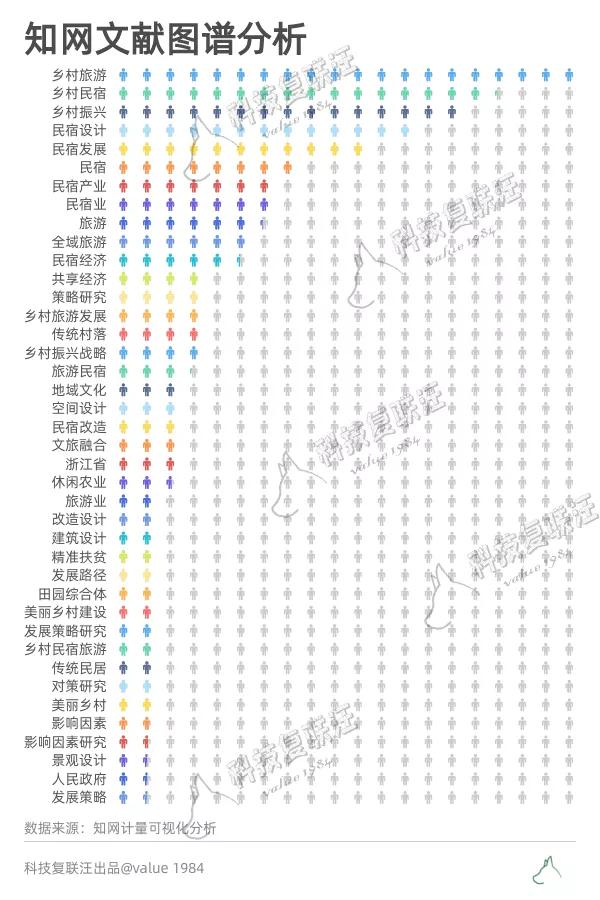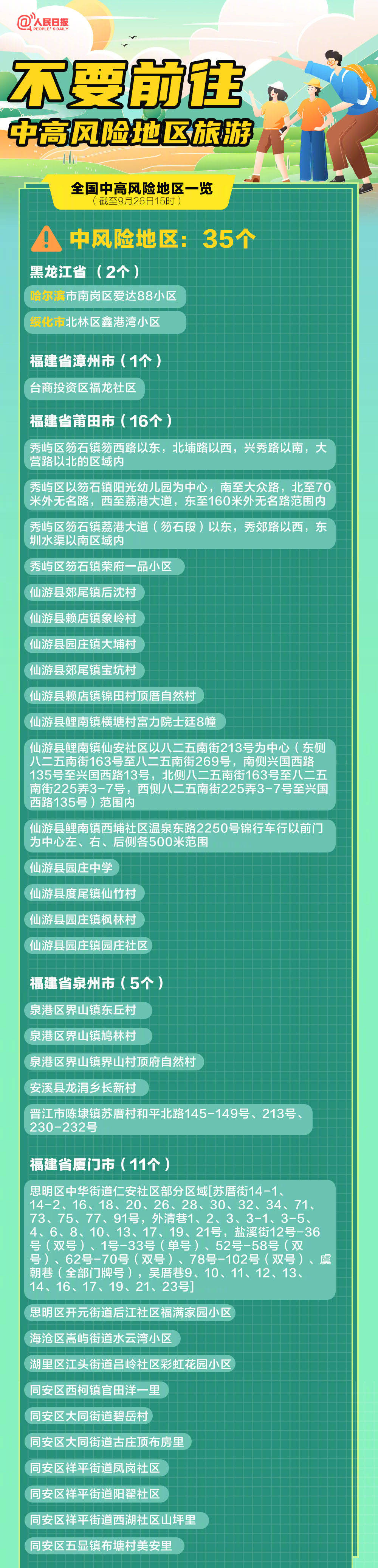我生长于皖北淮河平原,大学在南京。真正的南方和北方都很少抵达,始终在南北分界线的附近活动。曾经无数次与外地的朋友聊起安徽,我总是会说:“我家在皖北,人们印象里的安徽在皖南。”
在冬天,我来到潜山这片与我血脉相连的土地。第一天到潜山时,外面下起了初雪。雪花一片一片融入大地。潮湿的地面承载着车轮碾过的声音,一圈一圈在我耳边荡漾开去,仿佛时间的年轮在缓慢生长。时间最是无情,无论这一刻是何种境地,下一刻也会马不停蹄地到来。时间最是有情,经过时间洗礼的记忆,像从沙粒中淘出的金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闪烁。
我往往悬浮于生活,用一个沉默的视角观察生命来去。在潜山的风景里,我却长成了一棵树。
我的根系穿行于山脉,体味这一方风土人情的绝妙之处。那一颗停留于树梢的蒲公英种子,是命运走过时留下的痕迹。树梢不是适合蒲公英扎根的地方,却最得风景。在这偌大的山林里,又有谁能够瞭望山的那一端,尝试另一条路径?我走在这条狭窄的路上,却从未见过命运的真面目。那些随着风霜雨雪袭来的故事,都是人生的精彩碎片。我像一片落在潜山的雪花,就这样随风飘入山谷,将自己融在这里,体会这里。归属感有点奇妙。在安徽文化的源头之地,我抚摸王安石、黄山谷、张恨水等人留下的痕迹。这些在文学史中闪光的名字,与这个小城相得益彰。我甚至不能确定,是潜山因他们而璀璨,还是他们因潜山而动人。历史在这里停留,文化在这里枝繁叶茂,我开始相信哪怕山重水复,也会柳暗花明。
下雪的日子适合写诗。我在手机备忘录里记录了一些闪过的灵感片段,试图将它们粘合成一首诗。我看着散乱的句子,想起曾经在朋友那里读到的一句话——“吾诗未成。”我清醒地知道“吾诗未成”,同时相信最好的诗永远在下一首。
好诗不是停留在原地的地标,而是扎根于泥土的树木。随着时间的推移,树苗长成合抱之木,在一个人的任何阶段,在历史的任何阶段,都能够蔓延出繁茂的根系。我与潜山,与潜山的雪花一起生长。血脉里流动着对文字的执着,让我与山林对话。那些岩石告诉我,当一个人背负着向上的力,人生将永远处于夹缝中。我们是“历史的中间物”,是生活的两难者,是命运的同行人,幸而艺术为我们开拓土地,耕耘心灵,保留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我在《新年辞》里写:“人类开始饮水,采摘带霜的果实,尽全力保持愉快。其他的交给命运。”这是我对过去的确认与未来的理解。在潜山的日子,我常常想这些年,如同路人来了又去,如此往复。许多人迫于生活,或者远离了年轻的浪漫,脱离了写作的道路。文学是人生幸福的路径,也是一场与自己的拉锯战。那些让我感动过,振奋过,心伤过的文字,都给予我始终向上的力。我是山崖上推动滚石的西西弗斯,或许命运早已在我的脊梁上打下烙印,但在我未触及云层之前,我不打算停下。宛如潜山的初雪,哪怕落地即融,我也愿意那样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