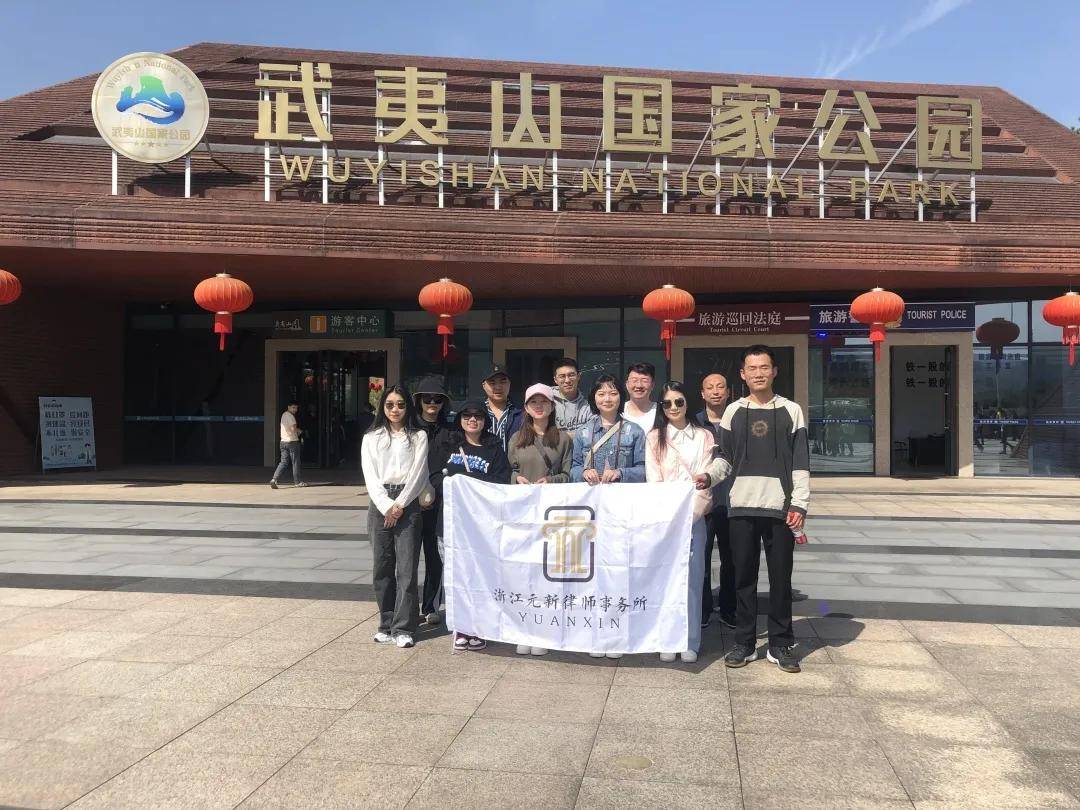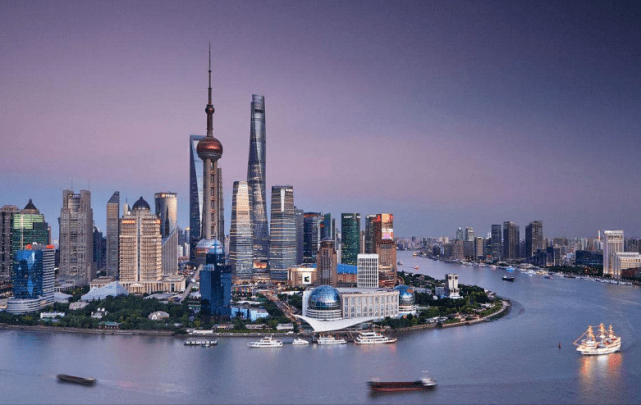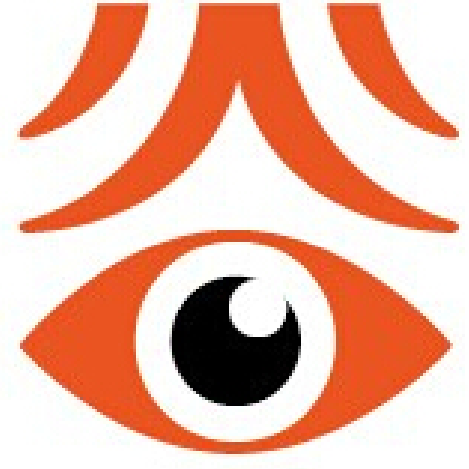叙利亚:坚韧乐观的国度
文、图/刘拓
发于2021.9.20总第1013期《中国新闻周刊》
叙利亚是我到访过的印象最深刻的国家之一,城市中苦难将尽时的勃勃生机、人民在贫穷破败中难以掩盖的高贵礼数,造就了它的独一无二。这些体验和我去叙利亚的时机有很大关系,2018年5月18日我从德黑兰飞到大马士革,那里正经历着南郊最后一场战斗。刚到城内时,我还能听到隆隆的炮声,站在高处能看到南部的灰烟。而当我11天后离开之际,大马士革终于完全解放,炮声再也不是经久不散的背景音,这一刻,当地人已经等待了五六年。
在政府控制区,我罕见地感受到对中国人的优待,即使去伊朗和巴基斯坦都没有这样明确的感觉。有些不能照相的景点,听说是中国人就可以了,在查护照的地方,看到中国护照的封面就能很快通过。叙利亚和中国是朋友,这句话听到了很多次,他们说的时候,经常还要配上手勾在一起的动作。去之前我完全没想到,中国能在民间获得这样的声望。

阿勒颇老城的街道。
我对于叙利亚现状的恐惧,在踏入大马士革古城的那一刻烟消云散,战争的阴霾从来没有直接影响到这里,这里依然是一个旅游城市,一个世俗而多元的避风港。大马士革不到5平方公里的老城内,汇集了中东几乎所有的宗教派别,他们和平共处形成的错乱感魅力无穷,穿着超短裙的女子走过高大的宣礼塔,罗马的石雕镶嵌在清真寺的墙上,而酒吧的热闹伴随着宵礼的邦克声。
在中东,除了基督徒比例甚高的黎巴嫩,叙利亚是穆斯林世界最为世俗开放的地方。大马士革中世纪的街区中,高档酒店和餐厅无处不在,一半以上的姑娘都披散着秀发,甚至穿着无袖衣服在城中穿梭。叙利亚的人均收入虽然远不及伊拉克,甚至不如埃及,但那种高档感仍在精心维持。我绝对不会想到,我住过五星级酒店最多的国家竟然是叙利亚。
大马士革人经历漫长战争后眼睛里的光芒最让人感佩,不管外国游客是否归来,正常的生活还是要过,对当下仍要坦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仍在战乱中的国家,游客的动机总是被怀疑,而在这里,人们会不断问你,我们的状况是不是挺好的,在这里玩是不是一点都不害怕?走在大街上,沿路的商铺,结伴而行的情侣,很多都会自然而然地向你说一句“Welcome to Syria”。向来赶景点如赶命的我,在大马士革的街巷中漫无目的地游荡了整整一日。

大马士革的婚礼。
倭马亚大清真寺是大马士革最重要的建筑,也是吸引我来叙利亚的最大原因。综合建筑本身的价值和历史上的重要性,大马士革清真寺在一切伊斯兰教建筑中首屈一指。大马士革有人连续居住的历史超过六千年,而清真寺所在的位置在两河文明时期就是圣庙所在,罗马人将其改造为朱庇特神庙,在清真寺的西门外还有罗马时期的柱廊,清真寺内部的很多柱子也是直接使用旧料。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神庙改建为大教堂,后来因为传说埋葬了施洗约翰的头,成为了圣约翰教堂,圣约翰的墓至今还在清真寺内。倭马亚王朝的穆斯林到来之后,于公元706年将大教堂改建成王国最重要的清真寺。这样一座辉煌历史的大寺,挺过了1300多年的光阴,至今平面格局和主体结构基本是当年的原物,才是最大的奇迹。
到达叙利亚的第一天清晨我就迫不及待到达寺外,但主麻日的清晨在打扫卫生,不让游客参观。我轻轻推开大门,晨光斜洒在平整的石铺地面上,巨大的院落一片金黄;管理人员允许我走到内廊下,穿越千年时光的金色马赛克绚烂之极。之后,在主麻礼拜的时间,在清晨、傍晚,在华灯初上后,我多次重新回到这里,看着地面上阳光和阴影的流转,看月光和灯光的辉映。那种壮美使言语显得苍白。
战前,很少有人选择去叙利亚沿海的两座城市——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游玩,但当时,这是叙利亚为数不多的安全选择。这里占多数的阿拉维派穆斯林,代表了伊斯兰世界最为世俗的一个群体,在城市东部的山村中,女性穿着随意清凉,这是即使在土耳其也只有在大城市才能看到的景象。
塔尔图斯是内战期间唯一完全没被影响的省份,像世外桃源。这里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十字军教堂,是全叙利亚当时唯一正常开放的博物馆。沿着海滩走到腓尼基时期的Amrit遗址,正是夕阳西下,在海边的店里顺便吃些小吃,穿着比基尼的女子边看球赛边喝着酒,这怎么会是叙利亚?

战后霍姆斯的废墟。
与塔尔图斯形成最鲜明对比的,是霍姆斯。霍姆斯是叙利亚在2011年较早开始抗议的城市,在后来的内战中,也遭受了最为惨烈的摧毁。匆匆路过时,我看到老城内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屋,满是水泥渣的街道两侧,都是弹痕累累的墙体。进入老城的大小路口都有军方驻守,形势紧张。
继续往北的哈马城,和霍姆斯一样也是逊尼派较为保守的地区,街头大部分女性都包裹头巾。哈马在1982年老阿萨德时期的叛乱中被严重毁坏,在此次内战中基本未被波及。这座城市以奥龙特斯河沿岸,从罗马时代沿用至今的大水车而闻名。
哈马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它的景点,而是当晚入住的青旅。我拿着2009年的《孤独星球》旅行指南推门进入了钟塔附近的一家旅馆,正在喝茶的老板当场定格,直直地盯着我,在知道我是游客后,他的手颤抖起来,眼睛里泛着泪光,用英语跟我说,已经七年了,终于有真正的外国游客再次从这个门走进来了。
当晚我和老板聊了很多,谈及十年前旅馆盛世时的光景,他指着那些空荡荡的沙发说,当时,有美国人在这里,法国人在这里,大家谈天说地,聊着第二天包车的事宜。他总是梦想这一幕能再次出现。他甚至立刻约了当地电视台想采访我,告诉大家又有游客来了,可惜因为我时间太紧,最终作罢。
叙利亚人的坚韧乐观令我感动,然而毕竟七年间失去的太多,回望起来仍不免悲伤。大马士革东北的Mar Musa修道院的经历,就是这七年的缩影。修道院建立于11世纪,目前还保留大量初建时期的壁画。由于修道院地处荒漠,风景遗世独立,一度成为了叙利亚的网红景点,不光不需要门票,而且食宿全部免费,来此体验的游客人满为患。内战开始后,修道院一度被极端组织占领,1983年曾修复这座修道院的意大利人保罗也被抓走,生死未卜。

Amrit遗址。
我去之前,很少有关于这座修道院的现状报道。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来到山下,爬到一半时,教堂里的一位修士远远发现我是外国人,便回去又喊了几个人出来,向我挥手大叫,到那里时点心和饮料都已经准备好了。繁华散尽,寺院中只剩下唯一一位女性,还有几位男性帮工。她平静地讲述了七年间在寺院发生的事情,短短半小时,我却仿佛看了一部史诗电影。正是因为她的坚守,修道院的道统没有中断,并且在极端组织到来之际,她积极周旋,让壁画得以保全。她翻开叙利亚文的圣经轻诵赞歌,在这没有信号的空谷中,恍如穿越到千年前。
选择这个时间点去叙利亚,事后看来很有意义,除了目睹当地人在战争结束时再次看到外国游客的复杂心态,还能对战后文化遗产的状况进行记录,这在阿勒颇最为明显。比我稍晚去的朋友,只看到了重建工作开始后建筑笼罩上脚手架的模样。
叙利亚政府的恢复工作很快,在解放仅一年半之后,城内的气氛已非常松弛,几乎没有军队维持秩序。正因此,我可以在废墟间爬上爬下,找各种角度进行拍摄。曾经的经学院、清真寺都大门敞开,阳光穿过弹孔,在熏黑的室内投下光柱,洒在柯林斯的柱头、马穆鲁克黑红相间的石墙,以及圣墓绣满经文的盖毯上,时间好像静止一般。但这绝不是阿勒颇的全部,到了晚上,废墟就不存在了。人们聚集在幸存的建筑里,纵酒狂欢,直到半夜一点,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城市。
我所到之处,都会爆发一阵又一阵欢呼,听到此起彼伏的Welcome to Aleppo的喊叫。城堡下面写着Believe in Aleppo的大字,在这魔幻的夜晚让我眼眶湿润。相比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生活态度确实让人相信,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