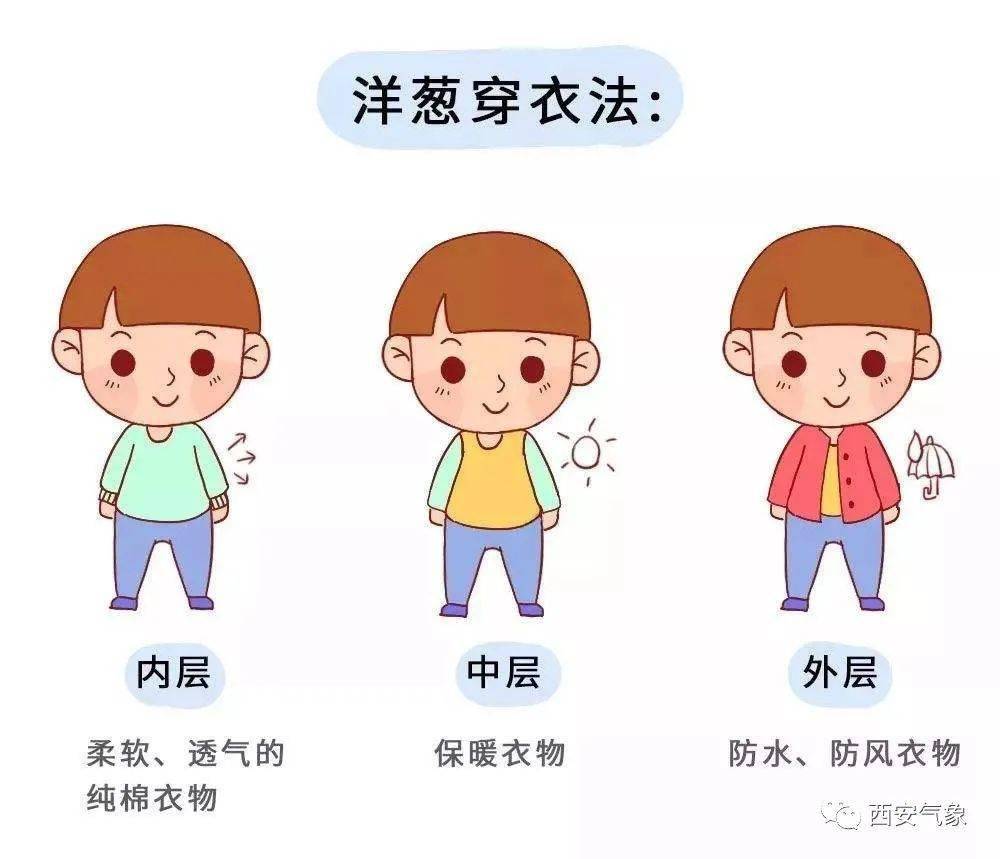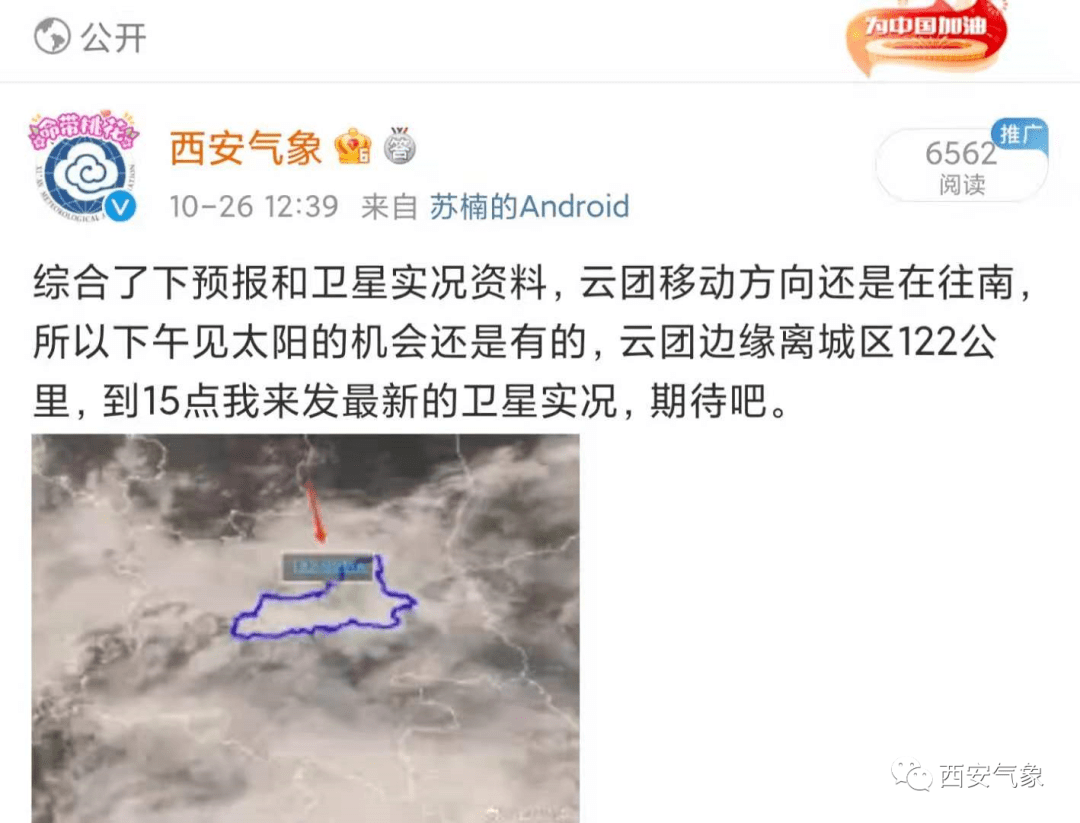汩汩而出的山泉水汇聚成一条小河,弯弯曲曲从门前绕过,屋后的小山坡驯服地俯卧着。野生的柿子树太高,枝条又脆,挂满了柿果无人摘,喂饱了叽叽喳喳的小鸟,掉落到地上来,浓浆浆的一滩,肥了各种爬虫飞虫,嗡嗡不止。草窠深处总有窸窸窣窣的声响,不知是藏着蛇还是蜥蜴,人怕它们,它们更怕人,隐踪潜迹,两不相扰。这是我曾经服务过的联系村,它有一个非常通俗的名字——洪家湾。这里的洪姓族人过去可是玉屏的官宦世家,名流辈出,所谓“洪半城,夏半街”的说法由来有自,足见曾经的洪姓声势之大。
我在这里驻村,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服务对象与朋友难解难分。这座地处侗族自治县境内的村寨,严格意义上来讲,恐怕还算不上侗寨,因为根据族谱记载,这里的洪姓人家是明朝洪武年间从江南迁来的“客人”,不过客居几百年,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主人。再加上通婚和文化融合的因素,客人成为了新的土著,新的土著又遇上新的客人,几百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搞人口普查的时候,如果不细看户籍资料,光是口头询问他们的民族成分,很多人都已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侗族还是汉族了。汉族的节日要过,侗族的风俗也不落下,社饭同样鲜香,腊肉同样肥厚,碱粑油茶一样的在火塘火铺上慢慢煨着。在这里,民族身份也就是证件上的一个符号罢了,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具备识别功能。
诗人的理想,是“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的村民们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前两条,可光是喂马、劈柴,哪有钱去周游世界呢?看来为了实现真正的诗意栖居,还必须得走出贫困。一条穿村过寨的弯弯小河就是这个村子优质的自然资源,因为下游还有一个村寨名叫混寨,所以这条河官方名称叫做“混寨河”。为了这个名字,洪家湾的村民们内心是有波澜的,明明是洪家湾的河,为什么要叫混寨河?好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并不需要对这条河的官名说得那么精准,通常都是“河”“沟”等字一笔带过了,就好像这里乡里乡亲之间很少称呼大名一样,支书叫“宝宝”,村主任呢,大家都管他叫“老黑”,日久成习,要是突然有人叫声大名还真有些不习惯了。
玉屏城北过红花坪爬上卓岭后,地势高平,山丘田坝守望相连,山不甚高,田不甚广,适合精耕细作,不足之处是不少地方过去非常缺水,干旱成为当地农业一个传统的威胁。现在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这种威胁缓解了不少,但是洪家湾、混寨一带因为长流着这条四季不竭的清泉,几百年来都是让人垂青羡慕的好地方。这条河不仅终年不竭,且无论冬夏,经常能看到汩汩的水泡从河底冒上来。我在河里捞过鱼虾,摸过螃蟹,甚至还捉到过乌龟,村寨留给我头脑中的记忆始终与这汪流水纠缠不清。岸边分布着多口水井,其中一口“乌龟井”,据民间传说还是仙人指引开凿的,村民砌成方塘,塘内水清如无物,只见细密的水泡摇曳着柔丝一般的水草,这才暴露出水的身影。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起朱熹那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么好的水,日夜不息地白白溜走,或者仅仅是自斟自饮,洗衣洗菜,岂不可惜?该村建起了一座桶装山泉水生产加工企业,千百年来泽被一方的甘露,如今已满城销售,滋润起全县人民的口舌胃肠。
记得一次走访贫困户,我来到“五保户”炳大伯家。大伯80多岁,一人独居,身体却很硬朗,原来歪东倒西的老木屋已被拆除,重建了一幢砖瓦房,只有两间,一间做伙房,一间做卧室,旁边搭了卫生厕所,独居老汉,已绰绰有余了。大伯非常热情,硬要留我吃饭,简直就是关上门来不让走的架势;我无奈,只好坐下来预备着陪老人家小酌两杯。老人手脚麻利,灶上的活我可一点都插不上手。火塘里的三脚架上支起一顶黑油油的老鼎罐,黢黑的一大坨腊肉在水中上下浮沉翻滚。我有些后悔了,不是担心多吃多占了老人的腊肉——火塘上方的火炕挂得跟肉林似的,别人不来帮帮忙,老汉一个人哪里消受得完?我不安的原因是不知道老汉能将这坨乌漆墨黑的东西弄出个什么味道,我能否吃得下。
其实是我多虑了。过去在家里我是俗话中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虽然爱吃腊肉,可从来不知道腊肉是如何切片弄熟装盘上桌的,再加上肉类食品在烹调处置之前往往不太美观,所以引起了我的担心。老人时不时拿根筷子戳一戳鼎罐中的腊肉,试探肉质的松软度,燎得差不多可以了,便将肉夹出来切片。换一口大铁锅支上,肉片下锅在油中吱吱地炸到微微卷起来,再加水。老人从门前菜地里现采几蔸蔬菜,洗净掰成一段一段,随手撒进锅里,再弄点干豆腐一起煮,这“农家一锅鲜”在自然而然的慢煮慢炖中渐渐呈现出惹人垂涎的魅力来。我的顾虑完全打消了,帮老人斟上米酒,腊肉下酒,青菜解腻,再配上酸爽的糟辣椒,这简单的食物,随意的烹调,烤出一点焦煳气息的米酒,真足以让人“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边喝酒边跟老人摆家常,我随口问道,某某村也有个洪家村民组,跟你们是不是一支啊?老人呷一口酒,大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我们可不是一支,那边的洪家,原本是二马“冯”,读音跟洪相像,因为我们洪家势力大,他们便冒了洪姓,别人不清楚,我们自己可是知道的。我们是水神共工的后人,祖宗保佑,那条河沟虽然不大,却从来流不干,就像人身上的血脉一样,只要人活着,就永远不会断绝……
老人酒兴高,谈兴浓,我随口一问,他便拉拉杂杂说一大堆。忽然听到屋外老母鸡叫唤,他才一拍大腿,恍然大悟似地跑出去,不一会便捡回两个鸡蛋来,兴奋地说:“酒慢点喝,我再加个菜来。”老人干了一辈子农活,力气大得很,我拦也拦不住。两个鸡蛋下锅,也是锅铲随意捞几下,蛋香便扑鼻而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这么馋,吃嘛嘛香,看来我的肠胃虽然一直被过度加工的食物驾驭着,口舌却仍然执迷不悟地眷恋着原乡本土的这些滋味,自在、自由、自然的滋味。
从老人家出来,时间尚早,正是城里人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寂寞的乡村,却已沉入梦中。小虫子的夜生活,现在也才开始,它们伴着我微微踉跄的步伐,争相让我品评谁才是这村中最痴情的歌者。我不甘示弱,也高吟一篇古风,不让虫类独占了这浩渺无边的夜的吟坛: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作者简介
杨清博,湖南新晃人,现居贵州玉屏,供职于玉屏自治县文联。
文/杨清博
文字编辑/邱奕
视觉/实习生 沈松钦
编审/李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