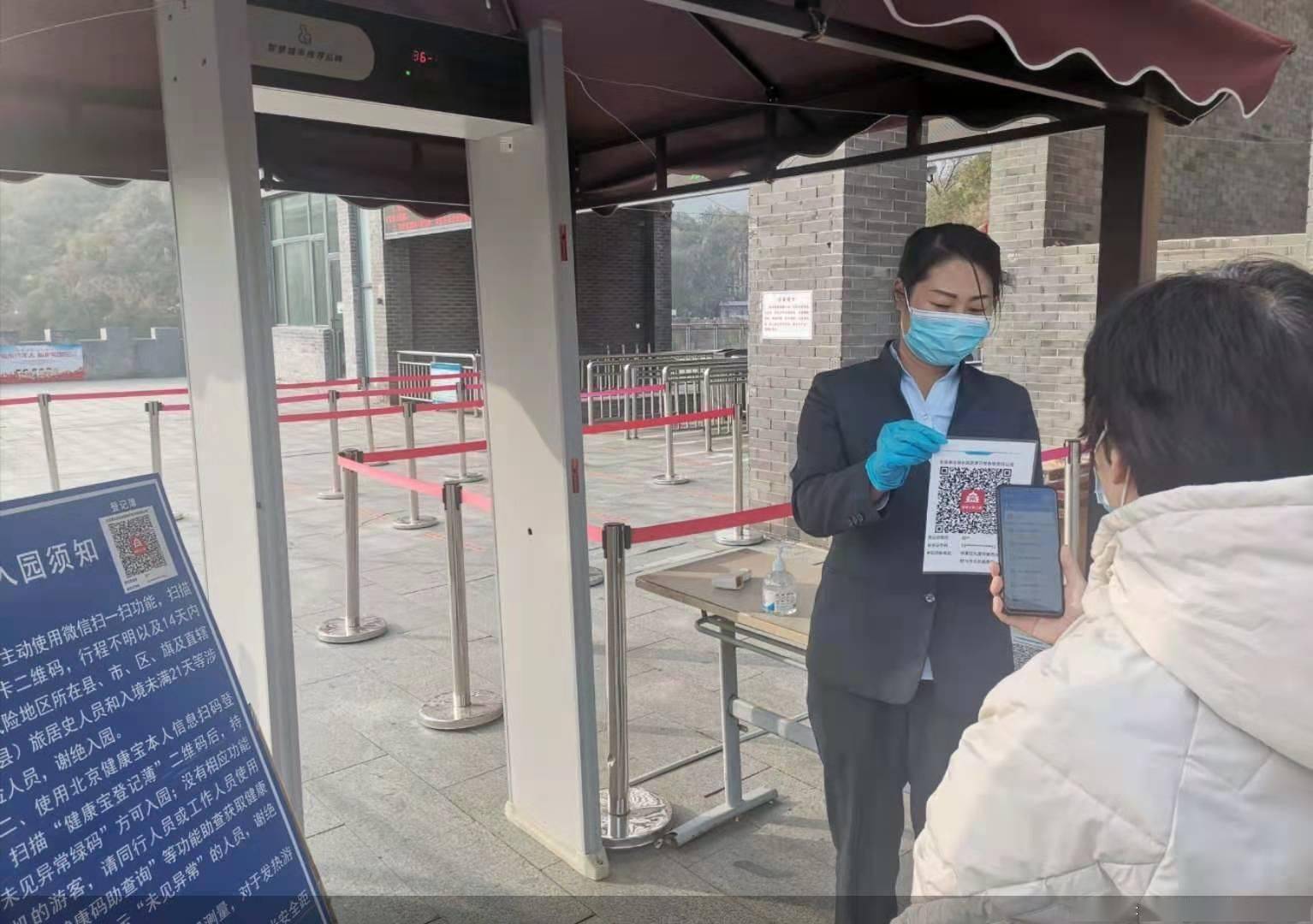十年啊十年,终于盼来了四川盆地的又一场雪。四川盆地,名符其实,四面的高山,遮挡住了西伯利亚的寒流。雪,在四川人的心中难得一见。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下过一场雪,今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冬天。古人说,恍如隔世,这难得一见的雪,真让人产生恍如隔世的感觉。
雪花在天上飞扬。
学生们不顾上课的铃声已经打响,纷纷跑出教室,在雪地里欢呼跳跃。雪花飘在脸上,雪花飞进领口,雪花融进了孩子们多少快乐的欢笑。
啊,雪花,你让多少人忆起了远去的童年。
啊,雪花,你让多少人生出了诗情画意!
望着漫天飘舞的雪花,热泪盈满了我的眼眶。往事,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刹那间,闯开我久闭的心扉,闯入我静如止水的心底,搅起我心海的浪花,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息。
三十二年前,我刚六岁。那年冬天,也是一个雪花纷飞的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屋外,满天飞雪。破败的墙缝中,不时吹来丝丝寒风,冻得我浑身颤栗。
生产队里死了一头猪。吃晚饭时,队长通知,每家每户去一个人分猪肉。父亲收工回来,连晚饭也没有吃,就匆匆赶往生产队的猪场里。去晚了,我们家的那一份,就不知煮到了谁家的砂锅里。
“妈妈,队里死了那头猪……那头猪有多大?”我使劲咽着口水,想到香喷喷的猪肉,强忍了半年的馋虫,迫不及待地从喉管里爬了出来。
“有多大?有60斤重!”
“妈妈,60斤 ,60斤重是多重呀?”我搞不清楚60斤的具体概念,但在我的想象中,这不会是一头小猪。我更加兴奋,迫不及待地问道,“妈妈,我们能分好多肉?”
“能分好多肉?能分一斤半肉。”妈妈没好气地答道。
一斤半肉,一斤半肉会是多少?
在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它的份量。我只是隐隐约约地希望,这瘟死了的猪能够大些,大些,再大些,这一斤半肉能够多些,多些,再多些,好让我饱餐一顿,好让我解一解半年多来对肉的饥渴,好让我喉管爬动的馋虫能够小些,小些,再小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好像没有一次机会,让我痛痛快快地吃过一顿猪肉,让我舒舒服服地打过一次牙祭。
屋外的北风越叫越凶,屋外的雪花越飞越大。
我已经撑不住自己的上眼皮,我的头已经在墙上“咚咚咚”地撞过无数次。但我仍然不愿上床睡觉。
“孩子,上床睡吧!”妈妈摇醒我。
“不,我要等爸爸!”我睁开眼,嘟哝哝说道,随即又眯上了眼。
“汪汪汪——”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了阿黄的叫声。我猛地惊醒过来,“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我跳起来,冲到门口,飞快地拉开门。
“哗!——”凶猛的北风夹着雪花铺天盖地地扑来。
“爸爸——”我冲过去,抱住爸爸的大腿。
“孩子!”爸爸伸手拉住我,“快,快进屋去!”
昏暗的煤油灯下,爸爸一手拉着我,一手高举着一块沾满血丝的猪肉。
“爸爸,我要吃肉!我要吃肉!”我双手使劲摇着爸爸的腿,高兴而急切地呼喊着。
“爸爸,我要吃肉!我要吃肉!”不知何时,睡着了的弟弟,也爬起来,加入到欢呼的行列。
“爸爸,肉肉!爸爸,肉肉!”也不知何时,仅仅一岁半的小妹也从床上爬起来,冲着爸爸手舞足蹈地欢叫着。
“孩子他爸!”妈妈拿起笤帚走过去,轻轻拍打着爸爸身上的积雪。泪水,大滴大滴地从妈妈眼中奔涌而出。
“看你——”爸爸伸出长满老茧的手,轻轻抹去妈妈脸上的泪珠,“快……快……快去给我倒杯酒来!”爸爸放下手里紧紧攥着的猪肉,浑身颤抖着。
“好!好!”妈妈旋即转过身去,拿出一个粗碗,倒了小半碗酒,递到爸爸手里。
爸爸抖抖索索接过碗,送到唇边,一饮而尽。
“好舒服啊——!”良久,爸爸放下碗,长长地叹息一声。
“爸爸!”
“爸爸!”
“孩子!”爸爸长满老茧的双手,轻轻抚摸着我和弟弟的头。
“孩子他妈,快生火,把肉煮给孩子们吃吧!”爸爸回过身去故意高声大气地喊道。
“唔——”妈妈答应着,带着一丝两丝的哭音。泪水在妈妈脸上静静地滑落。
窗外,北风仍在呼啸,雪花仍在飘飞,孩子们仍在欢叫。
如今,三十二年已经过去,母亲也在两年前不幸患病逝世。但是三十二年前的那场风雪,三十二年前的那天穿地漏的夹壁屋,三十二年前那顶着风雪归来的父亲的形象,三十二年前那父亲手举着腥红色猪肉的情景,三十二年前那母亲脸颊上滑落的颗颗晶莹的泪珠,却深深地铭刻在了我饱经忧患的心灵里,虽遍历人生风雪,虽阅尽沧海桑田,也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