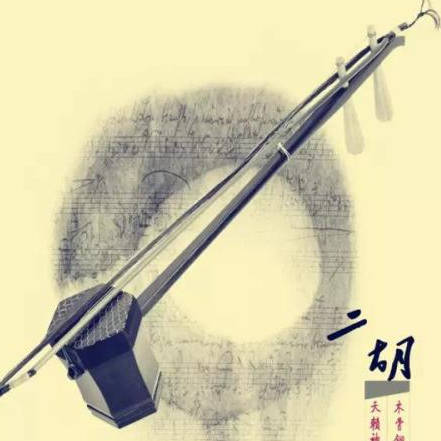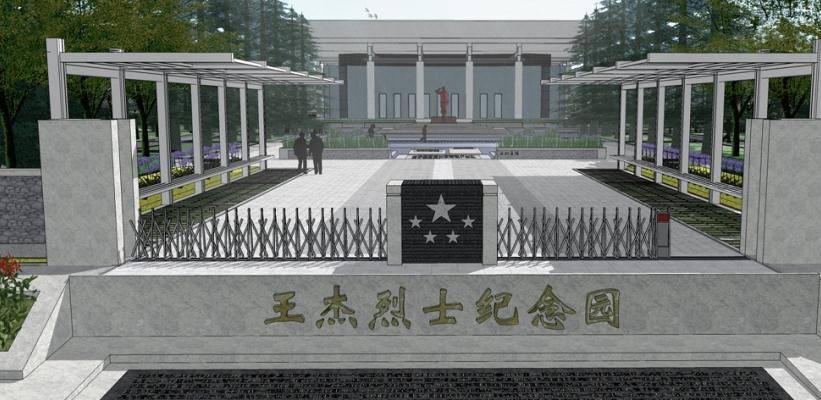□刘荒田[美国]
“其间可记者几何也?”(里面值得记下来的有多少呢),袁枚记录一次极为畅快的游玩之后这般发出感慨。那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中的一天,“佳节,胜境,四方之名流”,三者居然凑到一块,“不偶然之事偶然得之”,堪称极乐。
那天逢花好月圆的中秋,袁枚所拥有的随园,新近由姑苏人唐眉岑和儿子主理厨政。唐大厨技痒难耐,对主人说,好东西只做给您一个人吃,可惜呢,多找些客人吧!袁枚说,先作准备好了。他料定今天必有“不速客”。果然,霍进士驾到,不一会儿,又来了诗人尤贡父和陈古渔。客人说,我们都不是本地人,金陵名胜还没领略过。于是,主人领着三位客人外出观光去。这里,大厨在旁也一个劲怂恿大家出游,乃是为美食埋伏笔——他们游空了肚子,才有大快朵颐的胃口。一游就是大半天,经小龙窝,双峰夹长溪,桃麻铺芬,登临大仓山,从谢公墩俯瞰全城。复从峨嵋岭登永庆寺亭,那已是日落时分。四位雅人一路谈笑,吟咏,回到随园,月光大明。菜式绝佳,尤其是主菜“蒸猪头”,肉烂如泥,还有美酒。席间分配八个题目,让客人作诗。
如此美好的一日,怎么不教主人袁枚感叹:“嘻,余过来五十三中秋矣。幼时不能记,长大后无可记,今以一彘首故,得以群贤披烟云,辨古迹,遂历历然若真可记者。”这个中秋,全过程有的是材料、感怀,自然有“记”的兴致与价值,问题是:活到五十三岁才捞到一次,不得不“执笔而悲”。
是啊,一辈子,“可记”的有多少呢?五十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二十郎当岁,在乡间当民办教师,下决心当作家。元旦那一天,横下心,去文具店买了一本最昂贵的硬皮日记簿,花了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从此每天写日记,是为练笔。一个月后,我走进他的卧室,他把日记簿打开给我看,除了第一页写了三百字的《新年寄语》,以后,每一天只写两个字:“无事”。我说,“无事”还写个屁?他苦笑着说,是啊。从此簿子束之高阁。
如果只有生离死别,惊天动地的爱,遇到大人物,再不济也得救火,打架,这些才够格算“事”,那么,我们平平淡淡地度过的每一天,确实“无事”。换一个时髦点的标准——钱能摆平的都不是事。排除贿赂以枉法一类,钱无非用于买东西,买服务。然而,这不是大幸吗?难道为了记一页惊心动魄的日记去制造灾祸?一如家里的感冒药快过期,你无意招来鼻塞咳嗽。连袁枚也无法天天来个“平地起风波”,我们没钱雇请厨师,没有待客的随园,极普通的老百姓,只能努力从平常日子发现“可记者”了。
再想下去,“可记”何等可贵。人人明白,身外物尤其是随身可带一类,随着年龄的递增,要么变为累赘,要么变为不可靠。往昔之于今日之我,唯一的联系,最终可能仅仅是记忆,那还在思维未衰退为空白之前。形诸笔端,直接的功用就是保留、强化以及启动私人记忆。一位先前以研究古典诗词为业的博导,晚年视力大减,无法读书,便以回忆经典为消遣,曼声吟哦,沉浸其中。亏得他年轻时下过背的笨功夫。
是啊,记忆就是具有终极意义的财富,很可能是唯一的依凭。何况,一桩“可记者”,如袁枚的这个中秋,在记忆里尽可反复无数次,堪称最惠而不费的循环再造。
万一记忆也完蛋怎么办?上世纪六十年代纽约芭蕾舞团的舞者马塔·冈萨雷斯,晚年患严重失忆症,只能蜷缩在轮椅上。一次,护工给她播放《天鹅湖》,本来呆若木鸡,双手竟灵巧地随音乐挥动,当年舞台上的“天鹅”重现。这就是记忆对人的最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