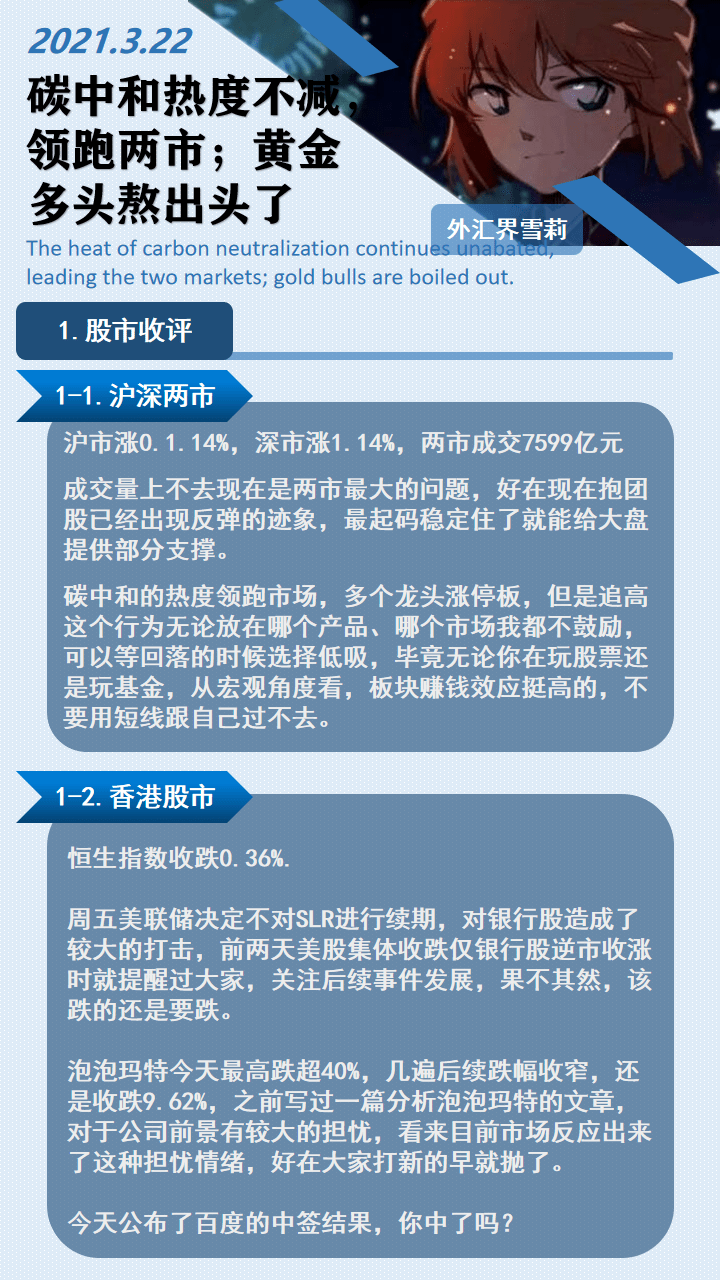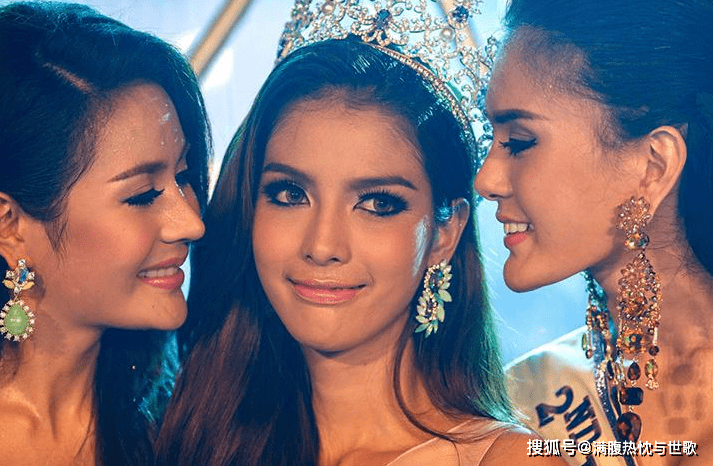题图 /Jim Holland
论游泳
这国家的河流甜蜜
如游吟诗人的歌,
沉重的夕阳在黄色的
大篷车上向西漂游。
小小的乡村教堂
保持着它织物般的寂静
那么精致而古老,似乎吹口气
就会将它撕破。
我爱在海里游泳,大海
不停地自语
以一种浪游人的单调
他不再记起
在路上到底已有多长时日。
游泳一如祈祷:
手掌合起又分开,
合起又分开,
几乎没有终止。
作者 / [波兰]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翻译 / 李以亮
O pływaniu
Rzeki tego kraju są słodkie
jak śpiew Trubadurów,
ciężkie słońce wędruje na zachód
na żółtych wozach cyrkowych.
W małych wiejskich kościołach
objawia się tkanina ciszy tak wąskiej
i tak starożytnej, że nawet oddech
potrafi ją rozerwać.
Lubię pływać w morzu, które wciąż
coś mówi do siebie
monotonnym głosem wędrowcy,
co już nie pamięta
od jak dawna jest w podróży.
Pływanie jest jak modlitwa:
dłonie łączą się i rozdzielają,
łączą i rozdzielają,
nieomal bez końca.
Adam Zagajewski
On Swimming
The rivers of this country are sweet
as a troubadour’s song,
the heavy sun wanders westward
on yellow circus wagons.
Little village churches
hold a fabric of silence so fine
and old that even a breath
could tear it.
I love to swim in the sea, which keeps
talking to itself
in the monotone of a vagabond
who no longer recalls
exactly how long he’s been on the road.
Swimming is like a prayer:
palms join and part,
join and part, almost without end.
Adam Zagajewski
Translated by Clare Cavanagh and Renata Gorczynski, Benjamin Ivry, and C. K. Williams
“游泳一如祈祷:手掌合起又分开,合起又分开,几乎没有终止。”这首诗的最后几句,闪现出某种“顿悟”的特质。或许你的语言抓不到,但是你的感知感受到了。
而“几乎没有终止”,则让我联想起扎加耶夫斯基的《永无止境》的开头:“在死亡中我们也将生活,/只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优雅地,柔和地,/溶进音乐……”
而在其名为《遗作》的诗中,他这样写:“有一次我们听舒伯特的遗作,/弦乐五重奏里绝望的宣告,/连绵不断,一心一意,几无止境……”
扎加耶夫斯基似乎痴迷于这种“无止境”的状态,足以超越时间,穿越生死。它就像一个不断重复的祈祷的姿势,永远向前,不论是溶进音乐,还是游向大海。
《论游泳》是这样一首诗,它没有确切指向。你反复阅读,越读越觉得难以把握,像一个在大海里游泳的人,游得越远越抓不到哪怕一根芦苇,无所凭依。但越是如此,你越觉得其实抓住了什么,你说不出但是却感受到的一个点,它通向了对“神性”的顿悟。
这大概就是扎加耶夫斯基所说的纯诗。他曾在一篇访谈中这样谈论纯诗:我所谓的“纯诗”指的是一首诗里非常成功的几行。它提供一个喜悦的时刻。读者和诗人通过这些纯诗行,同等地拥抱这种喜悦。
3月21日,世界诗歌日的这天,扎加耶夫斯基去世。世界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诗人。
扎加耶夫斯基是继米沃什、辛波斯卡、赫伯特之后最重要的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作为前述诗人的后辈,出生成长于“二战”之后的波兰,政治环境所带来的沉闷与黑暗,迫使他在读大学期间即开启以诗歌表达反抗与愤怒的创作之路,成为波兰“新浪潮”诗歌运动的主将。后因为波兰进一步严厉的政治约束,诗人开始半生的流亡,在欧洲与美国之间旅行和创作。
这样一位从反抗话语起步的诗人,从未停滞。伴随着步履不停的出走,他摆脱了气闷而狭窄的祖国,来到更加广阔的世界,得以用更延展的视野,更深沉的视角,来观照更复杂的人类精神图景。通过自己一系列惊艳的创作,他完成了诗人的成熟。
扎加耶夫斯基曾引用莎士比亚的“成熟就是一切”来注解自己写作的历程,“我认为自己年轻时作出的政治承诺是好的,也许可以说是必要的,但不是可以永远支撑我的东西。”在2002年,他又返回自己当年学习的城市,波兰的文化中心克拉科夫定居,直到去世。
扎加耶夫斯基最被人熟知的作品应该是《尝试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读睡曾经在2013年推荐过这首诗。这首诗的写作于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前一年,但因为“911事件”导致“世界的残缺”而被强行联系在一起。
这就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残缺的世界也要尝试去赞美?扎加耶夫斯基早年生活的波兰城市克拉科夫距离奥斯维辛咫尺之遥,阿多诺的那句名言再次响彻读者耳畔: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有人就向扎加耶夫斯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奥斯维辛之后为什么还要写诗,并且还要去“赞美”。
扎加耶夫斯基认为,阿多诺的意思并非反对写诗,而是说,奥斯维辛之后,诗人下笔的时候应该更加审慎。另一方面,诗歌需要处理的世界,不仅仅只有奥斯维辛,它还要求诗人去关注其他“愉悦”与“游戏”的向度,而这些向度同样不能被奥斯维辛所剥夺。
正是因为扎加耶夫斯基这种超越性的创作态度,决定了他的诗歌充满了包容、仁慈乃至神性与预言的性质。正如苏珊·桑塔格所指出的:“虽然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这里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总会敲响。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挡。”
荐诗/ 流马
扎 氏 在 读 睡
2020
《脸》
2018
《大提琴》
2017
《给新政府提几条建议》
2015
《房间——给德里克·沃尔科特》
2014
《中国诗》
2013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第2933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