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Yuval Ben-Ami 故乡与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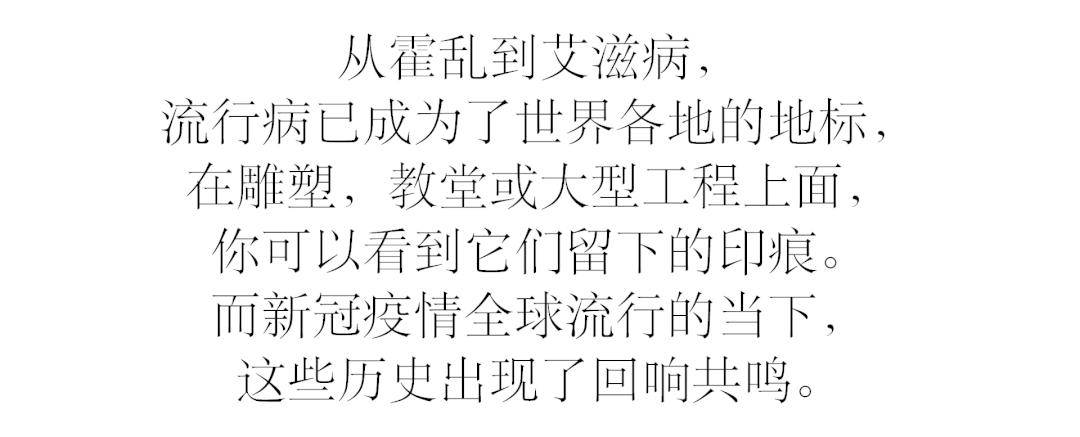
在宽度刚好可以容纳雪铁龙的砾石路肩上,我停了车,让我3岁的女儿走出车门。我劝她和我一起穿过普罗旺斯西部的低矮灌木丛,去看看近200年前席卷该地区的一场流行病留下的痕迹。
很快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块标志牌:“马赛运河。禁止靠近。水深危险。”再过去,一条水道从山坡上的一个拱形开口中涌出。绕过小山,水又涌了出来,没进下一个山坡。在隧道口附近,我们分食了一颗小柑橘。女儿对着躲在岩石深处的鸟儿鸣叫,而我则在沉思,疾病和人类文明在景观上印下的痕迹。

当霍乱在19世纪30年代肆虐马赛时,该市市长承诺要解决这一问题。随后几年,马赛运河建成了,为该地区带来了清洁的水源。
运河在法国地中海地区并不罕见,但它们一般涌流于山谷低凹处,而不是悬于其上。它们也不会穿过那么多条隧道。几周前,这条运河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们正从乡下的家抄近路去马赛机场。经过研究,我知晓了这桩掺杂着苦难与胜利的往事。
19世纪30年代,当霍乱肆虐马赛时,该市市长承诺要“不惜一切代价”解决这个问题。市民们需要干净的水,运河的建造者们为此克服了艰险的地形,给我们留下了长达50英里的奇迹。在当前这个可怕的时刻,他们的壮举引起了共鸣,同时又显得不可思议。
过去的流行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痕迹,包括纪念碑、礼拜场所、医院、防御工事、墓地和一些宏大的建筑工程。而在多使用一次性口罩和临时医院的现今,我很难想象,新冠肺炎病毒会在地球表面留下什么样的持久痕迹。
“我们对流行病的历史记忆很短,这很正常,”负责印度洋留尼汪岛历史检疫站的杰西卡·普拉伊(Jessica Play)说。“这是关于死亡和痛苦的记忆,是我们不愿去回想的事情。”
如今,全球困境期间,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地标古迹正在重获其意义。以下是其中的一些。

鼠疫柱矗立于维也纳格拉本大街的中央。顶端是金光灿灿的圣三位一体像,下方为9位天使立于云端。维也纳的鼠疫柱是该类纪念柱的一个典范。它纪念的是1679年那场黑死病的爆发,当年它在奥地利导致了大约1.2万人死亡。

去年3月新冠病毒第一波大爆发期间,维也纳的居民们在(纪念17世纪末死于鼠疫受难者的)鼠疫柱前点燃蜡烛.
自2014年以来,维也纳大学的学生兼工作人员托马斯·哈比奇(Thomas Harbich)每天都会在推特上发布关于这座城市的琐事,其中包括几条与纪念碑及其周围环境有关的推文。去年,他见证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座纪念碑重获新生,在新冠疫情中得以被重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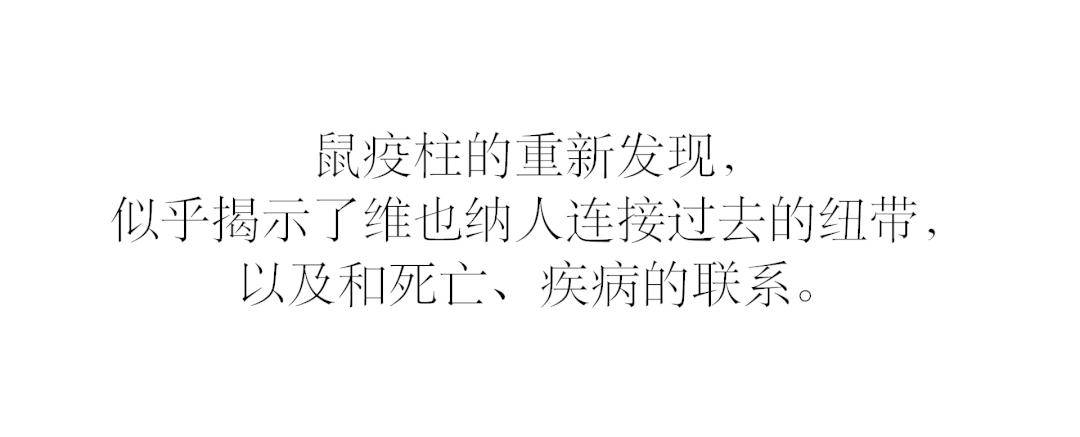
哈比奇说,“在疫情首次隔离期间,人们像黑死病爆发后那样使用它,使用它本来的用途。”他指出,鼠疫柱的重新发现,似乎揭示了维也纳人连接过去的纽带,以及和死亡、疾病的联系。
“人们对完全未知的事物做出的反应,可能会更具有宗教色彩,所以他们在鼠疫柱旁放置了蜡烛和写有祷文的小纸条。它看起来很特别,因为当时街道上完全是空的,而鼠疫柱在中间闪闪发光。”

医院的历史颇具讽刺意味。在西方世界,致命疾病所带来的灾难,使医院成为了希望之地。
“大多数医疗保健场所的所在地本来就是家,”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研究医疗保健史的历史学家简·史蒂文斯·克劳肖(Jane Stevens Crawshaw)说。她列举了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即有的一些长期护理机构,其中包括为孤儿和战争致残者提供的机构。

荷兰莱顿的瘟疫屋,自然生物多样性中心.
她说,这些机构的数量仍在增多,“但为了应对前现代时期的流行病(瘟疫和水痘),旨在为这些特定疾病提供专门治疗的医院开始发展起来。”
部分流行病直接催生了一些医院的建立。1710年,柏林成立了一家机构,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瘟疫,后来其演变成为了一家重要的医疗中心Charité。而其它流行病医院则已荒废不用了。澳大利亚悉尼爆发的猩红热,催生出了亨利王子医院(现为医疗保健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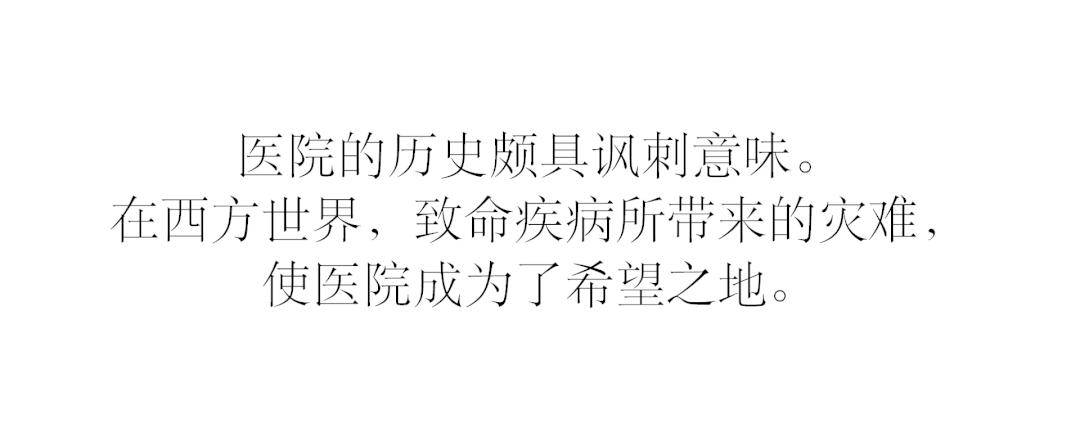
史蒂文斯·克劳肖提到了建于17世纪的荷兰莱顿瘟疫屋。“这是一个美丽的方形结构,四周环绕着一条水道,另一个水道则贯穿过它的中心”
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建筑曾被用作军事医院、军事博物馆、监狱和男童拘留中心。1990-2019年,它一直是该市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个侧厅,2016-2017年,当博物馆进行翻修时,它还收藏了在蒙大拿州出土的霸王龙特里克斯的骨骼化石。

检疫站旨在保护港口免受经由航船传播的病原体的侵害。抵达港口的船长需发布一份声明,包括船舶的出发地、航行轨迹以及船上人员的健康状况。港口代表将乘小船前往接收,然后引导可疑船只的乘客前往隔离处,在那里他们将被隔离。
意大利威尼斯礁湖中的小岛圣玛利亚·迪·纳扎雷斯(Santa Maria di Nazareth),是最早的检疫站之一的所在地。从1423年开始,瘟疫患者被送到那里,远离社会生活40天。这段时间被称为“quaranta”,是“隔离”一词的来源。

1793年费城黄热病大瘟疫爆发的六年后,一座优雅的乔治亚风格的检疫站在特拉华河边落成。
史蒂文斯·克劳肖称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机构为“具备混合功能的医院”,提供“医疗和精神治疗和护理”。
1793年爆发的费城黄热病夺去了当地十分之一居民的生命。六年后,一座优雅的乔治亚风格的检疫站在特拉华河边落成,如今是蒂尼库姆镇办公室所在地。
它是美国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检疫站之一。另一个是位于俄勒冈州阿斯托里亚的哥伦比亚河检疫站。纽约则于18世纪30年代建造了检疫站,用来安置天花患者,该建筑后来被摧毁,如今其上矗立着自由女神像。

1848年春天,法国废除了奴隶制,但这一消息花了9个月才传到了殖民地留尼汪岛。此后不久,自愿移民取代了奴隶劳动力。
留尼汪岛上的移民来自许多地方,因此总有一些流行病需要预防。由于岛上的居民特别容易感染疾病,检疫站为此就建立了。

在留尼汪岛大艇村(La Grande Chaloupe)的检疫站,移民们“会待上几天、几周,有时甚至几个月,”检疫站负责人杰西卡·普拉伊说。
为奴隶设计的检疫站很小,而且条件很不稳定;另一个检疫站是为来自中国、印度、也门和马达加斯加等不同国家的自愿移民建造的,于1860年在大艇村落成。
“人们会待上几天,几周,有时甚至是几个月,”该检疫站负责人杰西卡·普拉伊说。“普通的工人会睡在密室的双层床上,”她解释说,“但也有其他人,比如商人,或者有钱人。他们必须支付隔离费,但他们的状况反映了他们的地位。我们在历史档案馆的菜单中发现,他们有时会享用香槟和牛舌。”
检疫站的翻新工程始于2004年,目前仍在进行中。“我们想让大艇社区参与进来,”普拉伊女士说,“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培训人们的砖石、木工和其它手艺。”
其中一处院子被建成了博物馆,陈列着移民的烟斗等——许多移民都是靠抽烟来消磨时间,每天无所事事。另一处院子是研究所。在这里,药用和食用植物如今又开始开花了。

1631年,威尼斯陷入了瘟疫的魔爪之中。为了抵御这种疾病,共和国政府开始兴建一座教堂:圣玛利亚·德拉·敬礼教堂(Santa Maria Della Salute),或安康圣母教堂。这是动荡时期宗教敬拜精神的体现。
该教堂由巴尔达萨雷·隆格纳(Baldassare Longhena)设计。“他说这个项目是前所未见的新建筑,”建筑历史学家玛蒂娜·弗兰克(Martina Frank)说,他曾撰写了一本有关隆格纳的专著。这个设计具有深层的积极意义,它的灵感来源于对日后的感恩节盛宴的憧憬。

意大利威尼斯安康圣母教堂前,一名船夫在横渡大运河。
大教堂的兴建需耗时56年,而就在奠基之后7个月,1631年11月21日,这座城市即走出了疫情,并且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传统。
通常,人们会在大运河上搭建一座临时桥梁,随后游行队伍通过桥梁走向教堂。但由于Covid-19疫情爆发,感恩节盛宴取消,2020年的大运河上并未搭建桥梁。
威尼斯有五座巴洛克式教堂,灵感来自于不同的瘟疫,每座教堂均饰有相关的艺术品。在安康圣母教堂的主祭台上,装饰着佛兰德巴洛克艺术家约瑟·德·科尔特(Josse de Corte)精心制作的一组雕像。大师把这种疾病描绘成一个衣着飘逸的老妇人,被挥舞着火炬的天使追赶逃窜。
这是衰弱和死亡临近的缩影,还是说这位女士代表了一个邪恶的女巫?“更像一个女巫,”弗兰克笑着说。“当时整个社会都非常厌恶女性。”

2014年埃博拉病毒抵达利比里亚时,该国只剩下58名医生。由于长期内战,其他医生多已移民。只剩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通过改变社会习惯来拯救自己的家园。
在西非,约有一半的埃博拉感染源于与死者的接触,尤其是清洗遗体环节。虽然一些社区被劝说放弃了这一习俗,但其它社区却坚持了下来,有时还会攻击穿着类似太空服的防护装备的殡葬队。

一名男子在利比里亚蒙罗维亚郊外的迪斯科山公墓售卖花圈。
蒙罗维亚地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新的公墓,该公墓离城市足够远,使殡葬队得以避免在传统墓地周围遇到反对派。现在,约有2200名逝者被埋在蒙特塞拉多县的迪斯科山上。其中包括穆斯林,其坟墓面对着麦加的方向。
利比里亚公共卫生专家莫索卡·法拉(Mosoka Fallah)说,当地领导人同意,在雇用当地人为殡仪人员的前提下出售墓地用地,以建立一所学校,购买一台手压水泵。
2014年12月,葬礼开始时,法拉参观了迪斯科山,并流下了眼泪。由于官僚因素,该墓地的使用被推迟了五个月。在此期间,数百名利比里亚人被火化,这是一种极其不受当地欢迎的做法。“我看到很多家庭因为火化而伤心欲绝,”他说。“这真是大错特错。”埋葬在迪斯科山上的,有70%是骨灰盒。
法拉表示,迪斯科山如今是埋葬新冠肺炎死者的一个常见地点,因为穷人可以免费将亲人埋葬在那里。

“你知道吗,在这一带甚至还有一堵瘟疫墙?”保罗(Paul)问同伴安德里亚(Andrea),后者是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的小说《瘟疫墙》(Wall of the Plague)中的主人公。
两人都是旅居法国的南非人,都刚刚与恋人新近分离。他们的谈话充满了调情的意味,而疾病史则是一种战略上的话题转移。

法国吕贝隆地区自然公园瘟疫墙的边界标志。
催生了瘟疫墙的恐怖疫情于1720年乘船抵达了普罗旺斯。阻止其蔓延的尝试包括封城,切断连接渡船和河岸的绳索。一切都无济于事。两年内,这种疾病已经造成近13万人死亡,占法国东南部人口的三分之一。
乡村小教堂仍是这种流行病的见证者。其中一些乡村小教堂是献给蒙彼利埃的圣洛奇(St. Roch)的,他是狗和单身者的守护神,也是一位传奇的治疗师。环绕在它们周围的是瘟疫墙(Mur de la Peste),一种流行病学防御设施。
瘟疫墙旨在限制法国领土和教宗国控制的飞地——沃奈桑伯爵领地之间的通行。它起始于梅内贝斯村附近一条逐渐消逝的沟渠,彼特·梅尔(Peter Mayle)的《普罗旺斯的一年》就是以这个沟渠为背景的。
这堵墙绵延约18英里,越过橡树丛覆盖的山丘,一直延伸到山峦作为天然屏障的地方。但瘟疫墙未能成功阻止瘟疫的蔓延,其依旧在1722年到达了阿维尼翁市。

在美国和加拿大,有60多个纪念艾滋病受害者的场所,其中一些有玫瑰园那么大。
国家艾滋病纪念园执行主任约翰·坎宁安(John Cunningham)患有这种疾病已有20年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达旧金山后,他见证了同性恋群体的斗争,以及几乎同时出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纪念概念。一种是艾滋病纪念被子,它纪念了因艾滋病而丧生的生命,可以在不同地方进行展示。另一方面,位于旧金山金门公园的国家艾滋病纪念园则是一片广阔的土地,里面有树林、草地和植物,以及在石头和路面上刻有名字的人行道。

旧金山金门公园国家艾滋病纪念园。
在最近的一次Zoom访谈中,坎宁安回忆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决定为那些正在遭受灭顶之灾的人们创造一个空间,让他们聚集在一起,不仅可以共担悲伤和痛苦,也许还能通过回忆和治愈,带着希望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
该市为他们在金门公园划了10英亩的土地,成员们开始共同美化这个地方,此后已累计超过25万小时的志愿者时长。纪念园的核心是“朋友圈露天广场”,上面刻着2500多个艾滋病患者的名字,既有逝者,也有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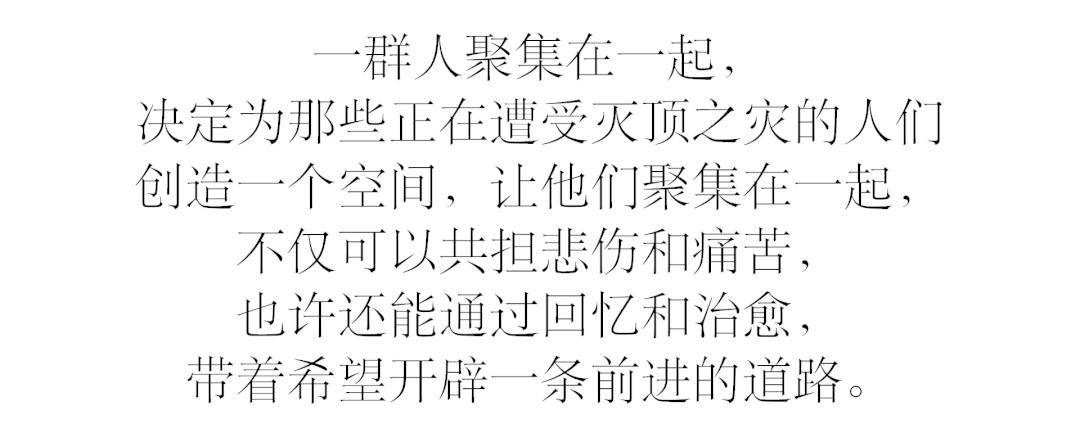
坎宁安强调了纪念园作为圣地的替代品的作用。“许多男同性恋者在他们成长的宗教社区受到排斥,他们来到旧金山,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在许多方面,这个空间,作为一个纪念场地,是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

几乎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乌拉圭,可能是第一批落成Covid-19纪念碑的国家之一。截至2月中旬,乌拉圭因疫情丧生的人数不到600人。
蒙得维的亚的建筑公司Gómez Platero Architecture提议建造一座纪念碑,该建筑由一条延伸向大海的人行道组成,最终是一条滨海步行大道。

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拟建的Covid-19纪念馆的渲染图。
“我们从事城市化工作,我们是公共空间的拥护者,”马丁·戈麦斯·普拉特罗(Martín Gómez Platero)解释说:“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公共空间,旨在帮助我们时刻记住,人类是自然力量的附属。”
他说,他的团队从2020年春天开始设计,终稿已送交乌拉圭总统路易斯·拉卡列·波乌(Luis Lacalle Pou),并得到了他的批准。纪念碑的地点被选在市中心的东部边缘,包括一个现有的码头和一个小岛。目前还剩蒙得维的亚市尚未作出决定。
迄今为止,新冠疫情已经夺走了约250万人的生命。所有人都曾因此与朋友和家人分开,如果他们曾经沿着某个南美城市的海滨漫步,那么他们谁都不会对这个地标无动于衷。

原标题:《历史上,疫情除了带走生命,还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纪念?》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