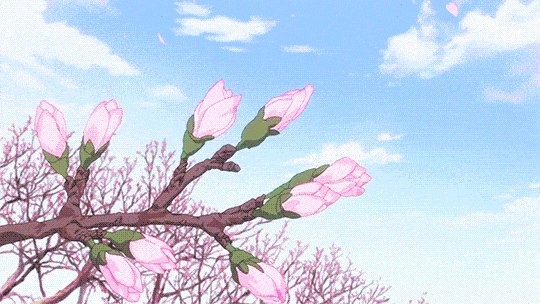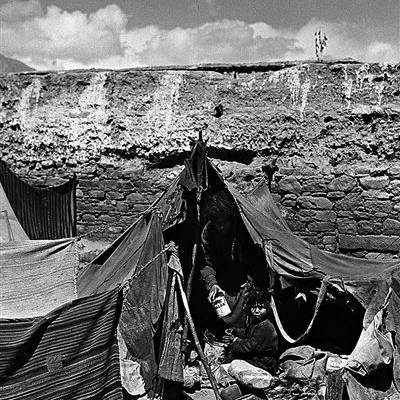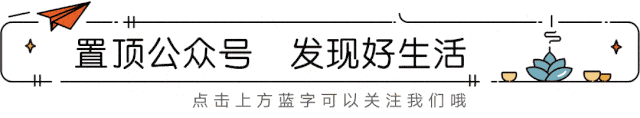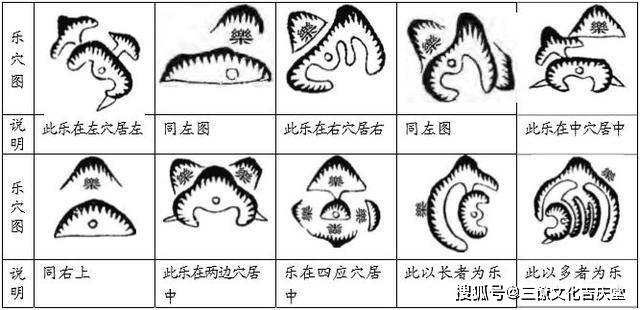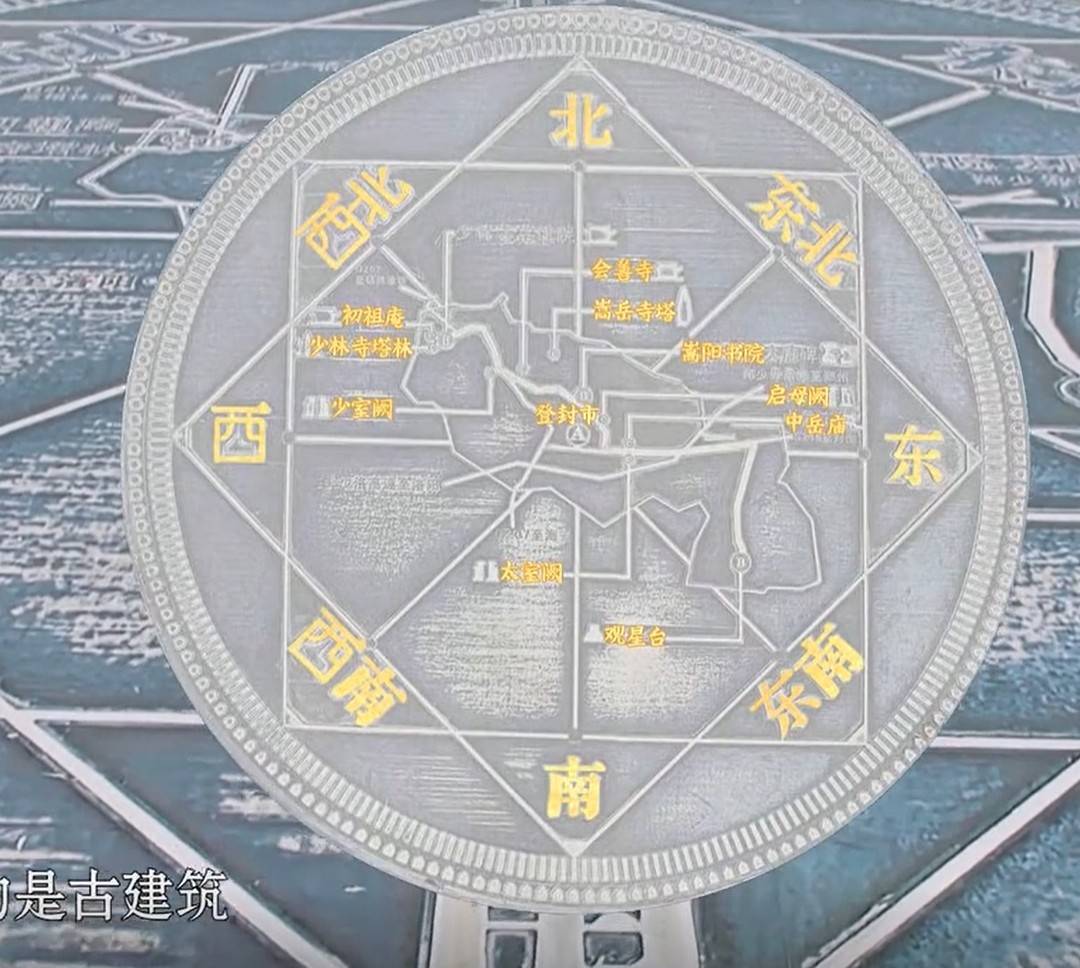除夕的前一天,天气不错,温度高达14摄氏度,便去天坛转转。比起前些天,天坛里的游人渐多,挂起的红灯笼也渐多,北天门前那两排银杏树上悬挂的红灯笼,比起去年明显又密又红。想起去年这时正是武汉封城以及天坛里冷清的样子,如今节日的气氛,已无可阻挡地弥散开来。天坛不过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们的心气儿。
百花亭南侧,有座藤萝架,我常到这里来,比起丁香树丛旁的藤萝架,这里更显清静。夏日里浓荫匝地,冬日里叶子落尽,白色的架子像鲸鱼的骨架浮出水面,白得格外清新醒目。
中午时分,只有一对男女面对面坐在那里聊天。我斜坐在他们对面不远的架下画他们。男的面对着我,年纪六十上下,面容清癯,有些谢顶,手里握着一个保温杯。女的背对着我,靠在藤萝架上,看不清面容,只见一头垂肩发飘散在大衣的肩上。他们之间隔着一段距离,露出一截白色长椅,上面放着点儿零食小吃。女的背对着我,男的则专注于聊天,而且说话轻声细语,格外缠绵。他们好像都没注意到我在画他们,甚至忽略了我的存在。
我一边画,一边揣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像是老夫老妻——老夫老妻,一般不会有这样面对面的缠绵交谈。冬日的阳光那样温暖,那些缠绵的话语,像小河淌水一样,被阳光晒得暖暖的,荡漾着轻柔的涟漪。
男的把保温杯递给女的,说是普洱茶。女的说你还挺讲究的。男的说自己就是爱喝水,也不懂得什么茶,平常爱喝点儿带味儿的,到了晚上睡觉之前,也得喝上这么一大罐子。女的问,睡觉前喝这么多水,不得半夜老上厕所吗?
这样问,显得有点关心的味道,更让我觉得自己的判断没错:这是一对老友,而且是有段时间没见面的朋友,日子隔开了一道浅浅的河,关心则是河上架起的一座小桥——如果来往密切的话,关心会跨过小河,来到岸的一边。
这也许是他们在春节之前的一次难得的约会。过年了,各家都忙忙叨叨的,腾不出时间,他们便选择了节前这样的一天,没到过年,离年又近,像他们现在的距离,恰如其分。聊聊家常,彼此关心地问候一下,情意都在寻常之间,平易如亚麻布,不是那种华贵的丝绸。
这时,我听到男的回答道:没事,我半夜不怎么上厕所,就是不喝水嗓子眼儿难受。女的说:哟,那你前列腺还够棒的!男的轻轻笑了一下。我忍不住也要笑。这话说得让他们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关心似已过了河。
他们的聊天,无主题,甚至没内容,光是围绕着喝水这样琐碎的事情扯闲篇。我想,普通人家,饮食男女,可不就是这些鸡零狗碎构成的日常生活和庸常情感嘛。谁能离得开水呢?水蔓延开来,滋润着我们微不足道的日子和情感。
女的接过保温杯,没有喝,握在手心里。男的让她尝尝,女的说她不爱喝普洱茶,有股子土腥味儿。男的遗憾地说,早知道的话,就沏点儿铁观音了;又问,铁观音,你爱喝吗?问得有些讨好的意思了——不过,情不自禁的讨好,往往是感情有情有意的自然流露。我听见女的笑了,说道:我什么茶都不爱喝,你忘了,以前那时候我就是不爱喝水,闹得现在血液黏稠。
她说的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男的没有接话。两人忽然冷场。不过,过了不一会儿,就听女的悄悄地对男的说:好像那人在画咱俩。我有些奇怪,她一直背对着我,莫非背后长着眼睛了,怎么会看见我在画他们呢?
男的说了句:是吗?就站起身来,女的跟着也站起来,把椅子上的东西收拾进提包里。两人微微瞟了我一眼,我才看清女人的眉眼,五十多岁的样子,长得清秀,身着紧腰阔摆的黑呢子长款大衣,系一条红色毛线的长围巾。我以为他们要走过来看看我的画,看看画得像不像。可是,他们没有走过来,而是迈过长椅,向藤萝架外面走去。他们走得有些匆忙,男的衣服领子和围巾拧在一起,女的一边走一边把衣服和围巾帮他整理好,然后挽着他的胳膊,背影消失在前面枯枝掩映的树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