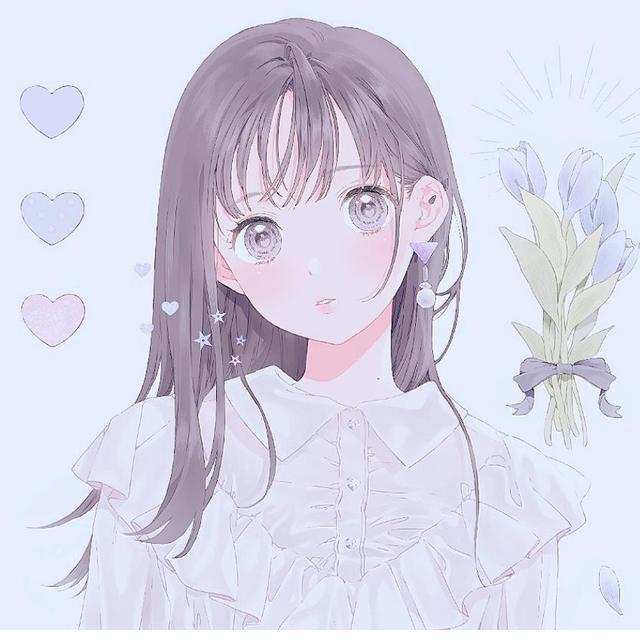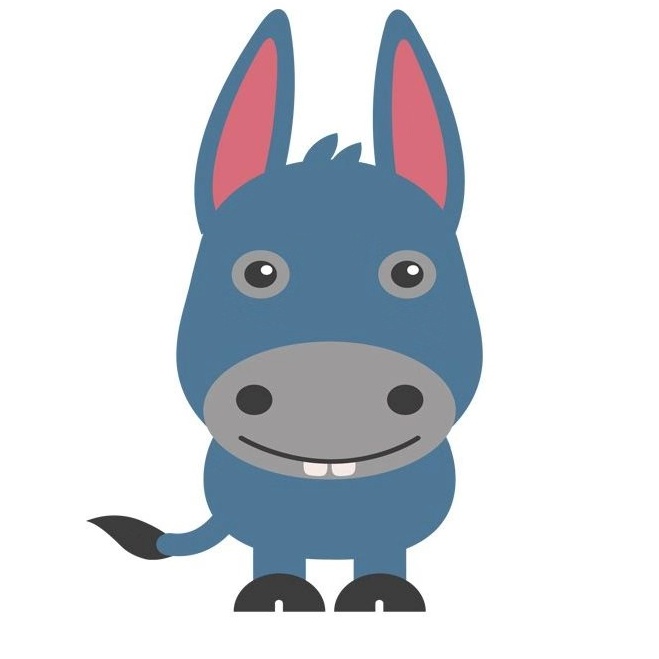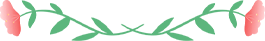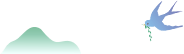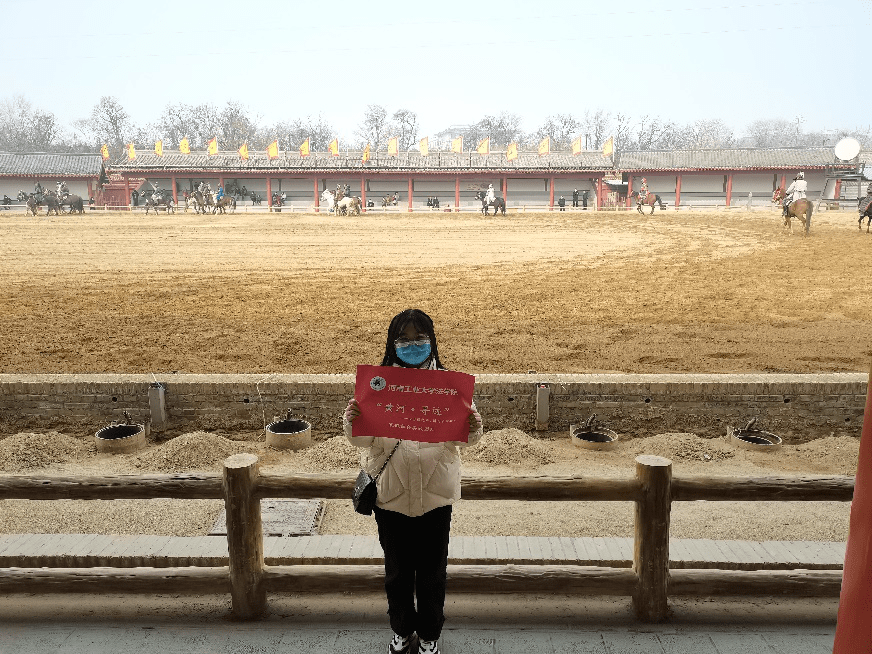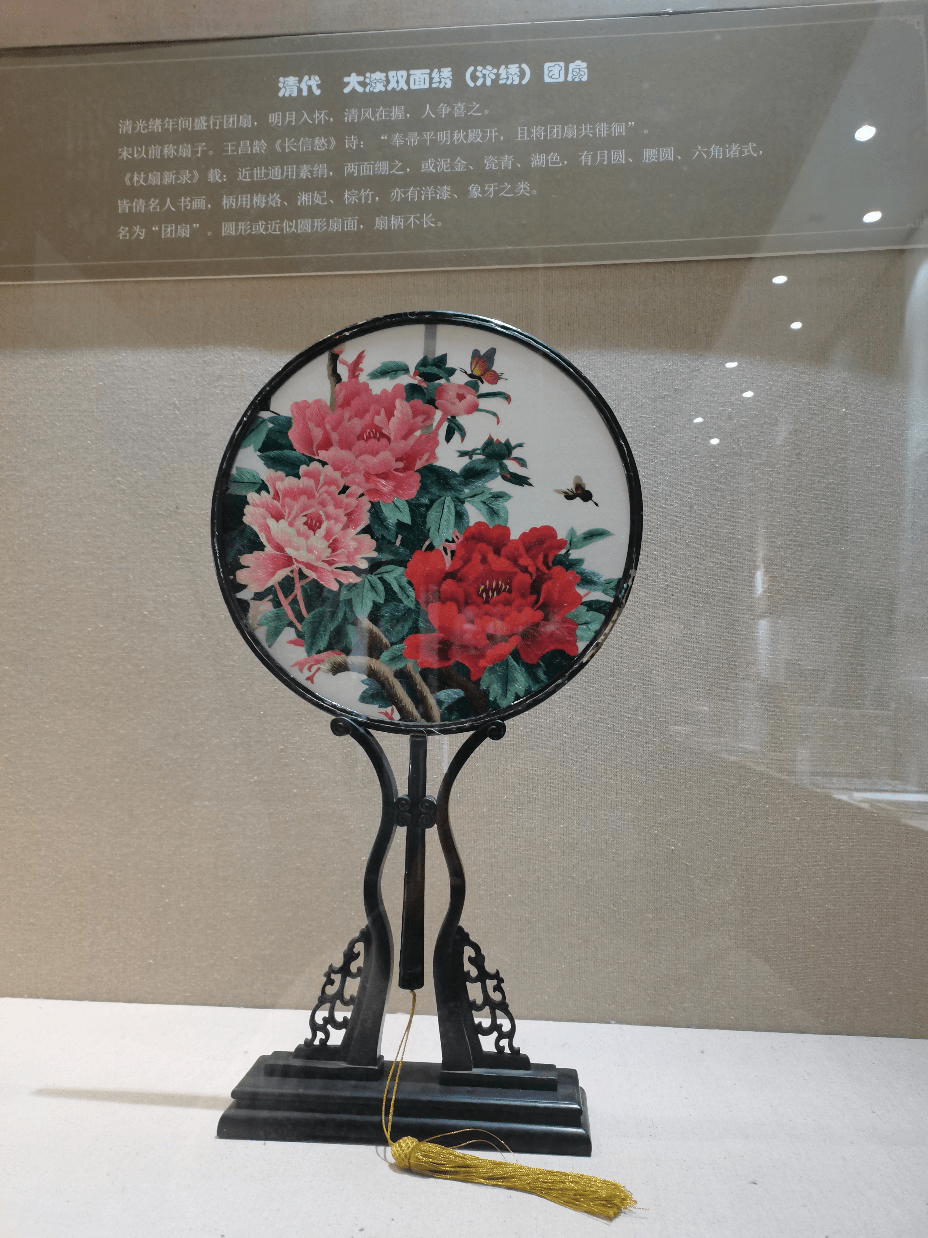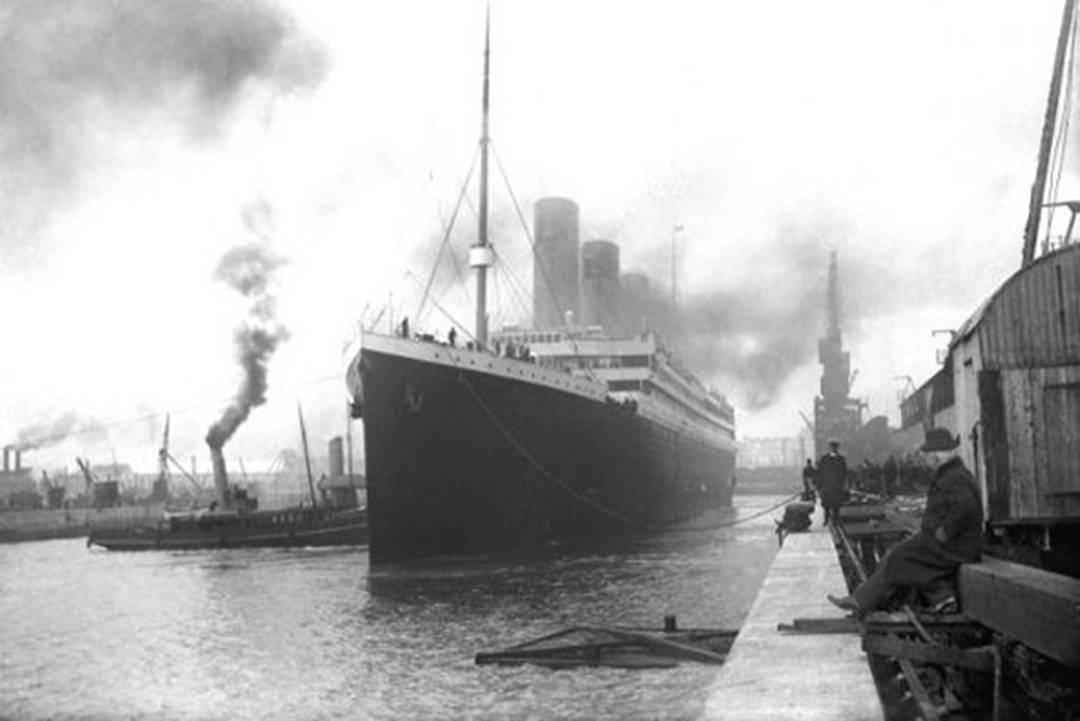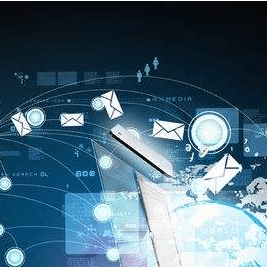值班大话君:刘芯莹
1966年哈尔滨城市影像,请注意,3分10秒时会出现圣尼古拉教堂的镜头。
洛博达(科特)伊林娜斯捷潘诺夫娜1946年生于哈尔滨。1954年随家人到俄国垦荒。自1957年开始居住在哈巴罗夫斯克。《哈尔滨女人》、《在我们院子里》等书的作者。

......马尾辫。辫子不长,才留了4年,可不管怎么样,数字54有很多寓意。我与哈尔滨的最后之约好巧也落在这个数字上。从我们回俄国那一天起,我就再没来过这里。
我当然想见到哈尔滨......我不知道与它相见时会是什么感觉,我害怕,回俄国前,那个住在正阳河的八岁女孩儿的记忆,会是我的帮手吗?虽说我从幼年开始就记住了很多东西。
这次旅程终于成行了。我和女儿一起出发去哈尔滨。订的旅行票保证了从哈巴罗夫斯克直接到哈尔滨的交通、宾馆住宿和早餐。一次性签证——自由活动与生活不受限制。
我们的车厢是加挂上去的。里面多数是中国人,俄国人很少。我们的包厢也是国际性的。
“瞧,”女儿嘟囔了一句。“也真想得出来!”
“稍等会儿,我们试试和他们讲清楚,”我安抚她说。可我们的邻居们不会讲俄语,我就试着打手势,解释自己请求什么。第一次尝试没成功。旅伴们把我们乱七八糟的手语理解成,我们是要把方便的下铺换到上层去。他们惊讶又兴奋地明确表示他们同意。
“不是,不是,”我不同意地摇着脑袋,动着手指头表演着从我们包厢走出去的小人儿。可是,我望着他们惊异的眼睛,明白了,交流算是彻底令人绝望了。
“唉,算了,”列娜摆着手。“我们就忍着吧。”
让我们吃惊的是,中国人罕有地客气和充满善意。尤其是在格罗杰阔沃几乎停车八个小时之后,我们的友谊更加牢固了。
我们被要求带上东西从车厢出来。执勤的女人把我们送到候车厅之后就走开了。我们在椅子上安顿好自己的零七八碎,就打算熟悉一下环境。大厅里只有我们这些可怜虫——为了方便多次调车一直挂在编组车尾的国际车厢的代表。没有寄存处,厕所锁着。连吃点东西的地方都没有。
可海关这个时候正查验着800个倒爷的货物。因为东西太重和情绪紧张,倒爷儿们红头涨脸、汗流浃背地拖拽着他们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旅行箱,顾不上讲究脸上的表情了。我们时不时往查验大厅张望,愁眉苦脸地发现他们的队伍无边无尽。最后,他们允许我们回到车厢。在令人生厌的几个小时的等待之后,车厢就如同自己的家一样,可以在这里放松,还可以和邻居们聊聊天。的确,难处都凑到一起了。操持着各种语言已经不再是障碍,我们能相互理解,对旅伴的情况也越来越了解了。
“真没想到,中国人是这么招人喜欢。”女儿若有所思地说道,当再一次露出微笑,挥起手的时候,是我们在和自己的邻里告别了。前往哈尔滨的,只有我们。
翻译娜塔莎在月台上迎接了我们。她把我们送到站前的宾馆后,告诉我们,哪里都有什么,该怎么办,临走留了联系电话。
在哈尔滨的第一天。我就不分头描述我们所逗留的八天时间了。我会试着把这些日子合成一幅城市充满情感地接纳我们的完整画面。我很难去比较什么。我不知道哪里是老哈尔滨的中心。我的记忆中只有正阳河、我们的街、松花江和学校的画面。缺少的,是能讲很多故事、解释清很多事由的尼古拉扎伊卡。我有他的地址和电话,还有他家的照片,是新、老哈尔滨的爱慕者娜捷日达鲍里索夫娜雅科夫列娃赠送的。
也许不是季节。城里没有欧洲人。中国人甚至连蹩脚的俄语都不会讲,可年轻人会英语,但我又不懂英语。第一天我居然迷了路。宾馆的名片不知为何也没帮上忙,中国人看过之后,耸了耸肩膀。我就接往前赶路,离住的地方越来越远了。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女人解救了我。她从我手里接过名片,问了这个又打听那个,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把我领到了宾馆。
后来的几天我们熟悉了城市。我几乎与任何一名游客没有区别,去了照例要去的游玩、消遣的地方。有一处除外。
我出生在这里。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婴儿出现在这个世上,这片土地接纳了她的第一口呼吸,听到了她的第一声啼哭。我们在哈尔滨住得越久,我就越能感受到这个光阴。
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尼古拉扎伊卡的家。主人在澳大利亚。但我们还是通了话。感谢他身处如此遥远的距离,还帮助我们弄清了情况。知道我曾住在正阳河,他安排好去的行程,而且还打听清楚我和姐姐上学的学校还保留着。当然,我们住过的街上已经什么都不剩了。我家租住过的那套居室的位置上是一幢多层楼房,但学校还立在原处。这么多年它没经受过大修,所以里面的结构、木制地板、墙壁、窗子,一切都和我遥远的童年时一般模样。

哈尔滨。2008年,这里曾经有一所小小的正阳河学校。
五十年的光阴,房舍完全没有变化。
我走进自己的教室......因为激动,心紧缩着。老师给我调过两次座位,我肯定能找到这两个课桌的位置。奥莉加叶皮凡诺夫娜是位严厉的老师,我很怕她。一年级我熬得很不容易。口吃和内心的恐惧始终影响着我。真是奇特,孩子的记忆能吸收进那么多东西!我还记得这扇门,等待着铃声,我的眼神就没从这扇门上移开过,尤其是阅读课下课的时候,我习字课的成绩始终不如人意。还有这条小走廊,我含着泪在走廊的窗边向姐姐倾诉过委屈。记忆留住了一切,一切没有改变。
夏天,学校被改造成儿童乐园。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儿童乐园,不组织餐饮活动,只是在夏季那段时间召集起孩子们,看护他们。我们的辅导员叫娜塔莎。是位年轻的姑娘,留着垂到腰以下的粗辫子,她尽其所能地让孩子们开心。孩子们在院子里摆放的桌上画画,用粘土塑小人儿,读书,排着队把娜塔莎的辫子编上再拆开,小孩子是不许动她的辫子的。
我倒没有特别地烦恼。我走进校园,在孩子们中间转几圈,人不知鬼不觉地钻过栅栏上熟悉的豁口,消失了,逃脱枯燥无聊的阅读、绘画和雕塑。有的时候,我会沿着街道溜达上一阵,再原路返回去,谁都没注意到我,而我,感觉到冗长单调的寂寞,再次钻出栅栏豁口,溜走了。
我还记得,是怎么举行结业队列式的,我在操场上一直沿着对角线穿过来走过去,消失于默默无闻之中,我满怀着期待和不安等着召唤我到颁奖的桌前。自然,没有奖励我。仪式结束了,大家围住穿着雪白薄料子上衣、手捧漂亮花束的娜塔莎。大家最后一次触摸那根编结得很美的辫子,讲着美丽的词语,感激的词语和爱的词语。而我,再次穿过那熟悉的栅栏豁口,走开了......
这一切是那么久远!再次察看这所房舍之后,我走到街上。院子变了,我们学校旁边给中国孩子们盖起了多层的新学校。他们聚在一起,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没有了从前的栅栏和运动场,但我还是能看到它们,因为记忆持久地把我带回童年,阻隔了不相干的烦扰。
最后一次按下相机的快门,启动摄像。别了,可爱的童年一角,我们前面的路通向松花江的方向。因为巨大的和一次又一次的生态灾难,对哈巴罗夫斯克人来说,这条江的名字已然成为灾难的警告。间歇性地向巨大的城市汲取饮用水的水体中排放废水,引发了不睦。我怕看到肮脏、让人难受的江水。
我的第一印象——松花江很像阿穆尔河。近几年阿穆尔的规模与它的支流相比,河水急剧变浅了。
我们下到岸边。微风吹皱了平静的水面。江面孤寂。我们走到老水泵房跟前,童年时,我们就在它的对面玩耍,我的表兄、不久前到访过哈尔滨的热尼亚洛马金也描写过它。我躬身掬起一捧江水。没什么气味。松花江干净了。
伊林娜斯捷潘诺夫娜洛博达
《艺术文学家》杂志
2010年第2期(总第26期)
Macrooz 译
后记
2010年,我们的杂志上刊载了伊林娜斯捷潘诺夫娜洛博达的文章《五十载情缘哈尔滨》。这是她讲述自己回到童年城市的一篇随笔,她在那里生活到八岁,直到一家人返回俄国。而在《哈尔滨女人》当中,以回忆录与档案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伊林娜洛博达“从年龄的高度走进往昔的迷宫,试图理清逝去的一切。”
对她来说,哈尔滨是个既愉悦又忧伤的话题,就如同一切光明都留在了遥远的地方。当哈尔滨重新恢复了慈善舞会,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处的很多哈尔滨人和他们的后人前往那座城市的时候,伊林娜斯捷潘诺夫娜是那么地高兴,她也梦想着这次旅行,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她却没能成行。伤心,痛苦,然后挥挥手,现在该做些什么!她本就是罕有地乐观、随和的一个人。所以她最终写出了讲述动物的童书,出版了几本小书,印量不大,但出版了!2002年是《在我们的院子里》,2010年是《在阳光明媚的青草地上》。
受到在《艺术文学家》杂志首次发表作品的鼓舞,伊林娜斯捷潘诺夫娜还想写一些自己妈妈的素材。妈妈曾是位医生,漫长的一生在中国和俄国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但因为各种琐事的妨碍,文章搁置了,然后,妈妈薇拉瓦西里耶芙娜身患重疾。我与伊林娜斯捷潘诺夫娜的往来转为偶尔一次的电话交流,而且,她再也不去每月一次在“远东国立图书馆”召集的“地方志学”俱乐部成员的聚会。要知道,她喜欢“地方志学”,也始终是那里受欢迎的客人。照看生病的妈妈消耗了她很多的精力。随后结束了。那份伊林娜斯捷潘诺夫娜总会带几份到《科学》地方志学分部、来自新西伯利亚的报纸《在满洲里的山岗上》,2011年第171期上,刊出了令人悲痛的简讯,“我们的‘哈尔滨女人’千古”。
伊林娜洛博达以这段话作为自己《哈尔滨女人》一书的开场白:“那么值得回望过去吗?我认为,值得,回忆和讲述完过往的年代,不在自己后代的记忆中留下模糊的影子。”
......
《艺术文学家》杂志
主编叶连娜格列博娃

伊林娜 斯捷潘诺夫娜 洛博达(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