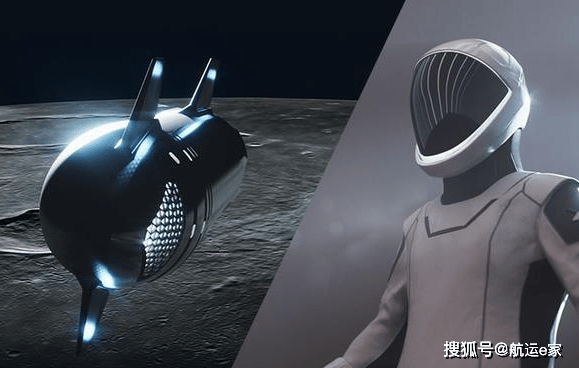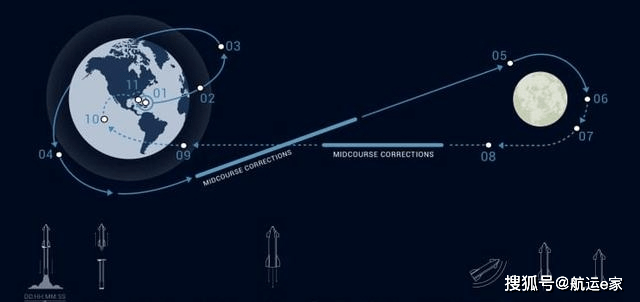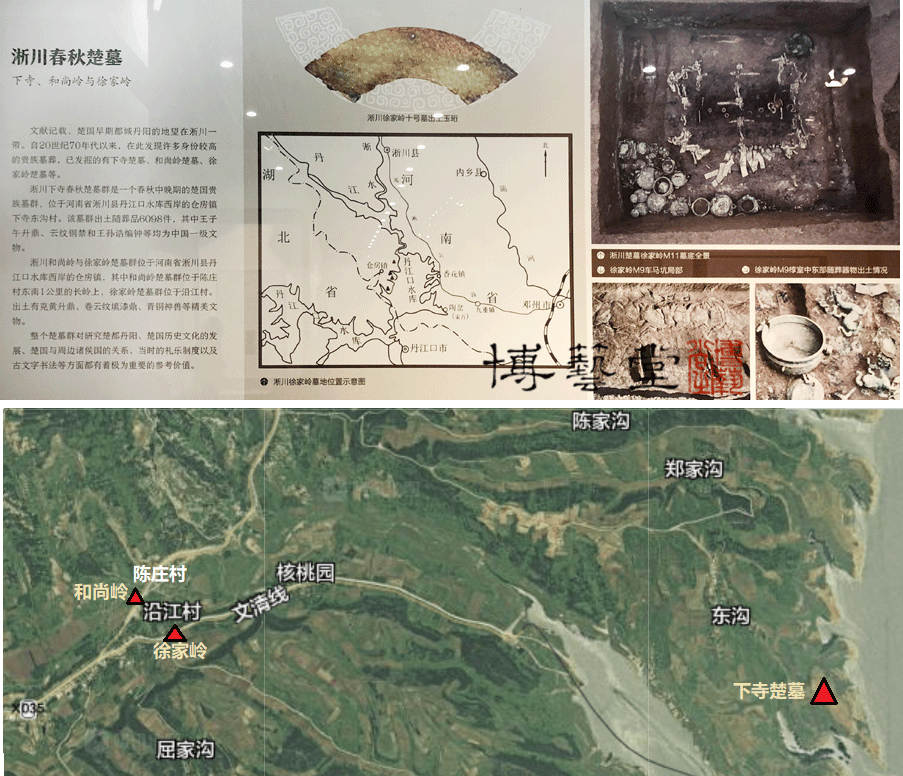谭圣林
转眼,离开老家那座山窝,奔波城市已经20多年了。
从游离人海边缘,到立足城市中央一隅,其间曾经的懵懂尴尬、委屈吃力、甚至郁闷绝望,一一收藏于内心的文件夹,电话微信传回家的,大多是整理过后的笑颜和笑声。
最初是租房,合住、单间、一室一厅。骑一部红锈斑驳的单车,穿梭于小街小巷。每天傍晚走出办公室,不敢轻易靠近光怪陆离的风声,只能在湘江岸边听风言和风语,然后悄悄拐弯到蜗居的落脚点。
后来买房,成家,再换房。每当夜幕降临,行色匆匆下班后,径直回到安身休憩之处。
年终岁末,城市再一次按下慢放键。脱掉寒风,穿上阳光。收拾行李,加满汽油,驶往父母亲那边的高速公路,回家。
无需导航,回家的路线很精确。就算限速,也限制不了归心。减缓速度,一个个弯腰的隧道,恍若父母亲弧形的身影。放下车窗,空气里的负氧离子灌进来,洗脑洗心。
一个个高速路口,是一个个他乡游子的驿站,南下的,北上的,求学打工的,经商从政的,众多接送春天的人,开车在这里转半圈或者一大圈,终究要绕到归途。
到家了,家里新建的房子,也模仿城市高楼,有了点洋气。年已七旬的父母亲,依然守护着躲在新房子后面的土屋,他们用不惯液化气,坐不惯沙发,睡不惯席梦思,受不了空调。在那些经久消失的岁月里,父母亲已经与小木凳、硬板床、柴火灶、黑木炭相约一生。
一条大黑犬从低矮的屋檐下飞奔过来,仰天叫喊着,批评我们这些离家太久未归的人,把我们当成陌生来客教训一通。不像它,一旦认定这个家,就坚定地守护一生。母亲摸摸大黑犬的头,打消它的火辣脾气,要它体谅归家人的难处。
辣椒炒鸭,米粉蒸肉,土鸡清炖,冬笋包饺,炒出一桌土菜,烫热一壶水酒,舀满一盆鲜汤,这些活对父母亲来说,是熊熊柴火中,几十年如一日打磨的手艺。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饥肠辘辘时,吸几大口香喷喷的烟火气息,有点呛鼻,但是可以为疲惫的筋骨消炎解乏。
走亲访友,晒晒红包,互换荣光,微信关注。煮雪烹茶,望梅止寒。
终究还是要返城。尾箱里塞满了腊鱼腊肉和土里土气,父母亲用纤维袋打包的红薯南瓜萝卜,依次钻进座位底下扎堆。
其实,城里不缺这样的荤菜素菜,缺的是家人亲人互相传递的热气腾腾。
车子的底盘压得很低,启动雨刮器,刮灰去尘,擦亮眼光,再一次远离乡愁。
在城市拼力那么多年,失意抑或顺意,始终对父母和亲人的嘱托保持敬畏的态度。就像从不敢怠慢家乡那一段颠簸的小路,再扎实的底盘和底气,再强硬的面子和里子,你只要稍不留神,就会被防不胜防的障碍划伤。
黄金周放假,读大二的儿子发来信息:“爸妈,我明天回家。”很直接的一句告知,却让我顿时泪目。原来,在儿子心目中,也是一样的定义,往爸妈的方向延伸,就是回家的路。
而我已经站在家的定位,等待儿子如约而归。在我背后的远方,阳光突然冒出来的山头下,是父母双亲翘首的凝望和念叨,越来越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