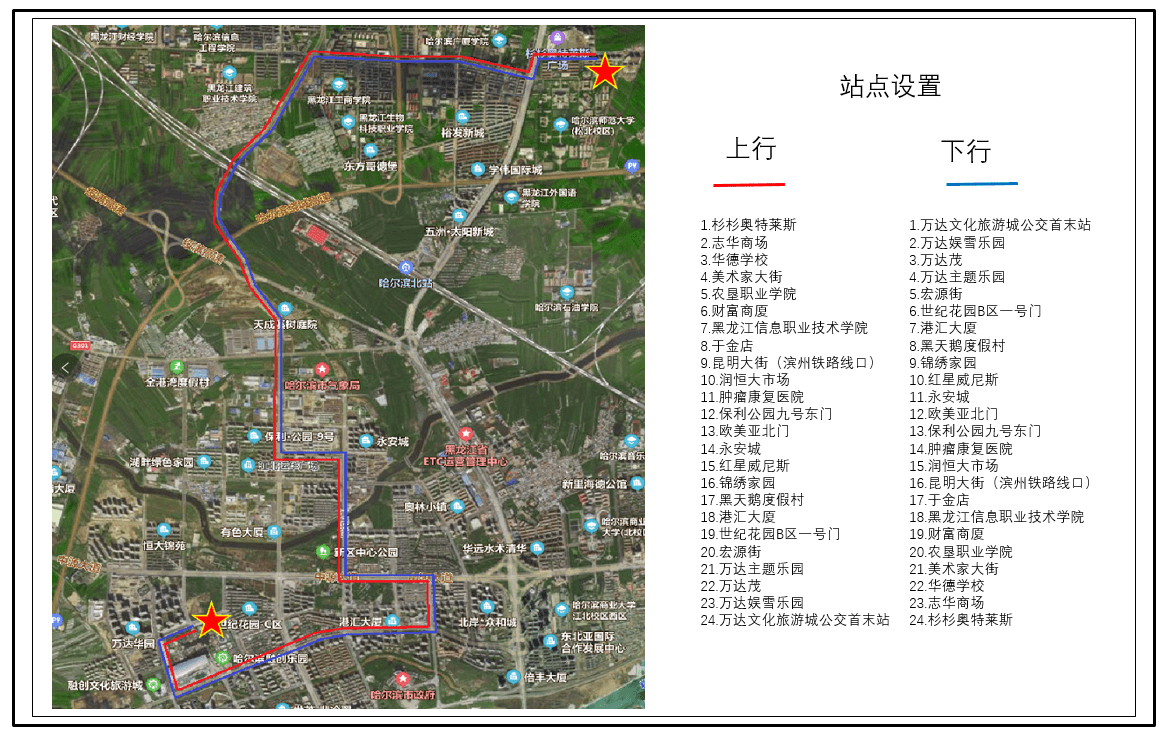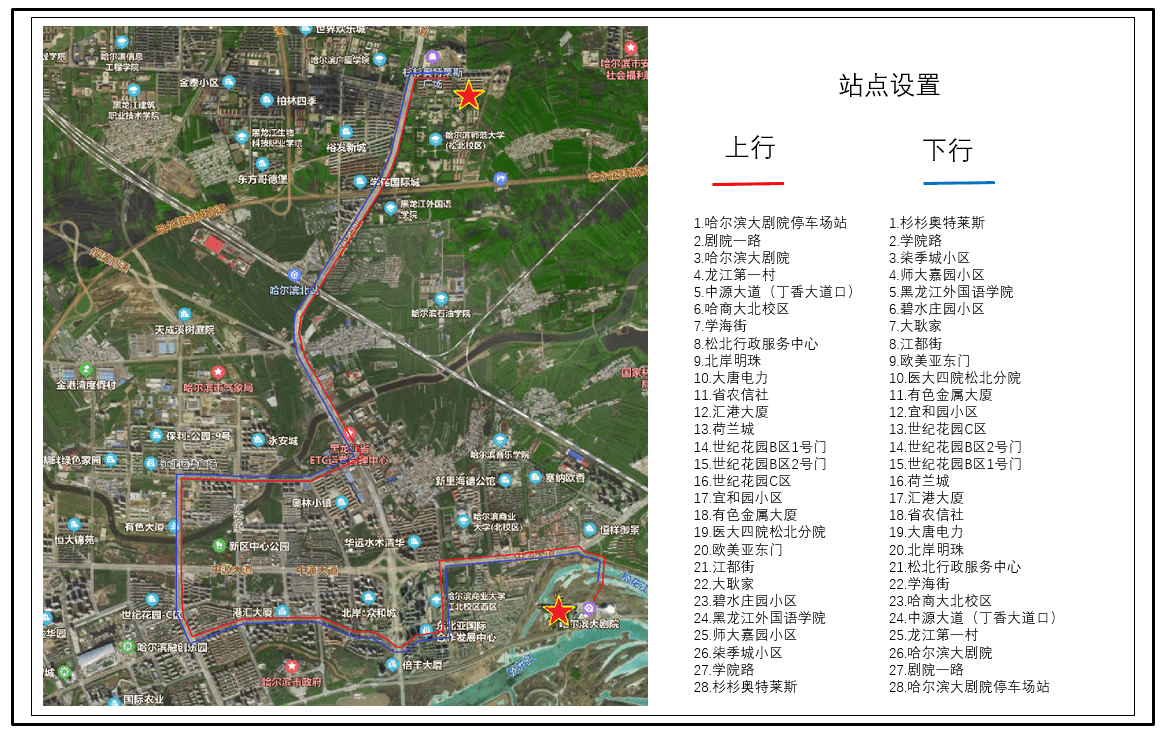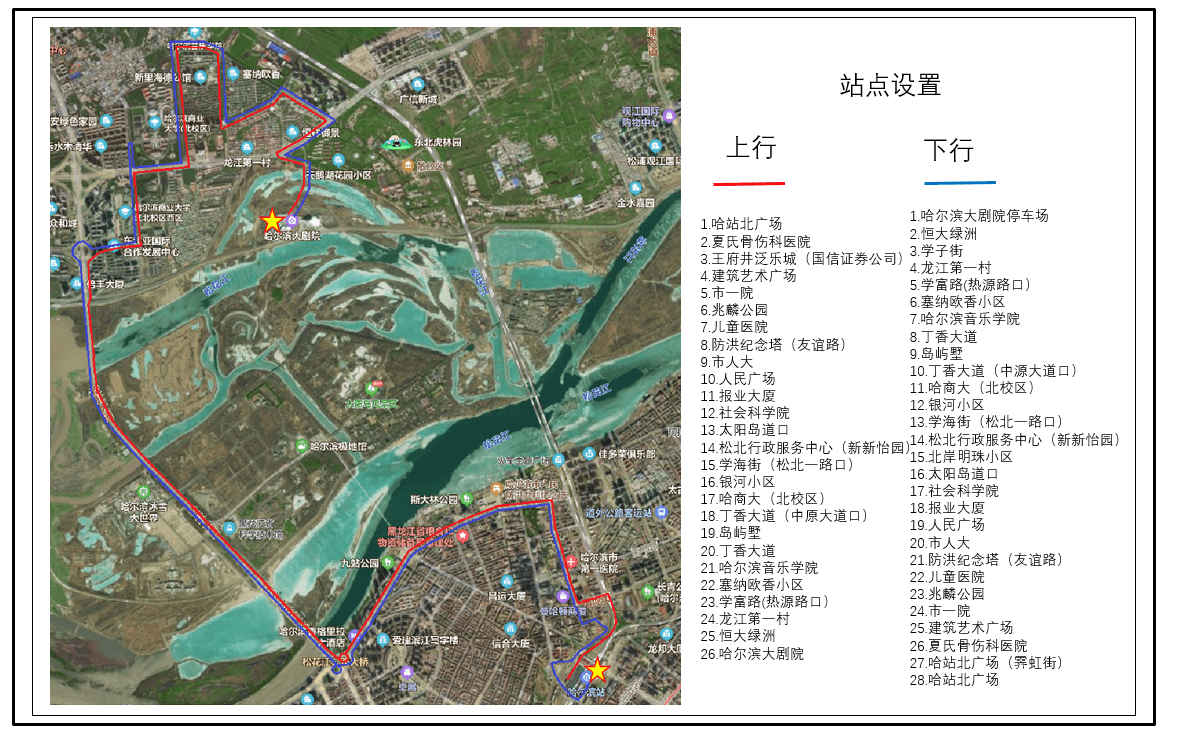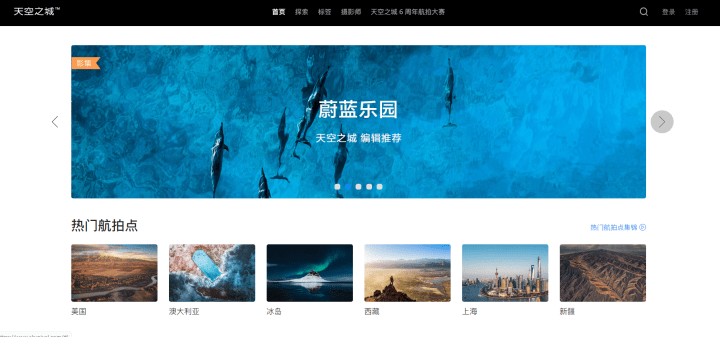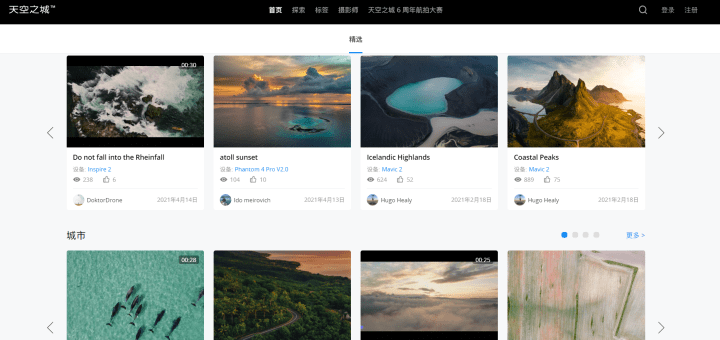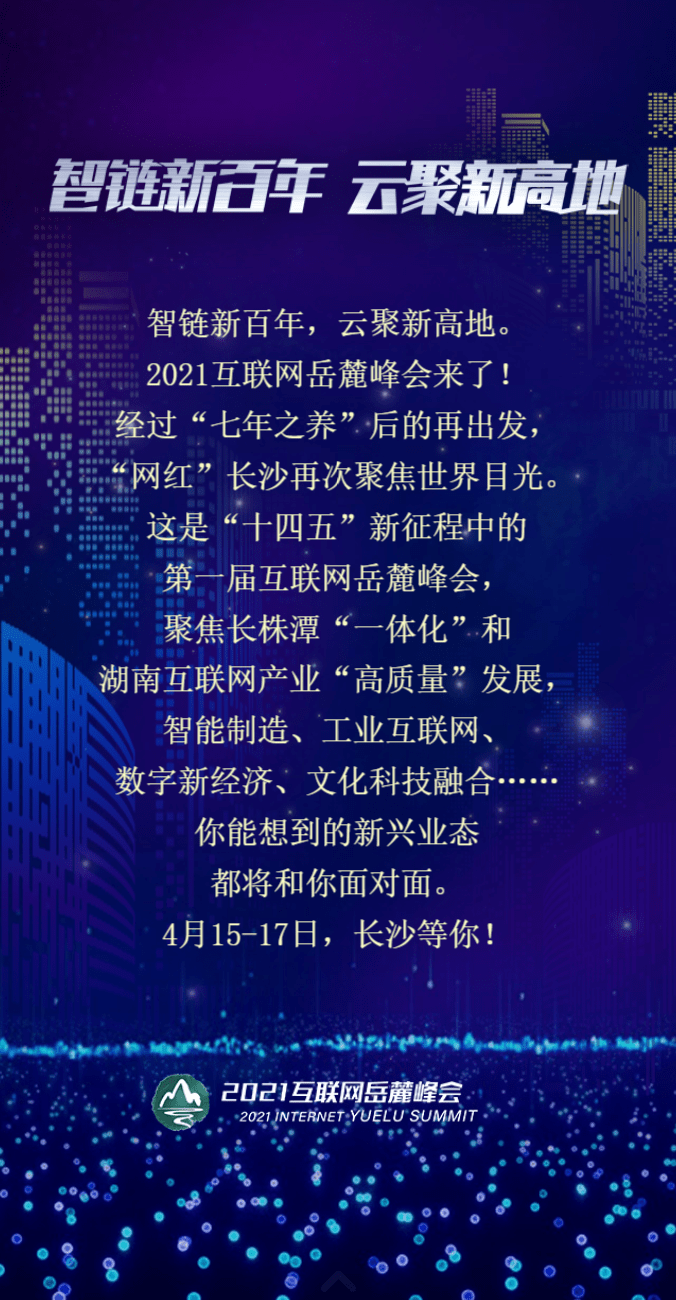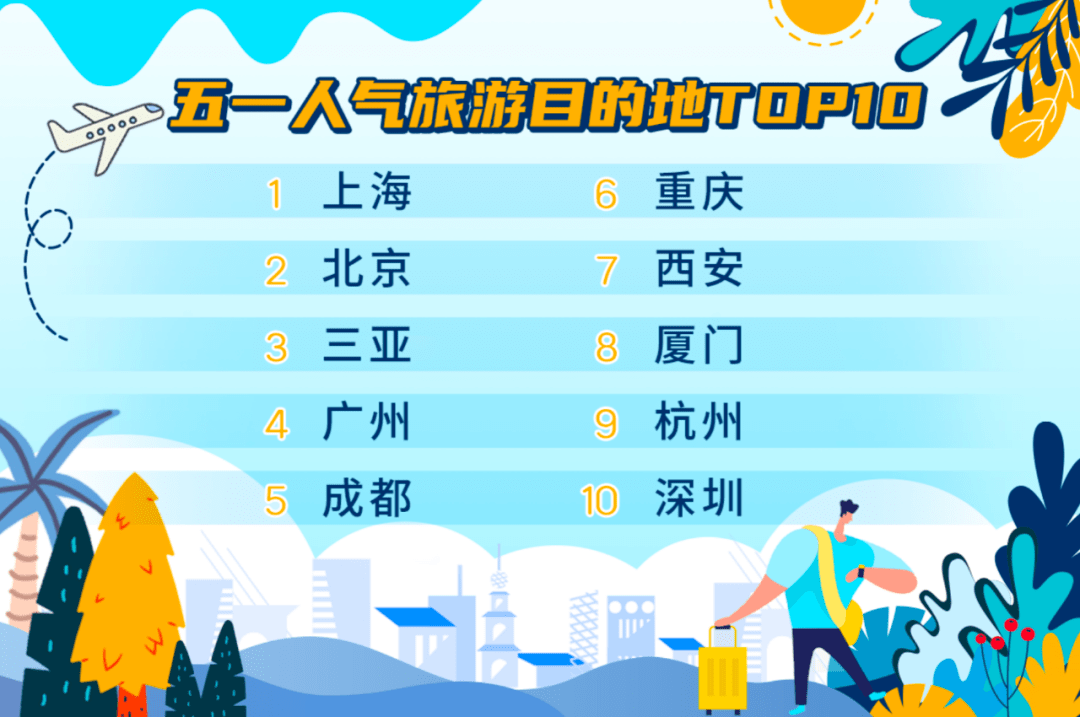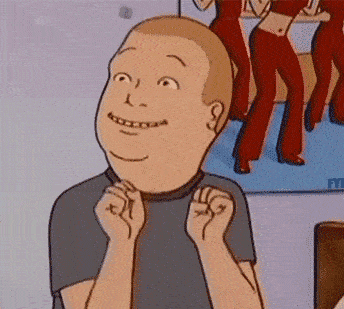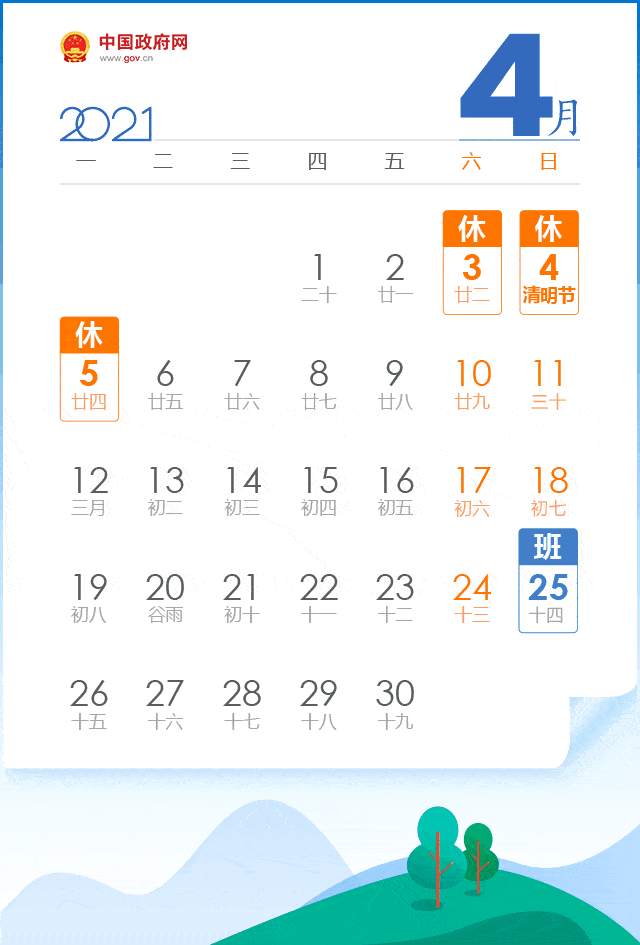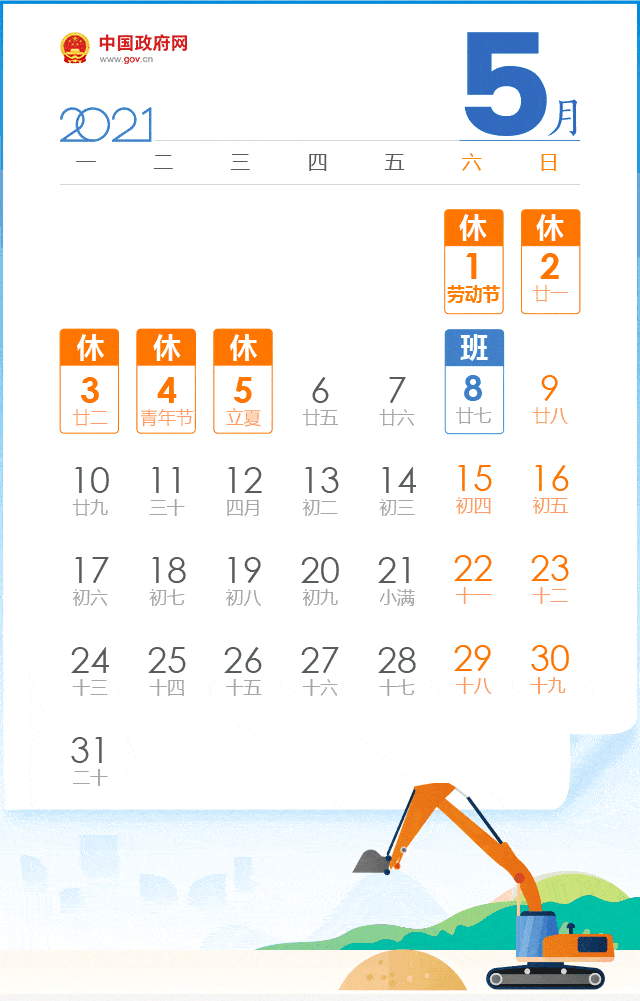捧着一本名叫《大河》的诗集,在油墨的芬芳里,我嗅出了母亲的乳香。
这条大河有一个磅礴的名字,黄河。
我是甘肃人,甘肃是黄河穿越的地方。我要看黄河,早晨八点多,从陇东庆阳出发,沿着古丝绸之路泾川、平凉、静宁、榆中,疾驰近五百公里,直到冬日霞光满天,才能在金城兰州一睹滔滔黄河的从容与不羁。
白塔山下,细雨绵绵,大河如龙,让人把心提得高高的,像羊皮筏子一样忽起忽落,不知将会发生什么……
黄河,于我而言,不仅仅是用眼睛去触摸,用呼吸去感知,而是一次漫长又沧桑的心灵漫步。我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每当想起,就有一股浓郁的乳香,让我沉醉。黄河,是我内心深处不可触碰的柔软。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的扎曲、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曲是康巴区域江河语音的汉译,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省区,然后注入渤海。
九曲回环,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程,它是雪山写给大海的信札,带着决然和毅然,把高原和水草的依恋,把沿途的山光水色,卷裹在十六亿吨的泥沙中,深情地呈现。每过一个地方,都要汇入和分支一股股河流,它知道这一番远足,绝无往返的可能,为了不让故乡过多地牵挂,它改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雪域高原的名字——黄河。
蓝天再大,大不过人心;大海再远,总想去看看。当这个念头突然被苍鹰携带的海风淋湿,如电光火石一般,一个伟大的梦想被点亮,一条河的命运就被注定,一段华夏文明史从此煌煌如炬。
饮马黄河,丝路凝重。一条路追逐着一条河,一条河依恋着一条路。从古到今,流过冬虫夏草,流过火锅,流过花儿和秦腔,浪尖上颠簸着丝绸、茯茶、青花瓷,一路向西。黄河,来到兰州,像是找到了落脚的驿站,把行李卸下来,烫烫脚,让牲口美美吃几把草料,回想一路风雨,一路惊险,心略略安了几分。
心安即福地。
黄河,是世世代代环县人的福音!
今年8月,我第一次踩着兰州黄河边的石头行走,把手伸进浑浊的河水,有一种美好的情愫瞬间温暖心窝。原来就是这股水呀,流淌在我生活过六年多的环县大地上,让数十万生灵对其感恩戴德。
聆听黄河,数字是枯燥的,历史却是真实的。
1992年7月,陕甘宁盐环定扬黄工程甘肃专用工程正式动工,十年九旱的环县,梦里激荡起水的欢腾,乳香的气息,日夜都在庄头村尾缭绕。1996年5月,从“塞上江南”宁夏而来的黄河水通到甜水堡,饱受干旱折磨和长期饮用苦咸水的环县人终于尝到了甘甜的乳汁,甜水堡昂首挺胸,名副其实。2011年10月,甘肃专用工程主管线通水, 环县北10个乡镇及县城 18.8万人,31.38万头(只)牲畜告别缺水历史。水,像活泼的孩子蹦蹦跳跳到人们面前,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老人几辈子,哪做过这般神奇的梦?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沿着明水渠,追着一股清流跑了老远,不想停下来,就想跟着它,看它流进谁家的桶里、缸里、锅里,看它用哪一种方式敲开一家一户的门,让老汉们惊大嘴巴、女人们痴了眼神、娃娃们赶紧找瓶子。我问一位工作人员:“这水干净吗?”他说:“水流百里自然清”。
从沙漠、戈壁滩到黄土高原,一滴水的晶莹,无数滴水在为之努力,为之牺牲。在环县,黄河流过的地方,西瓜特别甜,母亲怀中婴儿的笑脸格外灿烂。
《大河》的作者张海明,就是环县人,长期居住兰州。一条大河,穿过车流如织的马路,越过横跨大桥的栏杆,哗哗地流进他的诗中,流进这座幸福的城市。深夜的兰州城,飘着牛肉面的味道,混杂着羊肉串的腥膻,还有三泡台缓缓升腾的清香。那条承载着无数梦想的河流,乳香的气息愈发醇厚,安澜地将夜色一点点收拢,静静等待黎明的绽放。
□路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