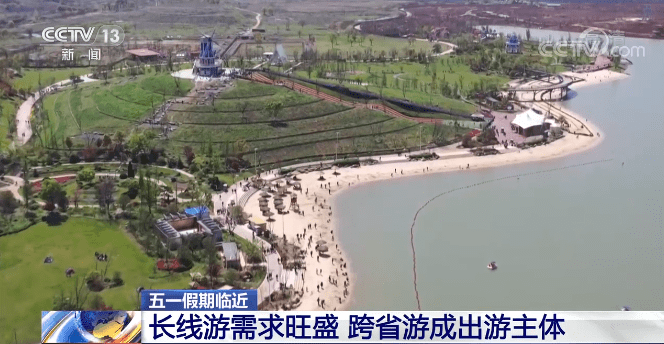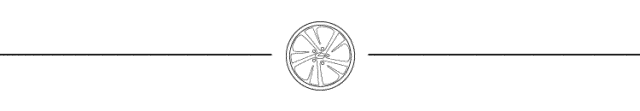上海迪士尼乐园创极速光轮,是迪士尼全球首发的项目,代表了高科技的最新运用 视觉中国图

1955年的《生活》杂志,刊出了加州迪士尼乐园“明日世界”中的“Carolwood Pacific”游览火车。它既代表了美国式的“乡愁”,也代表了开拓时代的探索精神。

《魔法王国的诞生:迪士尼乐园与美国文化》 [日]能登路雅子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 迪士尼乐园对科技的痴迷,与华特·迪士尼最初对火车的崇拜是一以贯之的。在迪士尼电影中,最像华特·迪士尼本人的角色,应该是《小飞象》的女主角米莉。这个从小立志当居里夫人的女孩,靠着最新的电影技术改革了传统的马戏团,也解放了在团里受苦的小飞象们。“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创始人对火车的迷恋上。后来,美国对海洋和宇宙的探索,都在迪士尼乐园中有所反映,而且也都处于美国当年探索西部的延长线上。” ]
直到当时的日本皇太子夫妇坐上加州迪士尼乐园的“旋转茶杯”,能登路雅子才敢相信,这座“美好到虚幻的乐园”竟然真的“存在于地球表面”。自1955年第一座迪士尼乐园在加州开业,到今天,它已经存在于世66年了。
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看到的迪士尼动画片和图画书,如今已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能登路雅子依然觉得它们“如梦一样美好”。那时候,她坐在家里“贫穷的小客厅”,守着黑白电视,眼巴巴地盼望动画片开场。迪士尼动画和日本职业摔跤比赛总是隔周播放。上一周她看到的是闪耀的迪士尼和美国那令人惊叹的富裕生活,下一周看到的则是摔跤选手空手劈翻美国壮汉的情形。这使得他们这些日本小孩对遥远的美国每周都要换一种心情,“一周因为落后产生劣等感,一周又因为胜利充满优越感”。
而在中国“80后”宋爱成长的世界,米老鼠、唐老鸭和白雪公主只留下一些辉煌的余音,各种海外品牌急速涌入她的视线,美国的、欧洲的、日韩的,《灌篮高手》《名侦探柯南》这样的日本动画片是她少年时代的“背景音”。但和能登路雅子一样,她也很喜欢迪士尼乐园。作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这座乐园代表的文化现象已成为她的学术兴趣所在。
从在昭和三十年代(1955-1964)度过童年的能登路雅子,到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宋爱,再到眼下涌向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小朋友们,他们未必看过很多迪士尼动画,却是迪士尼乐园的铁杆粉丝。究竟是怎样的“魔法”,让一座具有强烈美国色彩的主题乐园能够跨越世代和国界,拥有这么强的渗透力?这正是能登路雅子著、宋爱中译的《魔法王国的诞生》一书的研究主题。
屏蔽了现实世界的乌托邦
作为东京迪士尼的资深玩家,那里的游乐设施本身对宋爱来说早已失去新鲜感,真正吸引她的是那种投入另一个世界的“沉浸感”。乐园因季节变换而呈现不同气氛,这吸引着宋爱每一季都要去那里感受一下:春天的复活节季,乐园里四处可以看到“兔子蛋”造型;到了秋天的万圣节,“僵尸新娘”就会盘踞在每一个角落。乐园的每一个人,从游客到工作人员,都会穿戴卡通形象的服饰,像是约定了要共同投入到一场演出当中。
宋爱觉得,在东京迪士尼,想来体验“沉浸感”的游客不在少数。“虽然各个调查公司给出的数据不完全一致,但多个公司的数据均显示,乐园的回头客数量超过90%,10次以上反复到访的游客占比约60%。”在上海迪士尼,宋爱则看到很多年轻女性穿着lo裙和高中制服前来。她觉得,这也是寻找“沉浸感”的一种方式,“这两种装束都有青春无敌的意涵,代表着对漫漫人生中一个乌托邦时期的怀恋”。
“在东京、香港和上海的乐园,人是看不到外面世界的。”玩遍了亚洲三座迪士尼乐园的宋爱说。一个与世隔绝的梦幻之地,这正是华特·迪士尼对脑海里“快乐的地方”的设想。早在迪士尼乐园设计阶段,他就向工作人员反复灌输这个理念:“只要客人在这里,就不要让他们看到现实世界,让他们有在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多年来,这个理念已经成为迪士尼独步天下的“武林秘籍”,被一次又一次在世界各地成功复制。
在《魔法王国的诞生》中,能登路雅子具体分析了迪士尼靠什么营造出一个“独立王国”。比如围墙——“这里的围墙,跟电影院里的黑暗环境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是将虚构的世界与日常世界隔开的分界线。”还有倒三角的园区形状、只有一个入口的设计以及门口的隧道。在她看来,隧道就像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到的进入桃花源前的洞穴,只有走过去,才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而唯一一个入口,则保证游客能够按照迪士尼设计的“剧本”渐入佳境。
除了建筑和园区规划,乐园里的每一块屏幕、每一个工作人员,以至饭店的菜单和爆米花盒子,所有细节都会带上迪士尼童话的元素,参与到这场“造梦运动”之中。游玩时,宋爱常常会被一些小细节打动,比如一个冰激凌被做成唐老鸭一头扎进水里、只露出屁股和脚丫的形象,再比如有着绿巨人外形的馒头,等等。用能登路雅子的话说,进入乐园以后,人的味觉、视觉、听觉、嗅觉、触觉都会受到感染,乐园是在创造一个能够“将人的五感一手掌握的强效媒介”。
迪士尼本身就有许许多多经典卡通形象,更不要说,这几年还先后吞并了皮克斯、漫威、卢卡斯这样的巨头,这更让它成了动画IP的大本营。但主题乐园靠的并不完全是动画IP的魅力,吸引的也不只是儿童——事实上,它还有很多方法来激活成人身上的“儿童性”。在网上,许多网友写下了对迪士尼工作人员的印象:有人看到,一个女孩穿着公主裙走在乐园里,迪士尼的工作人员就会和她这样打招呼:“你好,公主殿下。”还有人看到,当一位唐氏患儿躺在乐园地上仰望天空,几个相继路过的工作人员也会陪着他一起躺下,安静地望向天空。宋爱则观察到,装扮成卡通形象的乐园工作人员一般是不说话的,“因为他们的声音会破坏游客对这个卡通人物原本的想象”。只有穿王子和公主服装的人可以说话,但也有固定的台词。
寄寓乡愁
在迪士尼乐园,火车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早稻田大学教授有马哲夫认为,迪士尼乐园本质上是一个“铁道博物馆”:几乎所有的游乐项目都是坐在一个交通器上,沿着固定的路线,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宋爱注意到,直到今天,蒸汽机车的意象依然会在乐园里频繁出现。火车对迪士尼来说意味着什么?在《魔法王国的诞生》里,曾经翻译过华特·迪士尼传记日文版的能登路雅子给出了她的解释。
她认为,对昔日美国的怀念,是贯穿整个迪士尼乐园故事世界的第一大主题。而这里的“昔日美国”,指的是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这100年的美国社会。在这100年中,工业文明迅速在美国的广阔荒野上扩散开来,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动力就是蒸汽机车和蒸汽船的运用。火车的轨道一路向西铺展,轰鸣的车头象征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国运,激发出无穷的希望与力量。
华特·迪士尼是成长于20世纪初社会变革大潮中的人物,在他眼中,蒸汽机车就是国家荣耀时代的缩影。第一部“米奇电影”是上映于1928年的《蒸汽船威利号》,片中的小老鼠神气活现,掌控着蒸汽船船舵。这类意象一再重复,甚至在 2019年上映的《小飞象》开头,依然有一列火车在夕阳撒下的金光中穿过沃野,铁路两边是仓库、麦垛和劳作的农民。火车带来的,是新鲜的物资、外出的亲人和外界的信息。
铁路所及之处,催生了许多快速繁荣的城镇。每个城镇都有一条中央大街,两侧林立着镇政府、邮局、理发店、杂货铺。快速富裕起来的居民在那里享受日新月异的变化。此后,随着城市化加速,往昔以中央大街为中心的乡村共同体很快消散,成了“美国少年共同的乡愁”。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以及插画家诺曼·洛克威尔的作品,等等,许多知识分子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一种扎根于美国风土之中的、质朴的生活方式,其核心意象就是“田园中的少年时代”。
在小镇长大的华特·迪士尼表达心中“乡愁”的方式,就是在加州的迪士尼乐园里复刻了曾经的乡村小镇,并把它安置在整个乐园的正门,起名“中央大街USA”。
走出“故乡”的迪士尼乐园
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全球化”,无疑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集中体现了美国文化符号的迪士尼乐园才能风靡世界,在一代代人心中成为“梦幻”“高级”的象征。即便如此,当迪士尼乐园真正走出美国,文化上的隔膜还是时时存在。
宋爱第一次到访的是香港迪士尼乐园。在园内玩耍时,她想去“冒险世界”看看。但她的小姑并不想去,她认为城堡区才是迪士尼最核心、最值得玩的区域。直到看了能登路雅子的书,宋爱才意识到,“西部世界”和“冒险世界”才是代表美国文化的核心所在,前者代表早期征服自然的美国梦,后者象征着文明世界对蛮荒之地的开拓。可小姑的想法也的确能代表很大一部分中国游客的期待:迪士尼就是公主的世界,为什么要到这里看“野人”?“我们与美国人并不共享同一套文化代码,所以会不喜欢‘野人’区域。”事实上,在后来建成的上海迪士尼中,的确对这两部分区域进行了大幅压缩。
相似的文化“冲撞”,还发生在2007年万圣节。香港中文大学学者Sunny S.K Lam曾在论文中分析了香港迪士尼与香港海洋公园的竞争。她认为,迪士尼之所以没能在香港“打赢”海洋公园,是因为前者的价值观就是美国式的阖家团圆,所以他们在制作万圣节主题时,不会把气氛搞得阴森恐怖。而海洋公园当年则主打“鬼屋冒险”,充满了刺激,这样的设置更符合亚洲的文化,吸引了很多游客。
在目前全球所有迪士尼乐园中,建成于1992年的巴黎迪士尼常被外界认为是经营失败的案例。早在这个项目开启之前,能登路雅子就在书中预言了文化上的矛盾:法国有着比美国更为浓厚的个人主义土壤,文化惯性比日本和美国更强,很可能带来更多的摩擦。“迪士尼乐园里不让喝红酒也不让喝啤酒,不让工作人员吵架还不让化浓妆,我们法国人可不能干瞪眼看着这种侵害自由的事情发生。”能登路雅子当时采访的一个法国人如是说。
《魔法王国的诞生》的考察截至1993年,彼时,迪士尼在美国之外的第二座乐园——巴黎迪士尼才刚刚建成。所以,其主要着眼点还在迪士尼乐园背后的美国文化因素,对进入东京和巴黎的情况虽然做了分析,但着墨不多。如能登路雅子所说,迪士尼现象正在进行中,这本书只能算是中期报告。
她记录下了当时处于经济增速顶峰的日本人对东京迪士尼的零星反应。比如,乐园刚开业不久,在见识了园内盛大的灯光秀和层出不穷的游玩项目后,一位日本老人发出这样的慨叹:“这下知道为什么打仗时会败给美国了。”而年轻人则不会这样想,他们只是沉溺在视觉和听觉的洪流之中。
1990年,迪士尼曾经收集了许多信息,想弄明白游客究竟会被什么所吸引。美国人的回答中,居于前列的是“园内的清洁度”“表演的有趣度”和“工作人员的良好态度”。而东京迪士尼开园五周年时,日本人提出的喜爱乐园的首要理由,则令人有些意想不到,其中最普遍回答是:够宽敞,够漂亮。比起乐园里的游乐设施具体传达了什么信息,日本游客更关注的是门口巨大的停车场。“处于经济上升期的人们往往更喜欢更繁盛、更巨大、更豪华的东西”,宋爱如此解读1990年代初期的日本人对东京迪士尼的反应。
对比眼下上海和东京的两个乐园,宋爱觉得,东京迪士尼和美国本土的乐园具有更高的相似度,尤其是在“造梦”这一点上:东京迪士尼的设计更注重一个“梦”的外壳,让人在“梦”中消费,而上海迪士尼拉动消费的方式则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她举了个例子,在上海, fastpass(玩热门项目的免排队通行证)可以花钱买到,也就是说,游客可以用钱来换时间;而在东京,fastpass一般是不出售的,只能靠自己提前到场排队领取。另一个细节是,在东京的乐园,游客不能外带食物,要吃东西只能在里面买。一方面,外带食物会提醒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不利于“屏蔽”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园区内外的食物价格差距不是很大,无需为了省钱而提前“备餐”。而在上海,因为2019年的一场官司以及之后的舆论批评,除了具有刺激性气味和需要加热、冷藏的食物之外,园区基本上放开了对外带食物的限制。
高新科技的试验场
可以说,自诞生之日起,迪士尼就不仅是个梦幻乐园,也是一个科技试验场。只是因为迪士尼穿上了一件充满浪漫色彩的外衣,其极具现代理性色彩的内核多少被忽视了。宋爱认为,对高科技的注重,正是乐园在迈出全球化步伐后依然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即便中国人对一部分动画片,比如《花木兰》这样出于西方视角的东方主义想象并不买账,但对乐园的喜爱却不见得会受到太大影响。”
从位于加州的第一座迪士尼乐园开始,痴迷于火车的华特·迪士尼就从未吝啬过在科技上的投入。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乐园曾花250万美元打造了模拟的深海探测潜水艇,用于“海底两万里”这一区域。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首次访美期间,突然提出要造访迪士尼乐园。为了迎接他,华特·迪士尼还特地“献宝”,计划让这8艘崭新的潜水艇公开露面,连台词都想好了:“赫鲁晓夫先生,这是我们迪士尼乐园的潜水舰队,是世界第八规模的潜水舰队。”不过最终,出于安全考虑,美国国务院和洛杉矶警察局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游览要求,后者因此十分愤怒,在记者会上发出连串质问。这起“国际纷争”为当年严峻的冷战局面抹上了一丝“黑色幽默”。
如今,迪士尼对高新技术的运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比如,在中国社科院编著的《中国新基建》一书中,就把这一点视为发达国家搞基建的重要经验,甚至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在一些技术运用的早期,政府并不需要花巨资购买不成熟的技术,而是把它们放在一些试验场中,观察其效用,也让公众逐渐熟悉。像线性感应电视、无人驾驶、轨道交通系统等我们如今已司空见惯的技术,最早就出现在1970甚至1950年代的迪士尼乐园。其他如单轨运输系统、发声机器人、电脑操控、无轨骑乘系统、虚拟现实技术等,都曾首先在迪士尼乐园试用,之后再扩散到城市交通、多媒体、航空航天等领域。
据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介绍,如今,在这座全球最新的迪士尼乐园,“创极速光轮”“飞跃地平线”和“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之战”都是工程师重新制作的高科技项目。其中“创极速光轮”是迪士尼全球首发的项目,“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之战”则被度假区称为“幻想工程师们有史以来设计过的最复杂的游乐项目之一”。
“每开一个乐园,迪士尼都是用最新的科技在打磨游乐设施”,宋爱说。她认为,迪士尼乐园对科技的痴迷,与华特·迪士尼最初对火车的崇拜是一以贯之的。在她看过的迪士尼电影中,最像华特·迪士尼本人的角色,应该是《小飞象》的女主角米莉。这个从小立志当居里夫人的女孩,靠着最新的电影技术改革了传统的马戏团,也解放了在团里受苦的小飞象们。“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创始人对火车的迷恋上。后来,美国对海洋和宇宙的探索,都在迪士尼乐园中有所反映,而且也都处于美国当年探索西部的延长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