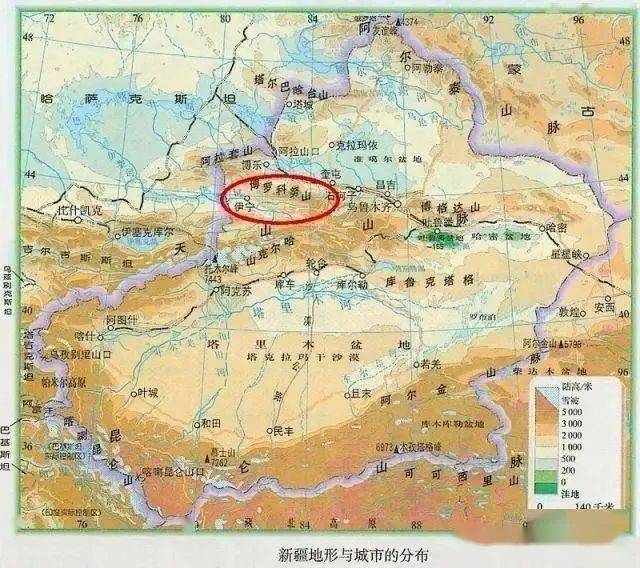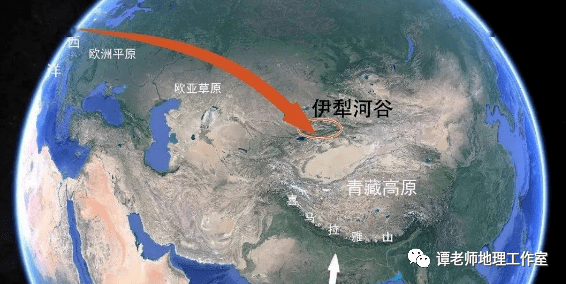成都人的衣食住行都跟锦江有着不解之缘,锦江是老成都人的捕鱼场,也是老成都人的游赏乐园。锦江上飘拂过旅人惬意的笑声,也洒落过生离死别的泪水。
水上欢声
锦江穿流市区,像两条修长柔软的手臂,将老城区紧紧环绕,最后在九眼桥附近的合江亭汇合。两江环抱、水色空朦的气象,最令成都人骄傲。老成都人的衣食住行都跟锦江有不解之缘:灌溉、行舟、漂木、饮用、洗漱、游乐……哪样离得开“二江”呢?
合江亭附近的水津街是老成都的柴市,旧日市民用作主要燃料的木柴多由岷江漂送。每当夏季丰水期,顺流而下的漂木在江边随着波涛起伏冲撞,船工们赤着上身,用带钩的竹竿将原木收集拢来,场面十分壮观;不远处的太平下街是竹子市,江中江岸满是竹排、竹筏和竹子堆成的小山;临近还有热闹非凡的盐市、米市;东门大桥的鱼码头则是鱼、虾、蟹、团鱼的天下,活蹦乱跳的水族时常引得小孩垂涎欲滴;北门大桥附近有大安米市,下游的小南海菜蔬码头,堆满新鲜又便宜的时令蔬菜……水量充沛的岷江,将积雪消融的沁人清流源源不绝地输往成都,也将水的生机与欢愉送达古城。
锦江是老成都人的捕鱼场。成都处于内陆盆地中央,境内水脉纵横,不乏鲫鱼、鲤鱼、鲢鱼、黄辣丁、泥鳅、虾、蟹之流。清末民初时南门大街、湖广馆、棉花街等都有鱼市,但鱼类在老成都人的饭桌上并非天天可见,它们是待客的佳品,是寻常人家的上乘菜肴。
老成都人捕鱼的方式五花八门,捕鱼工具有虾耙、罾、网、钓竿、渔叉、豪子等。因为鱼虾多,就是用手捧、用木棒或石头打、用筲箕撮,都能有收获。最有趣味的是鱼老蛙船、鱼猫子船,捕鱼人专饲鱼类的天敌为捕鱼工具,效果当然奇妙无比。远离大海大湖,老成都的捕渔业未能脱离小打小闹的家庭作业方式,虽成不了大气候,倒也别有一番风味。锦江的鱼有多大呢?据当时人们的回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九眼桥一带水域曾发现过一米多长的大鱼,一两尺长的鱼当然就平常得很了。
锦江也是老成都人的游赏乐园。“游锦江”是市民的至爱,这一风俗可以追溯到唐宋。清末民国时,游锦江、赛龙舟依旧是让人陶醉的盛大节目。从万里桥开始,游江的画舫和喧哗的笑语填塞锦江,岸边人潮涌动,往往入夜后仍然弦歌不绝。
陆游曾为之迷醉的“青羊宫到浣花溪”,到后世风采不衰。明代散文家钟惺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来成都公干,也曾兴致勃勃出南门,沿江西行寻访少陵草堂、武侯祠。他的《浣花溪记》描述:锦水漫江碧透,曲折婉转,或远或近,一路相随。从万里桥至青羊宫一线,“竹柏苍然……水木清华,神肤洞达。”再往前行至草堂一带,更为清幽,房舍树林掩映流水,竹篱板桥,水槛木亭,都别有风致。清末民国学者赵熙则这么吟咏那一带的景致:
青羊一带野人家,稚女茅檐学煮茶。
笼竹绿于诸葛庙,海棠红艳放翁花。
依旧是花艳竹翠,一派田园野趣。不论在不在花会期间,成都人对青羊宫到浣花溪的兴致都是不低的。
除了水,浣花溪一带的风物以杜甫草堂,以花木和幽深取胜;城东望江楼附近也占尽锦江春色,成为另一个诱人的去处。纪念女诗人薛涛的古井在明代已是名胜,与之毗邻的胜迹,还有几处清代嘉庆年间兴建的亭台楼馆。薛涛井乍一看也无特异之处,但是据说它很神奇——即便天旱,井水水位依然很高,距井口不过一尺多,而且取之不竭。而井水之清冽甘美,更是胜过锦江水百倍。所以,薛涛井畔的茶园,往往座无虚席,旁边还有五间大厅,是供人品茗的雅座。每逢乡试期间,井水还要被运往市中心的考场,供考官等饮用。那时节,薛涛井边还会派驻专门的守护人员,不许寻常人等随便来挑水。
光绪年间,薛涛井附近又建成崇丽阁(俗称望江楼)、濯锦楼,重建了吟诗楼等,与明代亭台相互辉映,加上曲径通幽,修竹疏篱,很引人流连。崇丽阁在原回澜塔旧址上修建,得名源自左思《蜀都赋》的“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它近40米高,飞檐高悬,气势恢宏,雕梁画栋。登上高层俯瞰江水东流,似觉水汽蒸腾。远眺望百里外的青山,翠色扑面而来。
据说四川文风虽盛,清代却没有出过一位状元为地方增色,士绅乡贤深以为憾。而本地有一传统,凡大型公共建筑落成后,都必定要请名公巨卿率先登临,以求吉祥。这一年的四川乡试副考官为贵州第一位状元赵以炯,众人议定,待考试结束,赵状元一出闱,就请他登上崇丽阁。果不其然,沾了赵状元的喜气,没过几年,四川就出了清代唯一的状元骆成骧。
九眼桥外本来就是东去的水码头,在古刹雷神庙饯行、接风的人每天络绎不绝。自崇丽阁等建成后,水榭风亭又添奇趣,来江边郊游宴饮的人日益增多,冠盖往来,车马驱驰,茶馆饭店生意异常兴隆,更有各方名士为亭台楼阁题咏、撰联。晚清著名诗人、书画家顾复初为濯锦楼题联:“引袖拂寒星,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停琴伫凉月,予怀浩渺,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写景言情都与江畔的胜迹分外熨帖。望江楼这一“岁时游宴及离樽送行之所”,更趋繁华。1928年,望江楼一带辟为郊外公园。直到今天,望江楼公园的建筑群体,大体格局仍与光绪年间相仿。
帆影点点
锦江上飘拂过旅人惬意的笑声,也洒落过生离死别的泪水。
两江水量充沛,冬季也能行船,九眼桥下游水深数米,因而两江上航行极盛,樯橹如林,帆影点点。向下游运旅客和百货,从上游输送木柴、盐巴、农副土产的大小船只,一年四季穿梭往来。即便到了1950年代初,成都至乐山段仍可通行10吨左右的木船。
拉着上行船的纤夫,赤脚过沙滩、涉浅水,步履沉重坚韧,挣扎着弯向地面的脊梁,已被阳光镀成釉亮的紫黑色;顺水行舟的划桨人就从容得多了,他们用乐山话唱出的小调(当时船夫以乐山一带人居多),有轻松的戏谑色彩。船上的旅客在这种悠然的氛围里,最能体会到船出望江楼后扑面而来的野趣:竹外桃花、春江水暖、家禽戏水、杂花生树……
载客船有大有小,小的叫“半头船”,可容纳五六人住宿,大船则一般只包舱面给坐客,底层由船主揽货。比较而言,下水船比上行船价格略便宜,船家供饭,菜蔬由客人自办,停泊起行,一般唯客命是从,所以沿途游览、购物很方便。
1912年夏,儒教的叛逆者吴虞应邀前往乐山,以排遣郁悒。毕竟是不赶时间的从容出行,按照当时惯例,第一天中午启程,泊船于望江楼下,接着登岸游薛涛井,到方公祠饮茶,晚间歇息。第二天一大早开船,到苏码头上岸早餐,夜泊张家坎。这天午后还有点逆风,否则可能还不止日行190多里水路。第三天又是绝早开船,在刘家场登岸用早餐,午后3点已抵达乐山——严格说来,水上行程仅两天。虽说在出行者和亲友眼中,到一趟乐山的概念,跟交通发达的今天不能同日而语,但在当时,这是费时既短又颇安全的旅行,“去省(城)近而无滩险也”。此前,吴虞因为跟父亲诉讼公堂,反目成仇,被斥为名教罪人,遭逐出教育界。这次得以变换环境,在乐山还去会友、游览、购物等,令一向心境愤懑的他稍觉舒服。
由水路出成都,东门外水神寺也是一大码头。1929年6月底,李劼人等利用暑假出川为成都大学(后并入四川大学)招聘教员,便是从这里启程。校长张澜与吴虞、魏时珍等同事与他们在河边茶馆饮茶、送别。
抗战期间,四川大学迁至峨眉,一些从成都返校的学生总是结伴而行。少年心境毕竟澄明如镜,几枝芦苇,一尾银鱼,半畦菜蔬,都会让他们心情不错。假如你看见那些一向调皮的男生多少有点拘谨,拘谨中又暗含喜悦,那就一定是有女同学同船了。在男女同学和悦的交谈中,两岸风光不知不觉退向脑后。晚上,江月朦胧,船上的文艺晚会却热烈明快。外语系那个戴眼镜的男生用英语朗诵《罗密欧与朱丽叶》,赢得旋风般的掌声;家住青石桥的中文系腼腆女生不唱川剧,却清唱了一曲大家都熟悉的《苏三起解》,竟看不出她的嗓音这么响遏行云。家麟对住在隔壁森严的秦公馆里的蕙小姐早有好感,离开望江楼他就开始惴惴然——没有想到跟她同学了,此次竟又同船,能否更接近她些?可惜才两天就到目的地了,只恨水程太短,行船太快。
假如不是安全系数较大的短途旅行,而是出省出国呢?那就令送行者和旅人都唏嘘不已了。在望江楼解缆挥桨,不知要经过多少曲折才能抵达万舟排列的朝天门码头;又不知要历经多少惊险,才能穿越漩涡湍急的三峡,驶入江天一色的长江下游……
行旅的艰难与漫长,令告别的场面总是凄凄切切,所谓“多情自古伤离别”。1903年夏,四川选送到欧洲留学的一批青年学生,也是从望江楼出发。他们经过城里各方知名人士宴请后,哭别祖宗祠堂,上完了祖坟,与亲人洒泪告别,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登上大木船。包着铜角的漆皮箱和存放皮袄、丝绸长袍、马褂等冬装的樟木箱,都被船夫运上了船,用绳子拴在船板的铁环上,与其他旅客携带的成包的丝绸、成捆的烟叶堆放在一起。他们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航行,经重庆、下宜昌、过汉口、抵上海,最后乘洋轮去欧洲,直到次年2月才到达目的地。
王鹤/文 本报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