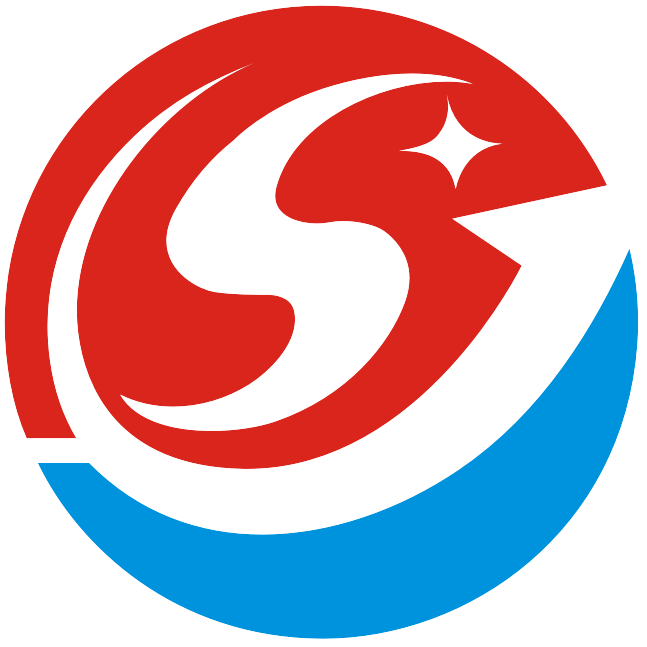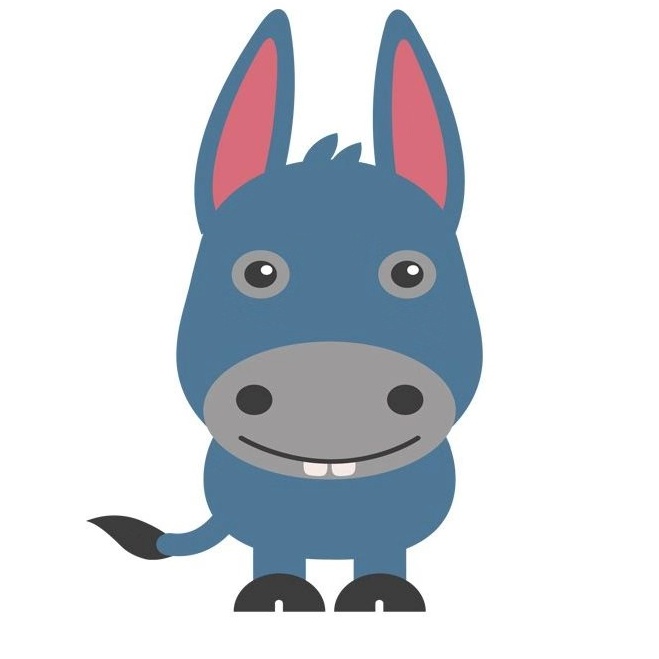正午,清阳楼上。
林子森在此宴请襄阳府内杜尔慷等几个行业巨头。
清阳楼历史悠久,楼内古朴典雅,是名士吟诗作对聚集之地。前朝时期,曾有名士在此题句:尝遍神州风云味,独尊清阳第一楼。更使得清阳楼名气大增。
主客到齐,分宾主落座。 林子森起身,拱手向四周,笑道:“几日不见,诸位可好?” 众人忙起身应道:“托大人洪福,一切都好。”
林子森接着道:“今天鄙人在此宴请各位,大家不要拘礼,我们今天以朋友想称,一切随意。”
趁说话间,白如银从怀中掏出一精致饰盒,朝向林子森打开,正是雪儿前日在善来银楼看中却因太过昂贵而未买的银饰,说道:“听说令师妹来此游玩,我等未能尽地主之谊,深感不安,烦请知府大人将此银饰转交令师妹,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还望令师妹玩的愉快。”百如银是个精明的商人,一件首饰,换的两个人的心,划算!
林子森忙用手推回,正色道:“那怎么行,白老板这不是将我置于不义之地么?才上任几天,就给落下个贪的口实,不妥不妥!请快收回!”
“我们都知道大人您清正廉明,我等又怎敢轻毁大人名声呢?大人刚还说了,今天咱们以朋友相交。这纯属私人情义。大人不收,是看不起我这经商之人了?”白如银作色说道。
“不不不,同城之内皆兄弟,只是此物太过昂贵,鄙人收受不起啊。还请白老板收回。”林子森急说道。 “大人既如此说,那我就将此物折价卖与大人好了,这银饰本是我白家工艺制成,就收大人十两银子的成本费好了。”
“这.......” “大人若仍不肯收下,就是不给我等脸面了,那我等只好起身告辞了。”白如银作起身欲走状。
任师爷忙打圆场道:“既然这样,看在白老板一片诚心的份上,大人您就收下吧?”
“这.......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任师爷,呆会取十两银子交给白老板。”
“是,大人。”任师爷应声道。 “好了,菜已上齐。诸位请用。我来此几日,可是还从未认真品尝过贵地的佳肴,今日可得一饱口福啊!”林子森拿起筷子。
“大人初来可能不知,襄阳地处南北要塞,南北各路商贾齐聚此地,襄阳可是齐聚南北各地佳肴啊?”杜尔慷说道。 “呵,是吗。那我可得好好尝尝了,来,大家不要客气。”说罢,林子森将筷子向红烧鲤鱼伸去,手到中途,却停住了,因为他们都不动,只是近似尴尬的看着他。
“怎么,怕我在菜你下毒?”林子森脸上的笑容有些凝固。 “不敢,大人。只是自古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大人此次宴请我等,只怕也但是为了吃喝吧?想必也是有事相商。何不说个明白,大家好吃个安心席。既然大人能诚心相邀,有什么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何不爽快说出,能尽力处,我等绝不推托。”杜尔慷语气极是谦恭,肥胖的脸上淌下几滴汗珠,如油腻般。精明的小眼睛直视林子森,有所惧又有所不畏。片刻,又即垂下。其余各富商也忙称是。
林子森知道,这是他们对把兵士撤走感到不满,借题发挥呢。借兵士与他们,看似小事。实则表示了官府和富商暗为一体。这次突然召回兵士,不能不令他们疑心。
林子森沉吟片刻,沉声说道:“既然各位如此坦率,那我也就直言相告了。”林子森脸上笑容不退,继续说道,“诸位想必已知,诺大一襄阳知府,现在只不过是一空架子。大灾三年,民不堪命。我即身为地方父母官,不能置百姓生死于不顾。无奈,我个人能力实是有限,勉强开仓施粥实是权宜之计,却也难以维持长久,朝廷赈灾之粮迟迟不到。说不得还得仰赖各位相助。”
“大人即如此说,我等若执意相拒,实是不仁。只是请大人明示,我等该如何相助?”白如银微皱眉头,缓声说道。白如银能在二十来岁就继承父辈产业,除了其雄厚的家力外,其个人的能力也绝不容忽视。今天要说服他们,着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好,白老板够爽快。我只想向各位借资白银五十万两。以粮代替亦可,务必请各位于三日内凑起。我好做赈灾之用。等朝廷赈灾之款到后,一并奉还。”林子森坦声说道,双眼如鹰般盯着在座各人。
“这.....嘿,大人想必也知,灾年之际,生意实是难做。大人您这是让我们为难呀?”王之贵丝毫不惧,阴声说道。
“五十万两,数目确实不小。但于各位而言,却也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前任知府每年从你们这拿走的贡银怕是就不止这个数吧?师爷,你是三任知府师爷,我说的该不会有错吧?”林子森将头转向师爷。 “大人所言不差。”任师爷忙点头答道,心里却暗暗吃惊。这些事,自己从未向知府提起过,不知知府从何得知。这一点头不打紧,只怕这些个大富商都会以为这是自己向知府抖漏的。果然,任师爷一抬头,就看见杜尔慷等人正怒视自己。任师爷不得机会辩解,只得暗叹倒霉。
“知府大人,你该不会是强逼我等借款吧?”王之贵语气更加阴森,已隐隐透出极度不满,怒火一触即发。 “王当家的,”林子森似笑非笑的说道,“您这是说哪里话,小弟虽识字不多,阅历尚浅,却也知律法至上这一准则,又怎敢做违纪之事,今日借银,全凭自愿,小弟又怎敢有威逼之意呢?”
“我等若是不愿呢?”王之贵说话丝毫不留余地。
林子森踱步接口说道:“各位都是商海之人,商人重利,但却无名,因而做事艰难;我乃为官,有名却缺银,步履也艰。假如我们得以互补,岂不甚好?”
“小的愚钝,只是不知大人何意?”杜尔慷看王之贵又待发话,怕关系弄僵,忙接口说道。
“你们今日借与我,哦,不,是借如襄阳知府白银,我得银,让你们得名。”林子森浅笑着说道。
“只是不知名从何来,有何意义?”白如银试探着问道。
“你们若肯借银给我,我给你们一个承诺,从此以后,你们在襄阳府内经商,只要是正当生意,任何人不得无故盘剥。境内大小官员见你们须行上小之礼。申报朝廷,让你们做真正意义的红顶商人。”林子森正脸说道。 为商之人都明白,商人经商,不怕生意难做,就怕官吏盘剥,商人立于世,一官一吏都不可得罪。三教九流中,数商人地位最为地下,连妓女从良,也是最后才考虑商人。因此,一个“名”字,对商人实是有着莫大的诱惑。
杜尔慷看看王之贵,又看看白如银,笑道:“大人这是要我们拿钱买名咯?只是大家都知,生意之人狡诈,却远不如官场之人阴险。这个‘名’也只是大人的一句话而已,我们又怎敢把他当真。这话还请大人收回。”
“杜老板,你是不相信我林某人了?我林子森怎么说也是一个知府,说话岂会如儿戏?”林子森似乎有些恼怒了,“你们做生意,讲一个赌字,赌对了,利滚滚而来,你们何不就在我身上赌一把呢?三五十万两银子对你们来说也不什么大数目!”
“关键是我们得知道值与不值。”王之贵说道。
“值与不值,看你们怎么想了。我林子森今天是诚意与各位相交。就看你们愿不愿意了。”林子森来回走了数步,仰了仰头,吁了口气,“诸位都知道,近日来,佛衣教活动猖獗,常聚集教徒与八万山,有叛逆之兆,余总兵,具体的你和他们说说。”
“是,大人。”余总兵虎目扫视了一下四周,说道,“自上个月来,佛衣教的活动益加频繁,聚会的次数明显增多。他们的教主也已从四川赶回,据可靠消息,他们近期内将会有大动作。如此以来,他们第一个要冲击的恐怕就将是你们的粮仓,银饰行,钱庄了。到时,仅凭你们那几白个护院,恐怕是难以阻挡吧?”
王之贵暗哼一声:“大人,若真如此,只怕襄阳知府也难避祸患吧?嘿,到时,只怕先遭殃的不是我们了。”
“哈哈”林子森大笑几声,厉声说道,“王大家的,我有一件事要事先申明了,听说你们每个月都要向佛衣教交纳一定的所谓‘保护费’什么的,不知是否可有此事,若真属实,等佛衣教叛乱之日,我上报朝廷,将惠众法师等人定为叛逆之人,你们到时只怕也难逃‘私通匪患’的罪名,那可是杀头,株连九族的大罪啊。你们可想清楚了。即便我不报,等到叛逆起事之时,他们恐怕也不会顾及你们往日的‘情谊’吧,那可都是些疾富如仇的人啊。你们可想清楚了?”说罢,林子森眼内精光四射,直逼视杜尔慷等人。
“大人,你这是软硬兼施了啊?只是我们也不吃素的,大不了我们就远走他乡。”王之贵猛地起身,怒气冲冲的说道。
“你们的根可是在襄阳啊,根断了,只怕到哪都难以成活。更何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又能走到哪里?”林子森丝毫不惧,扬声言道。
“哈哈哈,”杜尔慷起身抖了抖肥胖的身体,笑道: “王兄,少安毋躁。知府大人言重了,既然知府大人能以诚心坦然相劝,我等若再不识趣,就显得不明事理了。好,我出银二十万两,以粮食代替,可否?”
“好好,杜掌柜果然是识大体之人,林某在这里,代替襄阳百姓致谢了。”说罢,林子森将头转向白如银等人。 杜尔慷忙以目示意王之贵等人,白如银无奈的说道:“我也出银二十万两。”王之贵暗叹一声,也只得同意出银二十万两,其余个商家也都愿出银不等。
“好,很好。”林子森脸上浮上了笑容,拱手说道,“感谢各位的仗义出手,林某言谢了。来,把酒斟上,我诚心敬各位一杯,聊表谢意。”
“好,干。”杜尔慷等人恨声说道。
“就是嘛,官商一体,方能使一方繁荣啊!哈哈哈!”林子森笑得有些放肆。
“大人所言极是。”任师爷忙乘机奉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