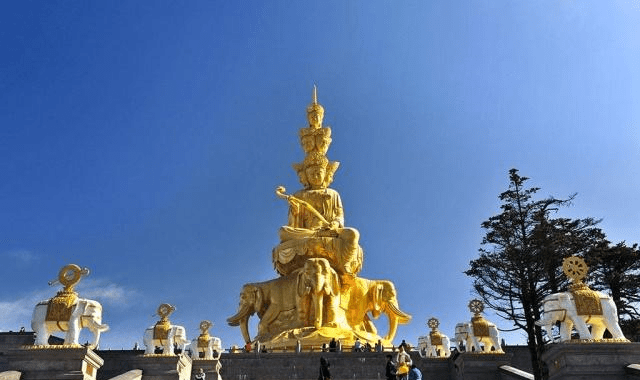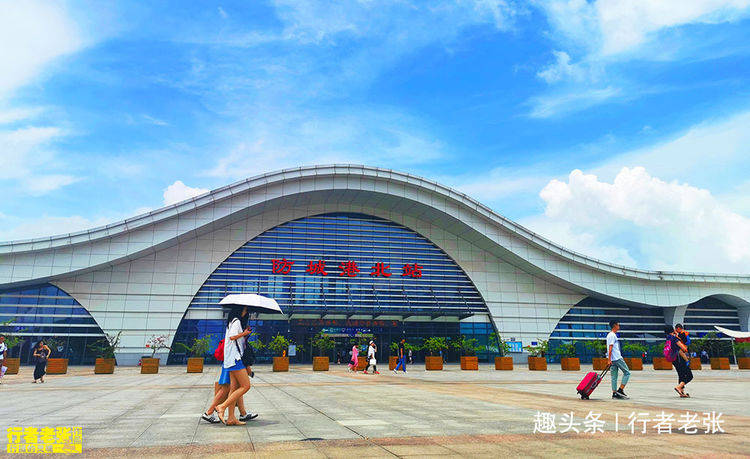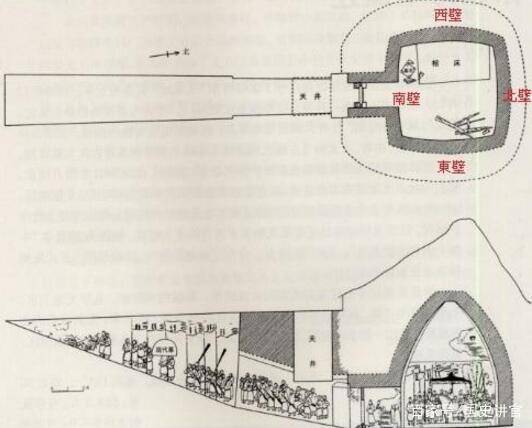襄阳古城,历来就是卧虎藏龙之地。论及当世,最有名气的却既不是拥有近万名信徒的佛衣教教主惠众法师,也不是富甲天下的襄阳商道三领袖杜尔慷,白如银,王之贵,而是年方二十的襄阳新任知府林子森。 林子森十二岁中举,十八岁榜眼,二十岁放任襄阳知府,其经历之奇,其路途之顺,令人羡慕,更令人妒嫉。当然,林子森能以二十弱冠之年执掌襄阳这个多事之地的知府帅印,凭的恐怕并不只是幸运!

这天,是林子森初来到任之日。粮商杜尔慷引领襄阳府内各富商在清阳楼大摆宴席为新任知府洗尘。
近几年来,襄阳境内一直闹天灾,民不聊生。佛衣教乘机而起,明里教化民众,暗里聚集滋事,多次密集乡民冲击府内县衙。各路粮商更是伺机哄抬粮价,愈使得民生维艰。正是这个人见人避之地,林子森却主动请缨而来,人尚未到,其传奇经历早已在襄阳传的沸沸扬扬。杜尔慷等人此次宴请新任知府,一为巴结,二来也想探个虚实。自古无官不成商,官商相护,杜尔慷等人更是深通此道的。
汉江楼上,灯火辉煌。汉江楼内,笙歌艳舞,觥筹交措,好不热闹! 宴会已入高潮,杜尔慷起身,微醉着道:“林知府能来我们襄阳就任,是我们襄阳人的福气,更是我们的福分。今后还得仰仗林知府多多照应。”林子森忙欠身正色道:“维护一方安宁,促进一方的发展是我的职责,我初来贵地,还得依赖各位支持呀。”白如银和王之贵对个眼,齐起身道:“好,来,为我们以后相互的支持干一杯。”酒杯碰撞声如夜鹰尖叫般再度响起。
席终人散,林子森半躺半卧在太师椅上。正在听任师爷对襄阳的情况简报。 襄阳连遭三年天灾,百姓逃荒,饿死者难以计数。商贾居奇;兼有匪患;朝廷又赈灾不力,就连兵饷也时时被扣,民怨兵急,时局十分不利。 师爷边说边察观知府脸色,林子森神色安详,喜怒不现,双眼微闭,表现出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成熟。真是个难以揣摩的主子,师爷暗想。不能时时揣摩出主子的意图可是身为师爷人的大忌!一个师爷可是半个知府啊!
想到此,任师爷试探着问道: “大人,襄阳现在的局面很是混乱,我们该怎么做?” 林子森缓缓起身,微笑道:“这正是我想问你的问题,你是三任知府的师爷,说说你有什么高见?”林子森不是个爱笑的人,但不论何时,总能保持着笑脸----尽管有时很压抑,很痛苦,久而久之,这笑反倒成为一种习惯。 师爷一愣:“这...........属下愚见,一切听从知府的差遣。”做师爷的都明白一个至理,那就是一定要表现的比主子后知后觉。你再聪明,也不能在主子面前表现出来,不知为不知,知之也为不知,否则便是自作聪明。任师爷历任三任知府师爷,更是懂得这个道理。
林子森悠悠说道:“天灾犹可避,人祸逼死人!”说罢暗叹一声,声音似乎有些压抑。 师爷诧异的望向林子森,不明白这个人祸具体指的什么,却又无法从知府的脸上捕捉到有效的信息,还想再问,林子森已打断他道:“今天收贺礼多少?” “富贵粮行杜尔慷送白银两万两,善来银楼白如银,如是钱庄王之贵各送白银一万两,其实多少不等,合计有五万多两.....”任师爷小心翼翼的答道。 “够阔绰的了。”林子森冷言道,“全部收下,充当库银,对了,府内库银还有多少?” “不足一万两,还拖欠官兵饷银......”
“哦,知道了。我累了,先歇了。”林子森边说边朝内室走去。 任师爷赶紧起身退下。跟随知府这几天,任师爷一直都没摸透知府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外面,无论遇见什么人,林子森一律笑脸相迎,笑容自然得无一丝虚假可寻,谈吐温文尔雅,一派大家风范,在无人处,偶尔又似禅定之人,少有喜怒颜色。是个怪人,师爷心里想。想不通就不想,揣摩不透,就顺其自然。不能真聪明就假糊涂,这是任师爷做人的一贯准则。
翌日,久旱的襄阳境内降下了第一场雨,丝丝绵绵,不大,却很喜人。
襄阳城内,贴出一张新布告:“新任知府到任,大办粥厂施粥,赈济灾民,直至稻子成熟。” 饥民诧异,疑是眼花。官府施粥,历来是少则三五日,多则一月。待到稻子成熟,还有近三个月,这等施法,从未有过。是真是假,时日一到,既可得知。
施粥当日,知府冒雨亲临。一个大空地上,临时搭起一个小台子,支起三口大锅,大锅两侧,早有布置两列官兵,以防饥民哄抢。 辰时,第一锅粥熟。林子森立于锅旁,取一筷子,插入粥中,筷子直立,人们欢声雷动。林子森示意安静下来,沉声说道:“各位乡亲,我林子森在此向大家保证,在我任期之间,襄阳府内决不会出现一个饿死之人!”声音不大,却清晰印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脑海中。全场再次欢声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