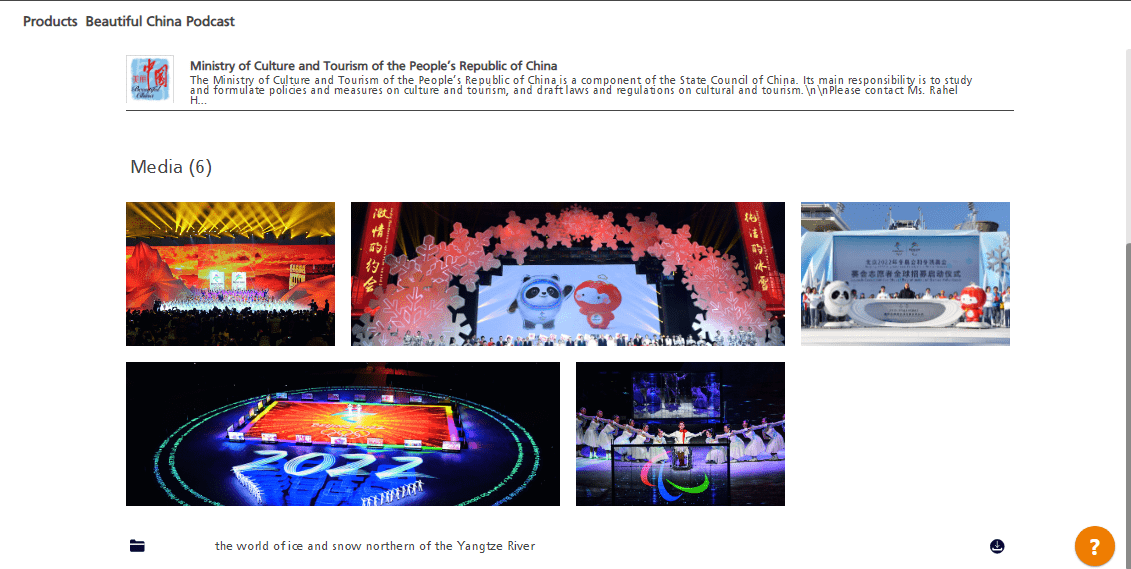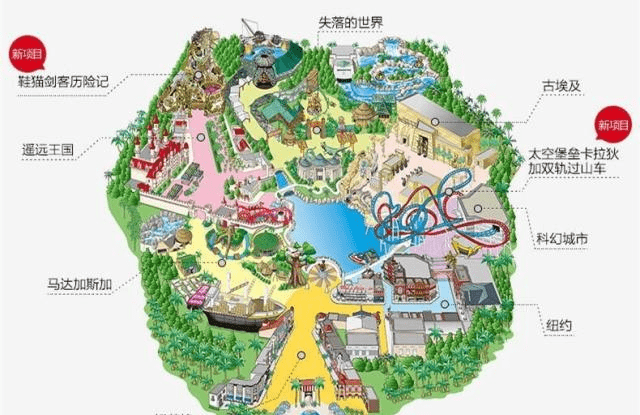引言
提起成都,人们自然会想到它响亮的别称-锦城。说到锦城,则又必然会想到与之密切关联锦江。假如把锦江比作一位雅艳的姑娘,那么,浣花溪、百花潭便是她的明眸笑靥,最集中地展现出那美丽的灵魂。研究成都的城市展史,离不开研究锦江,特别是研究浣花溪一带的文物古迹。
“浣花文化”几乎可以说是“锦城文明”的同义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既不是人们想当然的主观比附,也不是历史行程的碰巧偶合,而在于文明发展的内在结构:物质文化的强固关联和精神文明的历史积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任何一种文化的基础。
从农业、手工业(如织锦、造纸)航运交通等方面看,锦江都给历史上的成都提供了物质文明发展的条件。四川水量最大的河流岷江,盘绕千山万壑从岷山奔腾而下,到达川西平原。经过都江堰的疏导分流,道道清渠如扇面展开,似叶脉匀布,浸润着成都周围的农田。《华阳国志·蜀志》称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这“检江”在成都城附近的一段就是锦江。
由于二江“灌溉三郡”,才使得“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宋人范成大描绘他由成都西到永康军(今灌县)所见景象时说:一路江水分流,入诸渠皆雷轰雪卷,,美田弥望。”“流渠汤汤,声震四野,新秧勃然郁茂。”《吴船录》这说的是锦江上游的情况。而杜甫诗中“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则又可以看到浣花溪一带的状况。

总而言之,有了包围着锦城的肥田沃土,才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成都坝子发达的农业生产。如果说,川西平原的灌溉之利是由锦江与其它兄弟河道协同造就的话,那么,“濯锦”的功能,就得让锦江特别是浣花溪一段江流专擅其美了。
前些年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铜壶上,有生动的采桑图象,成都曾家出土的汉代画象石上有石刻织机图,而甲骨文上的“蜀”字就是绘的蚕的形状。这一切说明,川西地区植桑养蚕以织锦的历史可以推到很古很古,经由战国到汉代,则逐渐进入鼎盛时期,故蜀汉有,“锦官”之。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这就是锦江、锦城、锦里的由来。左思《蜀都赋》写道:“阛阓之里,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这说明文学家已开始对锦江边上兴盛而有特色的手工业予以歌赞了。历唐到宋,发展规模更大,见诸文学作品者更多。
刘禹锡《浪淘沙九首》之五:“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在同类作品中,这要算最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张何的《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则了织、濯、晒的全过程。其中写“濯锦”一层:“言濯春流,鸣环乃出,于是近深沉,傍清泚。朱颜始映,珍箧方启。

其始入也,疑芳树映落涧中;少将安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夺五云长风未散;泫百花徵雨新洗。作家以这样宛转的情思,优美的言词,瑰丽的想象来写濯锦,正说明这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锦江、锦里之名,在成都史册上更加显得鲜明耀眼了。织锦的主要原料是蚕丝。
织锦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原料的生产。于是,桑苗、蚕种、蚕箔等等的系列交易,便在锦江两岸繁荣起来了。这种以“蚕市”命名的季节性交易大会自唐代开始发展,五代寝盛。先由蚕桑、农具的买卖,扩展及于药品、花卉、百货、酒食,进一步更增加了许多歌舞游乐的内容。
五代时韦庄的《怨王孙》词,就写到当时蚕市的盛况: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珰,绣衣长。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队行云散。不知今夜,何处深锁兰房,隔仙乡。这一类锦里风光的镜头,活画出了浣花溪两岸繁华游乐的热闹景象。入宋以后,蚕市还有变化,一是时间拉长,自正月到三月不断;二是地区扩展,各寺庙更番进行,循环多处;三是贸易范围更广,游乐性更强。
宋人题咏蚕市之作更多,兹举苏东坡诗友仲殊和尚《望江南》词,以见一斑: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人散后,茧馆喜绸缪。柳叶正绕烟黛细,桑条何似玉纤柔。立马看风流。资锦水为条件的手工业,除了织锦之外,就要算造纸了。从隋代起,四川造纸业迅速发展,到唐朝,已居全国前列。近年来成都出土了许多当年造纸作坊的大石臼,其地址恰好在浣花溪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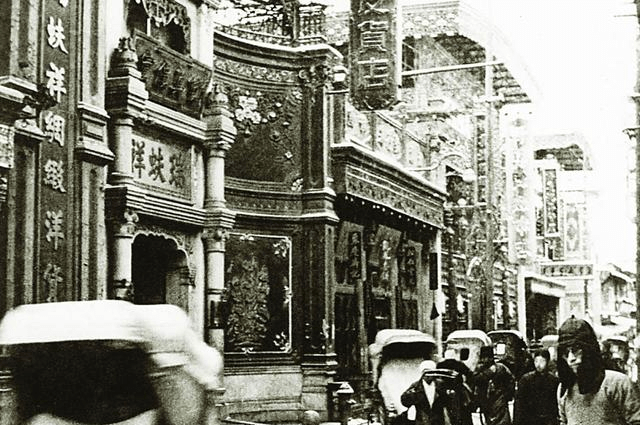
这绝非偶然。造纸要用大量的水,就得依傍锦江。上等麻纸的原材料,出产在川西平原。以锦江为航道,既便利原料的供应,又方便产品的输出。唐代中央政府的高级用纸,主要靠这里供应。在这样发达的造纸手工业基础上,女诗人薛涛才创制了有名的“薛涛笺”。此笺一出,风行全国,流香千载,历代诗人题咏不绝,成为文苑佳话。
浣花笺纸,百花潭水遂与浣花溪、锦江一样,名播人口了。造纸业的兴盛,又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我国国内现存最早的刻板印刷品《增胜佛母陀罗尼经咒》就是在锦江岸边(今望江楼附近)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的。由唐到宋,四川成为全国重要印刷中心。出版业的发展,又直接促成地方文化的高涨,两宋时期四川文人辈出,著述特多。这一切又与浣花溪水相关联着。
锦江,作为航运干道而起作用,在今天是见不到了,然而在历史上,这确是赫然在目的事实。当初李冰“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这种利用天然水道作传送带把岷山的木材运来成都的办法,后人一直沿用,直到今天仍可以说是较为科学、较为经济的办法。至于由锦江东下,沿岷江入长江以出峡,则是近代化交通工具出现以前成都与中原,江南联系的重要通道。

早期中国历史上许多事件就与这条航道有关。战国时,“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万斛,浮江伐楚”,“走的就是这条道。后来刘邦项羽争天下时:“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同上)靠的也是这条江路。三国以后,西晋灭吴时“王濬楼船下益州”还是走这条道。所以诸葛亮送费祎出使吴国,行至南门锦江大桥畔,费祎指着桥说:“万里之路始于此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万里桥(今成都老南门大桥)得名的由来,也简扼地说明了锦江在成都对外联络上的巨大作用。
唐宋时候,此道行船当然比前代更为频繁,所以杜诗中才说:“窗含西岭千秋雪,光门泊东吴万里船。”又说:“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可见锦江中下人的船只甚多。不仅外商云集,锦江两岸商业区的富商巨贾亦沿此水道外出,到全国各地贸易。刘禹锡《竹枝词九首》之四云:“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词中这个女性乃是成都商人在夔州居留时的“外妇”,商人归成都,久不见来,故托过路暂时停泊的“蜀客”梢信,特别说明他家住万里桥边。
这个小插曲展示了一点唐代商业区富贾们的浪漫生涯,其它情况可以由此推见。同时代的张籍,在《成都曲》中则明白地写道:“锦江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由于商船来往多,以故锦江两岸、万里桥桥头旅馆、酒家应运而生,这诗中的最后十问,表现了观光游人面临选择时的踌躇情态,正好说明了这里可供下榻之处甚多,那灯红酒绿,送往迎来,热闹喧阗的景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上约略提到的,就是浣花溪、锦江与成都历史上物质文明之间的客观而实在的联系。伏尼契写《牛虻》,从凝视海潮获得笔意,达·芬奇从微风吹起湖水的涟漪中得到启示,创作了蒙娜·丽莎谜一般的微笑。杜甫本人非常熟知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草书长进,豪荡感激。
杜诗中写鹰,写马,无不于奋骏神骏中见自己胸襟气度。他平生喜爱激流,正是其豪荡感情的一种寄托。当其面对锦江暴涨势如海潮时,其心潮又怎么能不汹涌澎湃,遐想万端呢?回顾自己一生,以“致君尧舜”之心,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句,纵观海内诗坛,真能“掣鲸碧海”者,能有几人?眼前春水飞花,浮槎入眼,,漫兴之作,谁堪对吟?何处得寻陶、谢辈高手而与之同游述作乎!
这诗题目明说是因锦江之“水如海势”而触动怀抱,诗中显示之胸襟气概,亦确如春天沃日之海潮,而诗之神韵音节,亦皆使人有惊涛巨浪之感。我们不能不说:锦江的奋迅激流有时候竟是叩开杜甫灵感闸门的冲击波。总之,浣花溪两岸历史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丰富而复杂的。这是成都文化史研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牛虻》
《竹枝词九首》
《望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