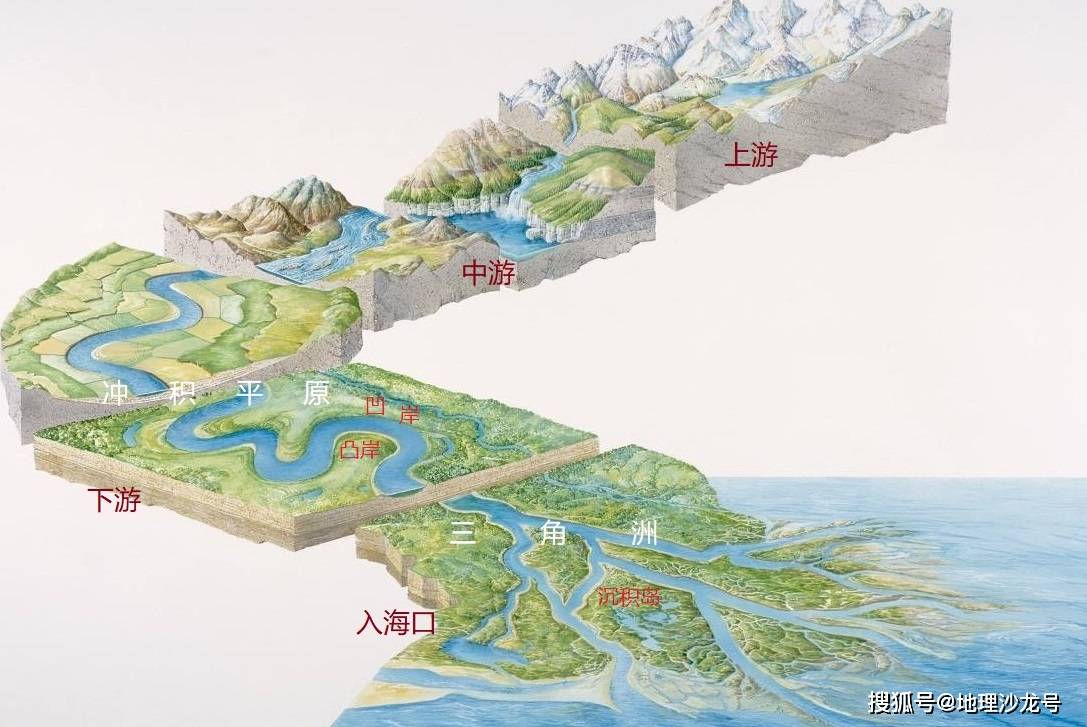□柳 黎
20世纪80年代初期,村里最好的房子就是学校和村委会,有着宽宽的木楼梯供人上下楼,精心雕琢过的窗格子方方正正地镶嵌在木板墙壁上,没有玻璃,就用半透明的薄膜胶布封上,既有挡风的功效,光线也还明亮。这样的景致在今天已经很少见,可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了,普通老百姓想住上有木楼板和宽宽的木板楼梯的房子简直就是奢望,更别说还有胶布挡风的窗格子了。
我的爷爷在世55年,辛苦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修建了3间夯土瓦房。那时候的农村基本买不到建筑材料,修房造屋靠的就是从山里扛一些较好的木料做成檩子、楼枕,条件稍好的就建成串架结构的抗震房,条件不好的就请左邻右舍背土夯墙,辛苦半年,便可建成一栋房子。夯土房倒也冬暖夏凉,最大的弱点就是不抗震。1974年,大关县木杆镇受地震影响,很多夯土房便在强震面前“缴械投降”,塌成一堆烂泥。爷爷刚修好3年的房子也被震得开裂,老人家心疼得直掉眼泪,并因心情抑郁于第二年去世,可见对他的打击有多沉重。
爷爷去世后,我的父亲在奶奶和哥哥、姐姐的支持下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便在老家的小学教书,每月20多元的工资勉强能维持家用。对修房造屋一事暂时是无能为力,便和大伯将爷爷留下的3间夯土房一分为二,各自为家。
几年后,我便出生在那一间半的土房子里,这里成了我真正意义的家。在我记忆中,我家的夯土房子应该是在侧面开了门,两扇狭长的门板对着开,房子为两层,楼下一分为三,外间为厨房兼客厅,简陋到只有几根长条板凳围着一个火塘,里间再一分为二,成了卧室;楼上可堆放粮食和杂物,楼面用竹子铺成,楼梯是把一根稍长的杉木从中破开,再用短而结实的木方子横着支撑起来,既简单又实用。
这样的老屋,简陋至极,却是当时老家许多父老乡亲赖以生存和休憩最温暖的家。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将单调而乏味的日子在一栋又一栋的老屋里演绎得精彩生动,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童年单纯而美好的记忆。五六岁的时候,我便每天端一个小木凳坐在门口,就着斜射进来的光亮歪歪扭扭地学写字,我和文化沾边的岁月,就此起步。
今天,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那样的老屋在老家已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结实、美观的砖混平房。许多务工归来的年轻人手里有了钱,也学着城里人建起了错落有致的小洋楼。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那些破旧的老屋也终将会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