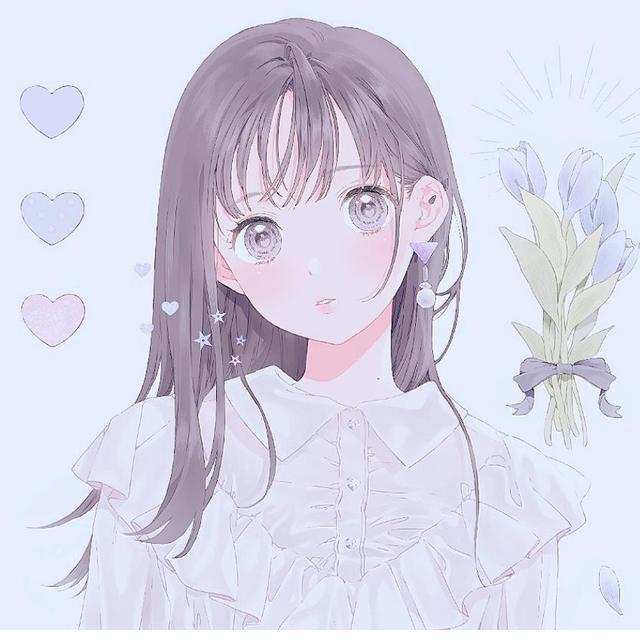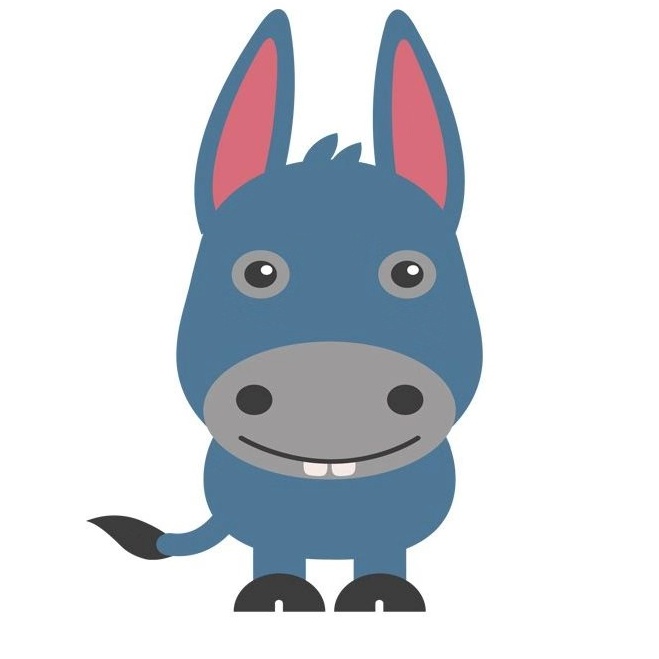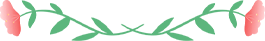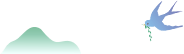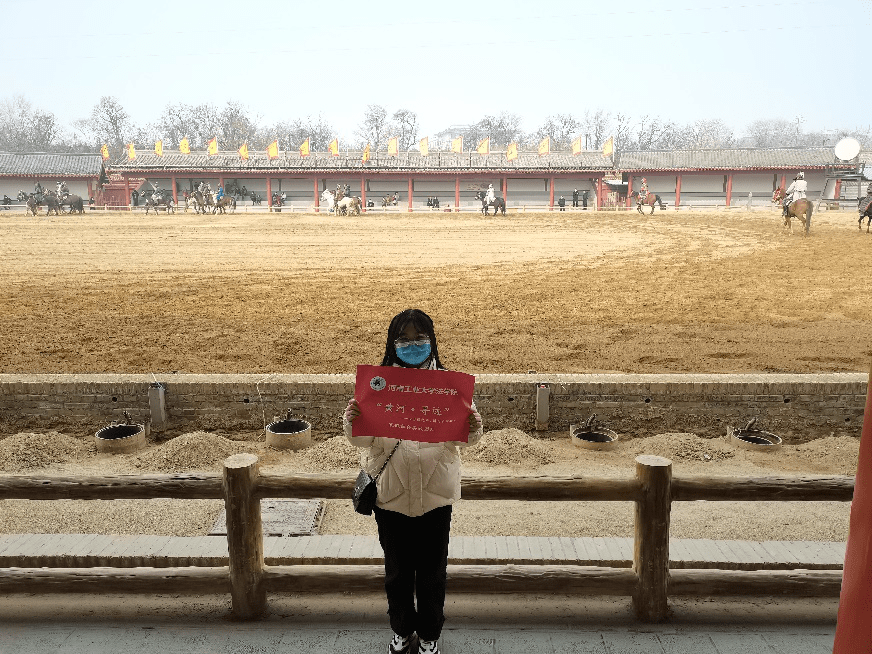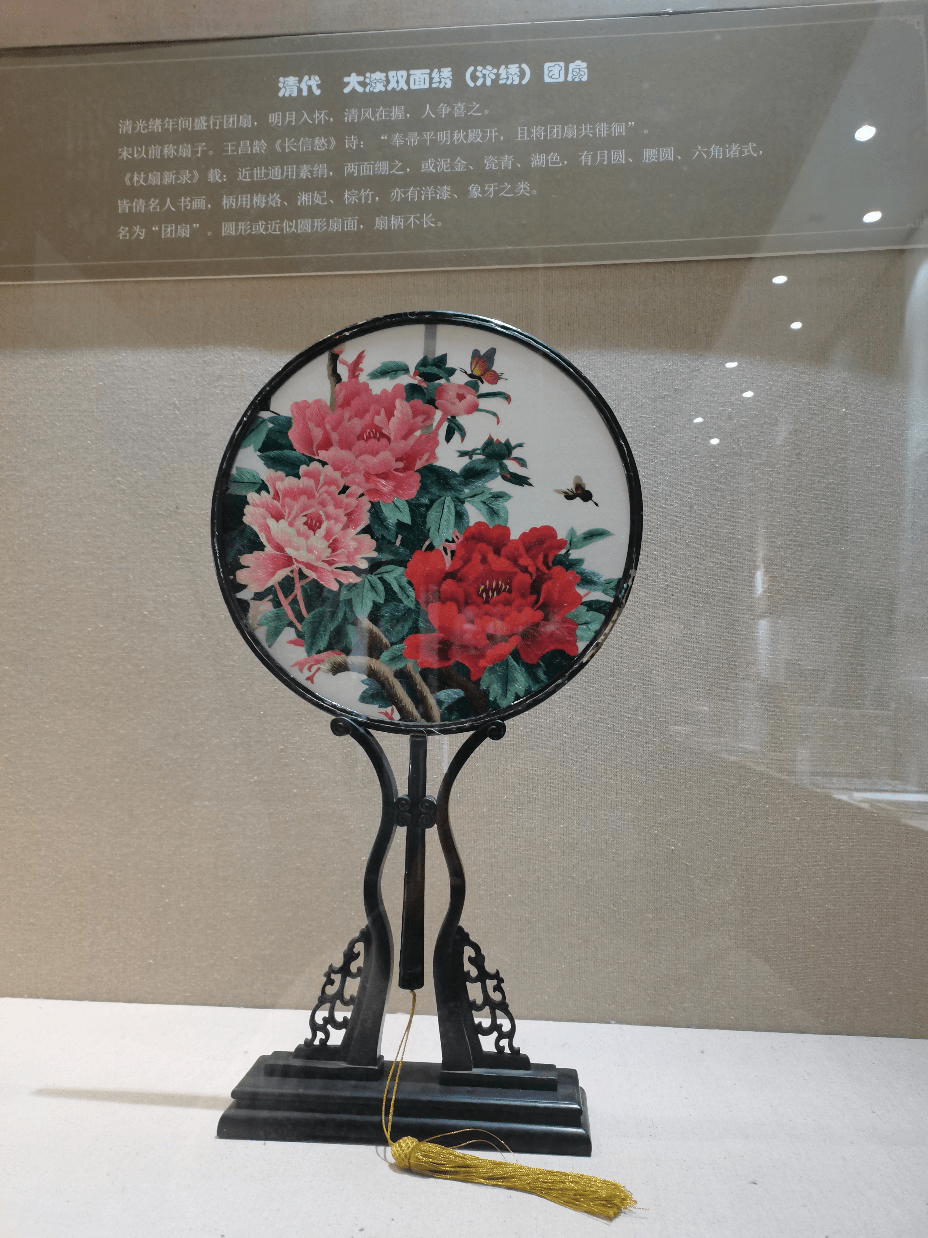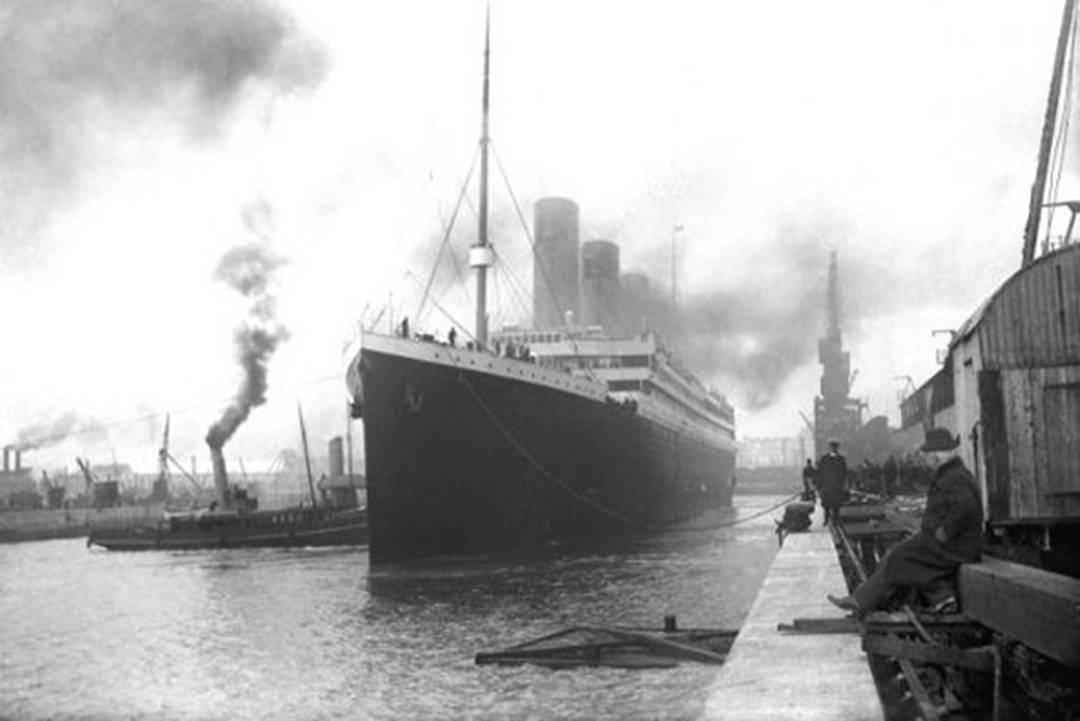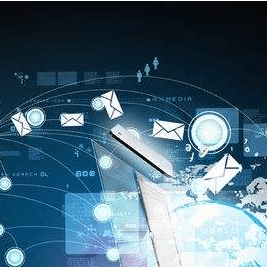故宫的旧墙斑驳了,工人们正忙着粉刷,数年后,新墙会再旧,工人们......历史是一场循环论证,人们不断追问,它仍给出相似的回答。而纪录片正是用一个个相似却意义不同的片刻,拼凑出了历史原貌。
 修缮技艺部学员进行大墙抹灰技艺学习
修缮技艺部学员进行大墙抹灰技艺学习
《我在故宫六百年》是一个关于故宫青春永驻的论据,它在记录历史,传承历史,也在创造历史。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故宫博物院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摄制,梁君健、张越佳担任导演的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已圆满收官。本次好剧邦特别邀请到两位导演,一起与大家分享创作与幕后的故事。
《我在故宫六百年》以“丹宸永固”大展、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古建岁修保养为线索,从故宫工作人员的视角出发,再现了一个与游客眼中截然不同的故宫形象。
梁君健导演回忆起拍摄《我在故宫六百年的》的契机:“这次参加到《我在故宫六百年》,实际上要特别感谢总台的影视剧、纪录片频道的邀请,也特别感谢故宫博物院给的宝贵机会。其实从拍完《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一七、一八年的时候,我们和总台的徐欢老师一直在企划拍摄故宫古建筑修缮题材的纪录片,当时还起了几个名字,比如说我在故宫修故宫、我在故宫修房子等等。一直到今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各方的支持下去完成了《我在故宫六百年》。”
 养心殿修缮工作:脚手架顶棚拆卸
养心殿修缮工作:脚手架顶棚拆卸
就像一代代穿梭在房梁间、考古地里、研究所内不畏艰难的故宫人一样,摄制组克服了内因和外因的干扰,《我在故宫六百年》最终用厚重却不沉重的历史质感打动了观众。
“在拍摄过程中,首要的困难是时间紧,因为受疫情的影响。我们本来希望是六到八个月的继续性拍摄,最终其实只进行了三个月,所以说我们是在一个很紧张的情况下就完成了整个制作。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古建营缮它本身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有一定知识门槛。我们在整个过程中,除了认真地去拍摄记录外,还要去了解一些专业性的知识,这也给我们的拍摄和制作带来了一些困难。”梁君健导演补充到。
纪录片是一门鲜活的艺术,梁君健导演谈到了在拍摄过程中的灵活调整:“《我在故宫六百年》整体的结构诞生在即时拍摄两个月左右后,最前期我们的计划是围绕着故宫丹宸永固大展为三集的整个结构,我们希望从中间找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展品,深度地去记录古建部的老师们,围绕这些展品所展开的研究,寻访和策展的过程。但因为时间因素和疫情的影响,当我们继续实行拍摄的时候,其实大展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已进展过半了。我们当时就不断地去调整,放宽视野。围绕着古建修缮和保护的更多部门。”
“从《故宫》到《如果国宝会说话》,再到《我在故宫六百年》,它们属于不同类型纪录片的表现方式,所以结构上因为类型不同,处理也不太一样。”张越佳导演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虽是非科班出身,但与纪录片结缘已久,在《故宫》、《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六百年》等纪录片中都有他活跃的身影。
 琉璃仙人
琉璃仙人
《故宫》拍摄于2005年,因设备和网络环境带来的革新,让近年的纪录片在拍摄技法和拍摄质感上都趋近成熟。张越佳导演从过往的三部作品中,梳理起这一变化。
“在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我们摄影技法和技术都有提升。《故宫》那会儿还不到2k时代,《如果国宝会说话》里我们更注重细节,有很多微距针孔,包括一些特效的解读来把焦点聚集到文物的细节上。《我在故宫六百年》是更直接地与人交流,拍摄过程中有更多未知,也带来了更多乐趣。”
 养心殿屋顶的椽子
养心殿屋顶的椽子
关于纪录片的拍摄,技术上的提升会给观众带来焕然一新的观感,但最重要的还是理念上的更新,跟上时代步伐,传递更适合新时代的表达,梁君健与张越佳导演一直在为此而努力着。
“《故宫》是一个历史大群像,是历史文化中,关于空间的表述方法,大量采用了再现的手法,结合故宫本体、结合文物、结合现实人的采访,来做的一个宏大叙事感的纪录片。”
“我们在18年拍摄了《如果国宝会说话》,采用了短视频、网感一点的表达。它是一个适合当下传播规律和传播特点的泡面番式纪录片,用 5分钟的内容带领观众了解一件文物。这种方式会更加凝练,不可能面面俱到,不能像《故宫》一样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得很清楚。”
 张越佳导演在工作中
张越佳导演在工作中
“而到了《我在故宫六百年》,我们用一种电影式的记录方式,去抓取在故宫丹宸永固大展中,负责营造修缮、布展的工作人员们。我们采用了直接记录,不摆拍只跟拍的方式。并在后期根据抓取到的不同类型的故事和场景进行分类,最终形成了每一集的主题。”
故宫的古建筑在一代代匠人们的呵护下焕然如新,导演们的技术与观念也在不断地磨砺下历久弥新,就像沉浸在故宫六百年,仍悠然散发出香气的楠木一样,这是时间的风味。
纪录片的本质,是人与人间的沟通。拍纪录片,是去别人生活的地方再生活一遍。《我在故宫六百年》不仅记录了一代故宫守护者们的匠心独运,也保留了他们非常活泼可爱的一面,很多“官方吐槽”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个更鲜活可爱的故宫人。

梁君健导演说拍摄纪录片最重要的是去理解人,去理解人的生活,《我在故宫六百年》是故宫人们的日常,也逐渐变成了导演们生活中的片刻。
“在这次的拍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感谢配合拍摄的故宫工作人员们。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除了自己工作之外,对我们也特别配合且热心,我们的很多专业上的疑问他们都会悉心解答,很替我们着想。比如说古建部的杨红老师,她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特别热情的大姐,她经常有一些想法都会主动跟我们沟通,问我们感不感兴趣,对于片子有没有用。”
“和拍摄对象保持沟通很重要,第一是要有情感投入,不要把拍摄纪录片看作是完成一项简单的工作,开机拍了东西,关机回来剪辑。你一定要把自己放进去,能够真心地去和别人交流,真心地去欣赏,去学习别人生活中的点滴,人心是互通的,你的拍摄对象一定能感受到。”
 故宫彩画
故宫彩画
“第二个方面其实就是时间,愿意花时间呆在那儿,即使不去拍摄,也愿意多去逛一逛,多去看一看。它能让拍摄对象更好地适应你和你的器材,也能够让一个创作者更好地沉浸在创作气氛里,它会给你带来熟悉感和安全感,让你在创作的时候感觉到有支撑、有信心。”
纪录片是声、画、叙事集合的一门艺术,《我在故宫六百年》展示了故宫人的风采,也展示了一个“看不见”的故宫。张越佳导演继续分享道:“游客们参观故宫时,看到的更多是宏伟庄严,故宫更高大上的一面。我们通过这次展览多角度呈现了故宫的很多侧面。比如故宫表面后,那些木建筑的构架与肌理。所以摄制组也在尽可能地去挖掘一个看不见的故宫,让这些细节从看不见变成看得见。”
 养心殿修缮工程:屋顶修缮
养心殿修缮工程:屋顶修缮
“在制作上,我们拍摄了很多干活工作的场景和每个人的工作状态,我们想塑造一个忙碌且充实的匠人形象。在后期的剪辑上,我们也尽量抓住古代与今天、古人和今人、新材和旧物之间的对比关系。比方一个古老的墙壁正在被今日的匠人们粉刷,这样时间的张力就能呈现出来。”
在配乐上,《我在故宫六百年》轻松又不失古韵的音乐得到了许多观众的认可。“我们团队也设计了多种音乐的表达和风格。该厚重的时候厚重,该轻松的时候轻松,该反差的时候反差。所以《我在故宫六百年》是一部集合了各个部门智慧和汗水的诚意之作。”
 木工房指导工具制作
木工房指导工具制作
除了声音与画面,《我在故宫六百年》的旁白文字磅礴大气,徐徐道来间让观众似乎亲临故宫。对于晦涩的古建筑术语,纪录片也做出了更年轻的尝试:“我们一直在尝试通过浅显的语言来与观众沟通。一些难懂的专业术语,我们会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来替换。比如说墙体的维修工程,我们管它叫做美颜。比如说彩画的修复技术,我们管它叫做治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观众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了解到文物的知识。”
不平凡的事都出自平凡人之手,《我在故宫六百年》记录了老中青古建保护者们的守护,展现了个体愿意奉献自己,甘为故宫的一砖一石一瓦一木的平凡与伟大。梁君健导演谈到了拍摄过程中让他难忘的一幕幕。
 导演梁君健在工作
导演梁君健在工作
“有一场戏我们拍摄了乔建军老师,他终于获得了一个机会去奉先殿探寻彩画,而这个彩画是他之前没有机会看到的,他终于亲手把它拓下来了。拓下来之后,他的表情激动得像个孩子,满眼放光。我觉得这样一种对于传统技艺、传统建筑的热爱,特别让人动容。他终于有机会通过物质性的留存,去触摸,想象到前人的记忆。”
对于古建筑的热爱让人们相聚在故宫,他们守望在历史的长河中。“另外就是在第三集结尾时,在修缮技艺部的大院里又开了新的发掘工程,而且这个发掘工程越挖,大家越觉得意外,挖到了明代早期的一些建筑遗存。从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存来看的话,能够看到故宫六百年的历史,甚至是比六百年更长的时间。我们对于历史的问题常常会在意外中得到解答,而且解答的时候可能会提出新的问题。”
《我在故宫六百年》中的“我”,梁君健导演给出了三层解答,三个“我”互为表里,正逐渐融入故宫,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第一个层次‘我’指的是古建筑,指的是故宫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它们在风雨里寂默地守望着。第二个‘我’,我们还希望用它来指代在这六百年的时光里,一代一代地营建和修缮,还有研究这些古建筑的传统匠人和现代学者们,是他们的力量让这组‘老房子’能够留到今天。第三个,我们还希望用‘我’来指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匠作技艺和匠人精神,这些物质实体和一代一代的匠人构成了我们的历史,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承乾宫天花修复工作
承乾宫天花修复工作
近年来,纪录片在年轻一代群体里掀起了一阵小热潮,青年朋友们愿意关注国粹国宝,《我在故宫六百年》也登上了在哔哩哔哩这样年轻的舞台。
梁君健导演表示很欣喜:“我们也特别希望年轻的观众能够喜欢这样的纪录片。因为我想不管是故宫还是其他题材的文博、文化类的纪录片,甚至包括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代表着地方文化、家庭文化的纪录片,它其实展示的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我们这片国土上,古往今来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这些东西会凝聚在一砖一瓦里,也会凝聚在一汤一食的美味中。”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纪录片,把这些物质性、以及物质性背后的精神层面的生活传递给大家,让年轻人看到一个多元、丰盈、令人动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
 故宫脊兽
故宫脊兽
采访临近末尾时,张越佳导演分享了他心中对匠心的定义:“我觉得‘匠心’没有被大家说的那么高大上吧。我拍过很多工匠和大师,他们都是一种很低调的状态,就是享受且静静地做好自己手上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不浮躁,不断地去耕耘,去重复,就能做到越来越好。”
 木匠申福只制作“丹宸永固”大展展品
木匠申福只制作“丹宸永固”大展展品
我们爱古建筑,或许和人们爱追逐某种永恒一样,它们寂寞地沉浸在风雨里,替前人诉说,为当下发声,成为未来的寓言,那是一种可以延续的永恒,也正是一代代匠人呕心沥血地呵护着、传递着的不灭火苗,所以薪火不息,所以丹宸永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