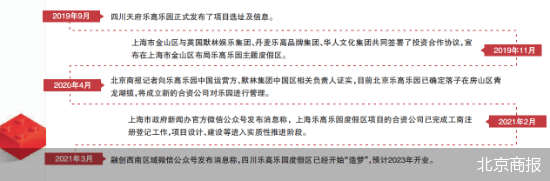长久以来,我对奥什的全部印象,来自于一部叫作《苏莱曼山》的吉尔吉斯电影。主人公是一位45岁的卡车司机,他与妻子和情人一起生活在卡车上。妻子是萨满巫师,忍受着丈夫的自私与暴力。为了挽救感情,她宣称自己找到了他们失散多年的“儿子”。卡车司机夹在两个女人之间,同时还要面对“儿子”。后来,妻子不慎坠山,他也赶走了情人,只剩下那个并无血亲的“儿子”,成为情感的羁绊。
苏莱曼山以穆斯林先知的名字命名。从那时起,这个地方就具有了神圣的意味。对中亚的穆斯林来说,苏莱曼山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圣地。人们甚至相信先知穆罕默德在这里祈祷过。苏莱曼的五座山峰上分布着八座神圣的洞穴。不同时代的圣徒曾在这些洞穴中苦修。路边的灌木丛上有朝圣者系的布条,那是祈求好运用的,同样是伊斯兰教的传统。

(圣山上的博物馆)
苏莱曼山并不算高,周围也没有其他山脉,只是平地上突兀地隆起五个山包。我花了微不足道的门票进去,沿着发卡一般别在山体上的石阶往上爬。朝圣的人群早已将石阶踩得十分光滑。我在路上不时遇到穿着长袍的乌兹别克大妈,朝圣之路让她们呼哧带喘。
山顶只有篮球场大小,但可以俯瞰整个奥什。我发现,这座城市缺乏高大的建筑,到处是平铺的小巷。山势较为平缓一侧的山坡上,遍布着数量惊人的墓地,显然人人都想把自己的骨头安放在圣山附近。墓地一直绵延到山脚下,那里坐落着银色的苏莱曼清真寺,如同海市蜃楼。天际线的尽头处,是帕米尔高原的雪山,令人生畏又充满诱惑,那是我最终想要抵达的地方。

(山顶的朝圣者)
朝圣者们汗流浃背地爬上山顶,是为了进入一个小小的洞穴。1496年,少年巴布尔在这个洞穴中闭关沉思。巴布尔出生在安集延,是帖木尔的后裔。被乌兹别克人赶出费尔干纳山谷后,他在中亚和阿富汗四处征战,后来游荡到印度次大陆,建立起统治印度数世纪的莫卧儿王朝。
可是即便征服了印度,巴布尔依然怀念奥什。在《巴布尔回忆录》里,他写到奥什的渠水奔腾,到处盛开着郁金香和玫瑰。苏莱曼山下有一座清真寺,外面的草地阴凉喜人。常有当地的无赖打开渠口,把毫无戒心的纳凉人冲个落汤鸡。巴布尔写道:“在费尔干纳地区,就气候和景致而言,没有其他城镇能与奥什比美。”

(巴布尔洞穴和朝圣者)
巴布尔的洞穴门口铺着地毯,散落着几双鞋子。我脱了鞋走进去,看到一位中年毛拉正带着五个少女做祈祷。少女中有三个是吉尔吉斯人,两个是乌兹别克人。我坐到她们对面,打量着洞穴内部。洞穴已经不是巴布尔时代的样子。它更新,更规整,铺着砖石,像一个建在洞穴内的小型清真寺,毛拉的祈祷声回荡在狭小的空间里。少女们看着我,面带狐疑之色。我感到了自己的僭越,于是起身退了出去。
巴布尔洞穴后面,有一条通往山下的小路。几个年轻的当地女子正排队从一个光滑的石头斜坡上溜下去。两个穿着长袍的乌兹别克大妈带着旁观者的热情站在边上。看到我驻足不前,一个大妈过来和我攀谈起来。她用手比划着“大肚子”,又指指这些年轻女子。最后我终于搞懂,这些年轻女人都是在等待生育的新妇。按照当地习俗,如果一个女人在斜坡上溜下去七次,她就会生下强壮的孩子。乌兹别克大妈笑起来,露出亮闪闪的金牙。年轻时,她大概也这样溜下去过。
下山的路上,我又路过数个小洞穴或者裂缝。我看到朝圣者们把肘部、手臂甚至脑袋,放进早已磨平的凹槽里。据说,这些裂缝各具神力,可以治疗身体不同部位的疾病。所有这一切,共同构筑了苏莱曼山的神圣。
山下的阿克布拉河西岸,有一排传统茶馆,在闲适的氛围中供应茶水、拉面和抓饭。我点了抓饭,因为费尔干纳的抓饭远近闻名。在乌兹别克的浩罕时,我就吃了抓饭,至今记忆犹新。奥什的抓饭同样没有令我失望。米饭上撒着羊肉碎和鹰嘴豆,配以新鲜的番茄洋葱沙拉,非常可口。
我正吃着,一个栗色头发的胖姑娘也走了进来。她看到我,点了下头。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盘抓饭坐了过来。她是比利时人,在奥什已经住了半个月。这是她第三次来吉尔吉斯旅行。出于某种缘由,她对这个国家有着莫名的好感。她没去过中亚其他国家,每次都在吉尔吉斯呆上几个月。
“这里的人特别善良。”她环顾着四周。
我也环顾四周——巴扎就在不远处——制作马蹄铁的敲打声“叮叮当当”地回荡着。

(黄昏中的苏莱曼圣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