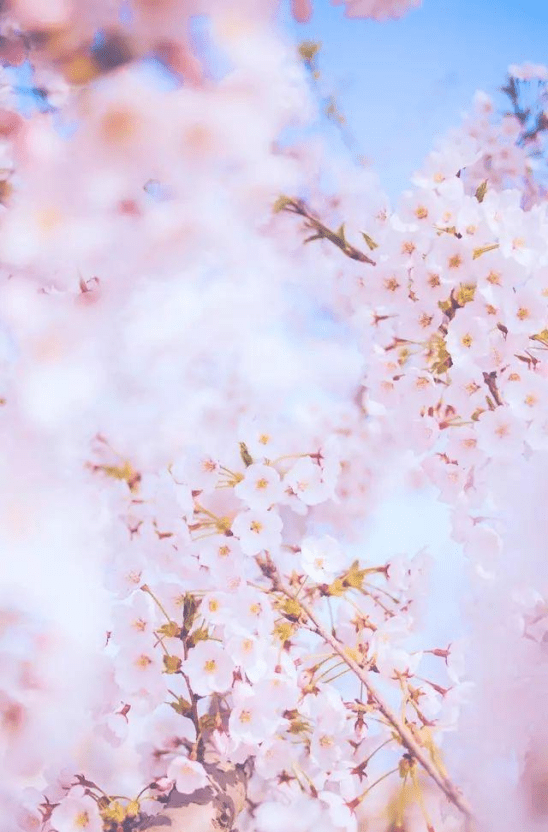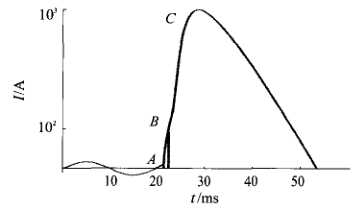□王厚基
堤上,冬日的风散漫地拂来,温润如春,却带些微咸。江流一路往南,便是连接南海的珠江出海口。
这里是磨刀门水道东岸,江岸迤逦,一湾接一湾,水阔浪平,绵延数十里。三百年前茫茫大海滩涂,三百年后沙田绿洲鱼米乡,江河日月,默默见证着这片名曰坦洲的土地海河成陆成田的沧桑巨变。
脚下的江岸是最早的坦洲水居人逐梦的黄金水道。咸淡水交汇,天赐的富饶诱惑人们从南粤各地纷至沓来,他们用最简陋的舟楫最传统的方式捕捞出最肥美地道的海鱼虾蟹,与投奔附近沙丘山地割芒狩猎的中原移民为邻,将世代的命运交付这方水土……如今,坦洲山下斑驳古旧的基围石墩犹在,让人遥想当年耕海渔人祖辈的辛勤围垦。
曾几何时,水居人被称作疍民。随波逐流的生命如同蛋壳般脆弱,满载鱼虾的疍家艇也载满悲酸。南海肆虐的飓风暴雨,西江无情的海潮洪峰,葬送多少以渔为生的磨刀门疍民,卷走多少金斗湾的茅寮棚舍围口村落。浮生江海水流柴,弯弯渔艇是枯枝。出海三分命,上岸低头行,疍家人纵然逃过海上劫难,也躲不开陆上的欺凌。《辞源》上载:疍民“旧律不容陆居”,“视为贱族”,被“禁止船只泊岸,遇喜庆事不许穿鞋袜长衫,有病不许延医诊治,死亡不许棺柩上岸,娶妻不得张灯结彩……”妈祖水神也未能为之庇佑,他们只能向天长啸化解胸中的哀怨,对海长歌呼唤生活的期盼和美好的爱情,让饱蘸海水苦涩的劳动号子化作歌谣去慰藉孤独的灵魂。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载:“疍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可见来自咸水的歌明末清初就在广东沿海一带流行。数百年来,金斗湾的疍民就在“江行水宿寄此生”的生涯中摇橹唱歌,他们在打鱼撒网时唱,在困苦难过时唱,在喜庆欢聚时唱,在恋爱织网时唱。用海涛沙石般粗粝的歌声,唱出鱼虾满仓,唱出满天星斗,把生命的喜怒哀乐都唱个透。
也许,在诗人们眼里,疍民们“煮蟹当粮”“踏浪花”,一派“唱晚渔歌醉落霞”美景。但在疍家人心内,自己却是悲苦的“水流柴”,自嘲风浪中讨食的生命如蛋壳般脆弱。
“沙田疍家水流柴,赤脚唔准行上街,苦水咸潮浮烂艇,茫茫大海葬尸骸……”船在风雨中飘摇,一天劳作无获而归,浊浪拍船联想身世,如泣如诉的歌,叹尽了生命悲凉命运之伤……而当夜幕降临,渔火升起,哥妹双双对唱的情歌,划破黯淡的滩涂,柔情而又绵长“……天上有星千万颗咧,海底有鱼千万条,啊咧阿妹,我有千言万语想同阿妹你倾谈呀咧……可惜牛郎织女,中间都隔着天河嗬啰……”“海底珍珠容易揾,真心阿妹世上难啊哩寻啰嗨……”召唤爱情的歌,依然带有一缕咸苦。
素有“金斗”粮仓之称的金斗湾,近代不知养活过多少“南番顺”人,但这里终究不是净土,战乱、天灾、饥荒、人祸,曾让金斗湾满目疮痍。“……左弯右弯,坦洲近海近山,过去流言,有女唔愿嫁金斗湾,烟赌林立,恶霸横行,年年水咸,食水要上山担,路烂难行,踢爆脚公,磨损脚踭,基地种菜生孽,水田种禾又唔生,台风洪水一来,金斗湾变成白鸽坦……”每当洪潮退却,基头围口一片狼藉,疍民唱出对家乡的满腔愁绪,对生活的无比懑怨,令人唏嘘。
而在时代的风雨下,耐劳的金斗湾疍民没有离开故土,他们深爱这里的一水一土,即便为生活所迫舍舟上岸也不离不弃“……扯起白帆耕大海啰,筑起石堤隔开天……新筑十里金堤,环抱金斗湾,拦住洪峰,断绝水咸……大婶围裙穿珠链啰,大伯烟斗套银边,后生胸前挂玉坠啰,妹仔襟头贴花边啰嗬……”在广袤的滩涂上奋勇围垦造田建起水上村庄,让瓜果稻谷重又香飘“金斗”。歌里洋溢着疍民们劳动的喜悦,流露出用汗水和智慧换取新生活的欢畅。
夕阳下,我在河堤上凭栏远望,落日的余晖给红树林染上一层金红。昔日万艇耕海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小艇穿梭溅起点点浪花,似是讲不完的沙田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