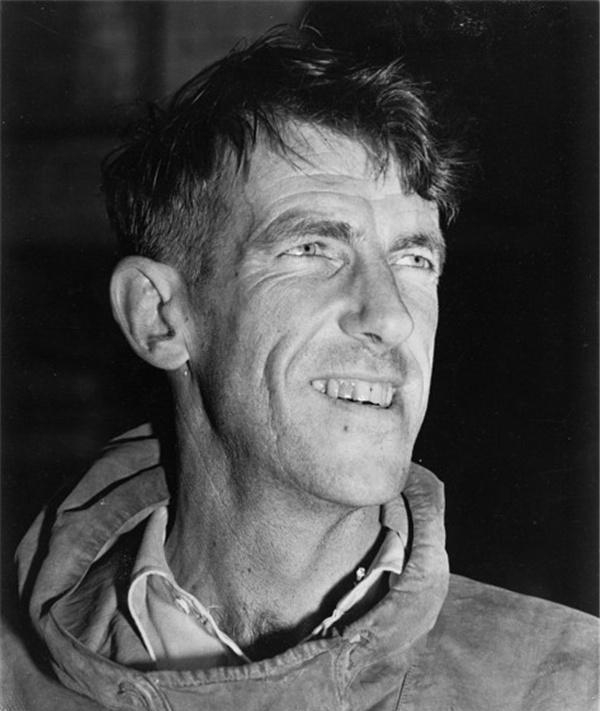在旧金山一次文化人聚会上,和一位新认识的作家聊天,先互通姓名和籍贯,他说他是四川大足人。我说,那是举世闻名的地方,我30年前去过。他问我印象如何。我当然说“好极了”,可是,搔头苦思,对那次一路顺畅的团体游,只模糊记得石窟内的释迦牟尼佛、还有文殊、普贤等菩萨像。但是,两桩小事却在脑海中活灵活现。
一则:离开石窟,和团友们排队登上巴士,车门口,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儿,手拿一个碧绿的网状方块笼,向旅客兜售。我拿起一看,知道是蝈蝈笼子,很喜欢,问多少钱,回说一块钱。我从口袋掏钱,却没有一块钱,打算向太太要,她已上了车。我对孩子说,等等,即上车拿钱去。开大巴的司机吆喝:人齐了没有?我说,稍等。司机有些不耐烦了,对车外的孩子凶巴巴地说:“以后不准来!”孩子做个鬼脸,离开了。我在车门口叫他回来,他转身微笑,高声说:“送给你。”车已开行,我只好落座。拿着笼子端详,是儿时熟悉的玩具啊!那时我也会编,先去菜园篱边,从状似剑麻的“莨古”上割下一两片带尖刺的剑叶,削掉刺,剖成篾片,编成盒子,作蝈蝈的房子。当然,用途不限于此,昆虫如牵牛,还有聒噪的知了,来者不拒。石窟一游,感动我的是:放学后客串小贩的孩子,圆圆的脑袋,清澈的眼睛,把笼子果断地放到我手上时纯真的笑。
二则:当晚,旅游团在石窟附近一个小镇的旅馆过夜。晚饭后一起外出,街上冷冷清清,路灯的光影凄迷。一行人走累了,坐三轮车回去。碰巧用光了人民币,以“两元”面额的美钞付车资。车夫拿着钞票走到路灯下,坐在门外纳凉的街坊们围上来,一边传看钞票,一边低声议论。次日打听到缘由——当地人从来没见过“二元”美钞,怕收到伪钞,集体研究一番。
这些小事,别说和进行中的游山玩水没有联系,对以后的生活也没产生影响。可是,张爱玲说:“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如今想来,我那久远的记忆舍本逐末,根由恰在趣味。偏离主线,逸出常规,无意而得的经验,一个不小心就产生戏剧性效果。河的回澜、树的旁枝、文的闲笔、报屁股的补白,多是这般鲜活、本真、自然。“不相干”并非来自刻意——先有剧本的不算,预作酝酿的不算——务必攻其无备,谁也料不到。“艳”是惊出来的。
原来,这里藏着一种人性的“密码”——表层是对“旧”的厌腻,对“新”的喜好;骨子里是对“独立”的关注,对“秩序”的逆反。“我真希望我们能成为更好的陌生人”,莎士比亚这一名言透露的就是尽可能地与他人“不相干”的渴望。无依赖,无因果关系,无明显的互动,但不能说绝无关联,此刻我的家就是这样。我在书房里读书,妻子在厨房里炒菜。女儿在地板上做瑜伽。女婿在餐厅打开手提电脑办公。大的外孙女一会儿打空翻,一会儿用剪刀裁开向我“买”的白纸(她拿得太多,我说一块钱一张,她打开钱包付款,我暂时扣下),画上数字和图案,制作一副扑克牌。小的外孙女用订书机把从我手里拿走的白纸(不愿意付一块钱)订成一个信封,再向我要一张白纸(还是不愿意付钱),趴在地毯上,给姐姐写信。谁也没有下命令,谁也没有刻意配合谁,呼应谁。这些“不相干”拼合起来,就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