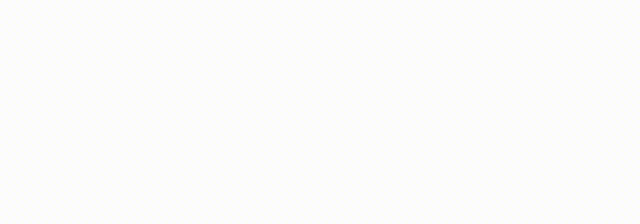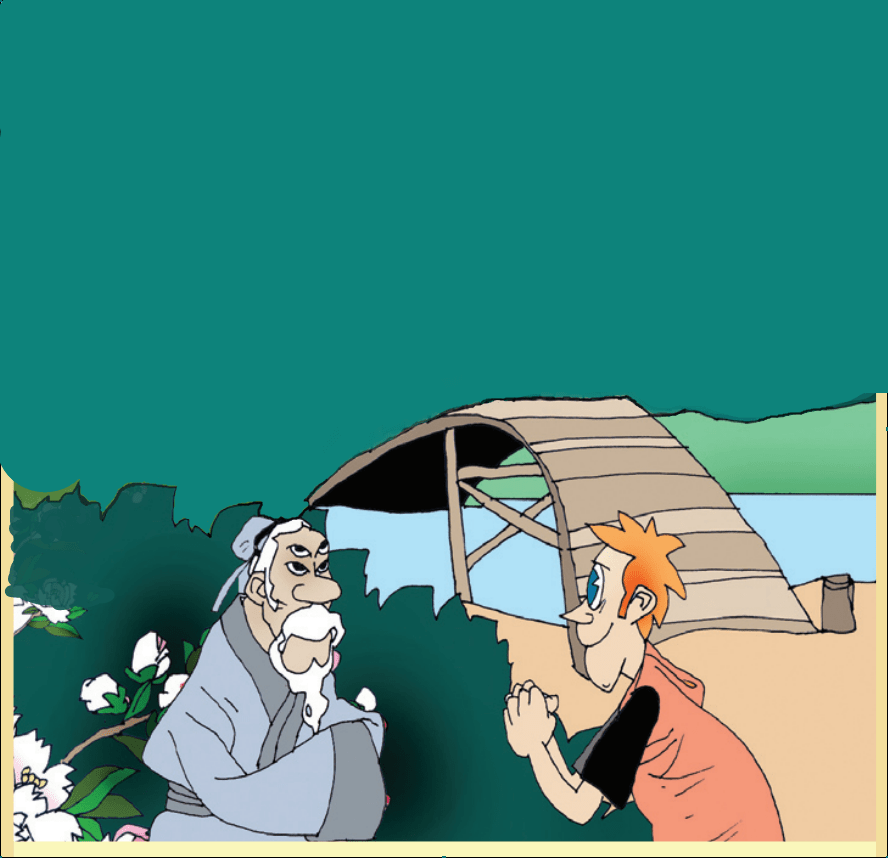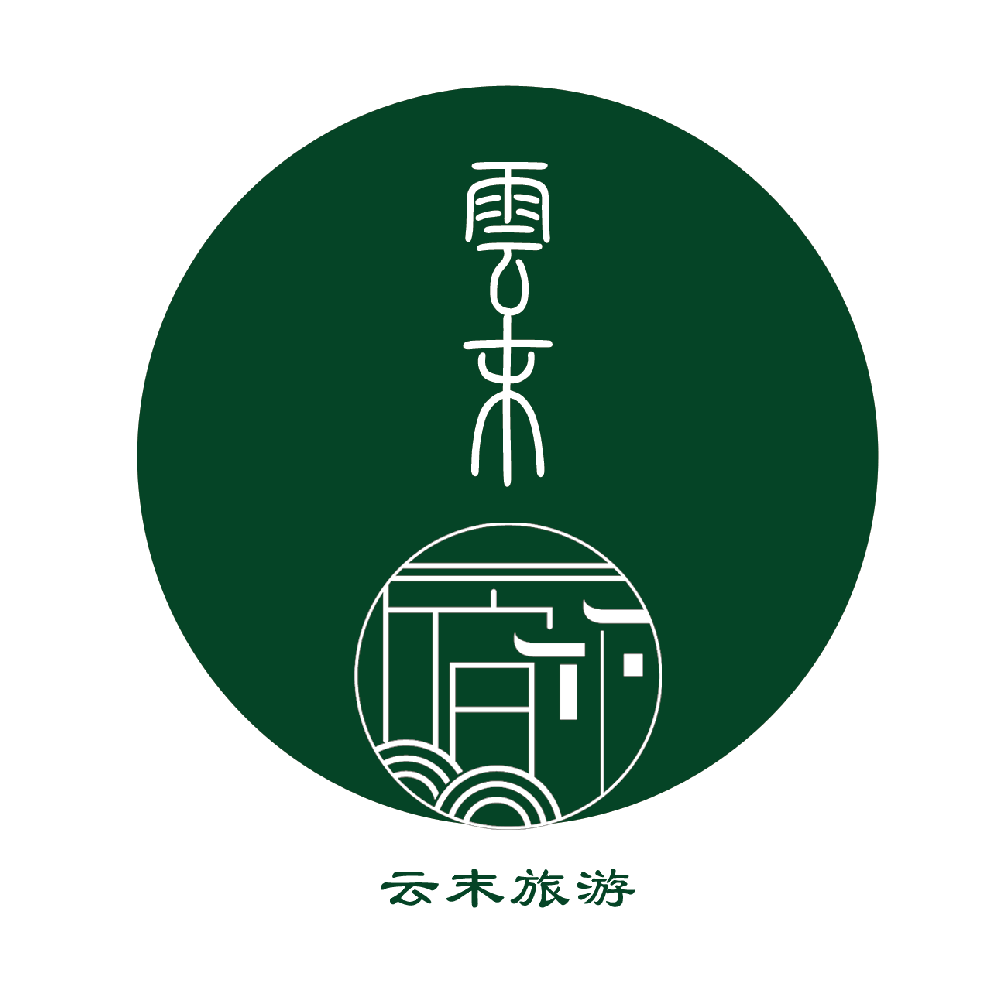本文约2000字,阅读时间2分钟。
山西的面粉
程永新
八月中旬的上海,正是夏天酷暑时节最为难熬的几天,登机去山西,心里面充盈着满满的胜利大逃亡的凉爽。飞机降落太原武宿机场已近傍晚,天空乌蒙蒙的,没有一丝风,但周遭的温度足以慰籍刚从蒸笼里滚出来的躯体和灵魂。接机的小陈是熟人朋友,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直扑平遥古城。平遥有一群我的作家师友,因为被琐事缠身,我成了一个掉队者,于今要赶上远征的大部队。望着车窗外快速后撤的绿色农田,心绪焦急,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
小陈不停用手机与前方大部队联络,知道师友们已用过晚餐,准备去观摩《又见平遥》的演出。一听观摩演出我立刻来劲了,曾记得在呼伦贝尔观看反映鄂温克族生活的歌舞,看得我是热泪盈眶,一簇箭,一群麋鹿,一堆篝火,带有地域文化的民族歌舞,往往能将当地人的日常浓缩于一方舞台上,人事沧桑,物件隐喻,点点滴滴都融汇在优美的旋律中,最大程度地艺术化,最大程度地呈现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到了平遥,落单的大雁与师友们汇聚,握手拥抱,彷如游子归来。匆匆吞咽几口干粮,随着人流进入剧场。《又见平遥》是王朝歌的情景剧,形式独特,演员与观众面对面交流,有布莱希特戏剧的间离效果。之前在各处看过几出露天的山水印象歌舞,美是美,可惜比较同质化。而《又见平遥》有人物,有故事,将历史上晋商和镖局的传说完美呈现。观众随演员挪动,一场一景,一暗一明,历史的空间向前延伸,文化的血脉上下游走。最后来到一个庞大的剧场,银灰色的幕,银灰色的光,接近高潮时的一个场景令人震撼:一张张桌子上摆放着雪白面粉,十几个演员分别匍匐在桌上,深跪着俯首其间,双手捧着白色的面粉,突然间腾身而起,齐刷刷地将面粉抛向天空,面粉变成了雨幕,变成了意念,从空中向大地洒落,人影晃动雨幕,物象解读过往,天地仿佛从历史的幽深处凸显。来之前刚读过山西作家蒋韵的非虚构《北方厨房》,作品切入点很小,从北方的饮食写起,带出姥姥、父辈、我的同代人及晚辈和子孙,饮食史的背后是大历史,洋洋洒洒,从容道来,一派大家风范。边读边想起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是写大历史下的芸芸众生,而蒋韵的方法相反,写厨房写饮食写日常,历史和文化潜流在时间之下缓缓涌动。

翌日去晋中的张壁古堡考察,夜宿崇宁堡。傍晚时天空下起了雨,晋中的雨连绵悠长,润物无声,不经意透出阵阵凉意。打着雨伞去餐厅,遗留的和新修的古堡建筑在雨幕中移动,仿佛在歌吟某个遥远时光。晚餐时上了很多面食,莜面栲栳栳搭配臊子,平遥碗托是用荞面做,还有猫耳朵和饸络面等各种面食,我这个彻头彻尾的南方人,头一回见到麦子后代的各种变化,有的根本叫不出名字,只能假装谦虚地聆听天津来的龙一津津乐道的科普。龙一不愧为美食家,说起食物来眉开眼笑,两眼铮亮,矍铄的眼神透过圆圆的镜框流光溢彩。一个饕餮之徒一定是热爱生活的楷模。众多面食中我独独钟情黄黄的像金元宝般的葱油饼,那面粉元宝有股来自田野的浓香,没来由地有种甘甜,久久残留舌尖。我也曾行走北方多地,面食也领略不少,比如山东的,比如陕西的,唯独今夜山西的面粉借着音乐和演绎,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悟。民以食为天,同样的麦子,通过人类的创造,变成个个不同的美食,这是历史,这是文化,这是民族源远流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酒足饭饱后散席,盘中尚留几块金元宝,我忍不住叫来服务员,悄悄将其打包。之所以“悄悄地”,是甚怕被同样来自大城市的龙一小瞧了。

晋中的雨,淅淅沥沥,大珠小珠,绵长深情。师友们被困屋内,无法外出逛游。电话里传来林那北老师玉女般的呼唤,团长的客厅居然有一张麻将桌。于是,北老师、葛水平、龙一和我相聚团长的客厅,玩开了麻将。团长南帆亲自为我们沏茶,武夷岩茶自是醒酒的极品。规则由龙一定,娱乐至上,无怨无悔。龙一不仅是美食家,还是一个大玩家,恍忽间觉得搁一百年前,他一定是镖局掌门人,驰名江湖妻妾成群。几个小时过后,龙一是大赢家,他把牌一推,潇洒地说:就这样,玩过了不用结账!那神情俨然像免你们一死的衙门县令。
回到房间,静听缠绵的雨声,竟然听出古琴的幽幽呢喃。目光扫视,桌上的金元宝在灯光里熠熠闪光,一点都不饿,可还是抵挡不了那股来自田野麦子的香气,忍不住咀嚼了一块。第二天出发去王家大院,整理行李之际,想都没想,毅然决然把金元宝塞进了旅行袋。自那以后,金元宝伴随我整个晋中之旅,直到离开太原那天,才在机场把最后一块金元宝吃完,想的是要把这浓缩的乡情符号带去远方。
奇怪的是,行色匆匆,过了那么多天,那金元宝还是那么的香,那么的甜,依然有回味遗留在舌尖。以前只觉得老坛汾酒清冽,山西陈醋诱人,于今还要加上面粉与那个令人愁肠百转的戏剧场景。
思念山西的面粉。

文中图片来源:《又见平遥》
原标题:《程永新:山西的面粉 | 食与戏》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