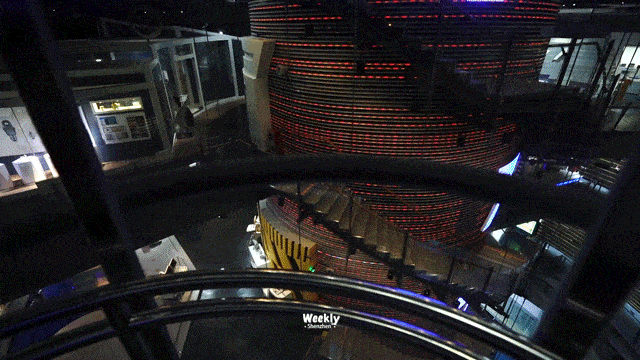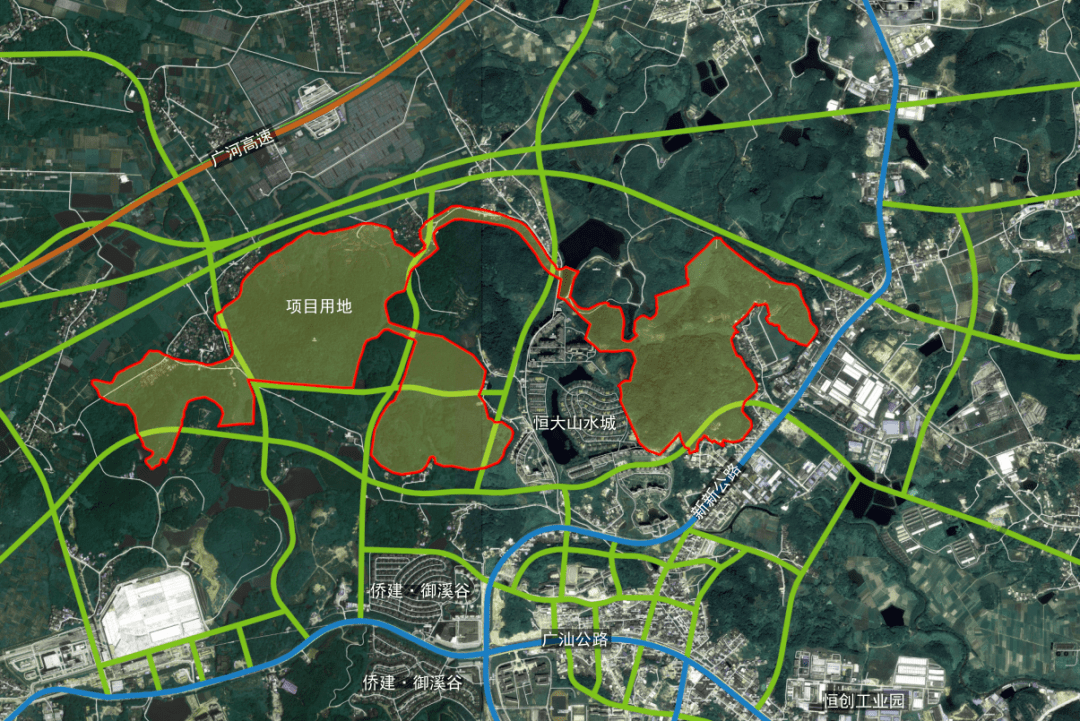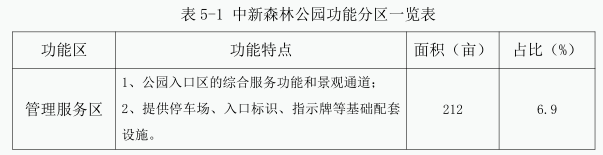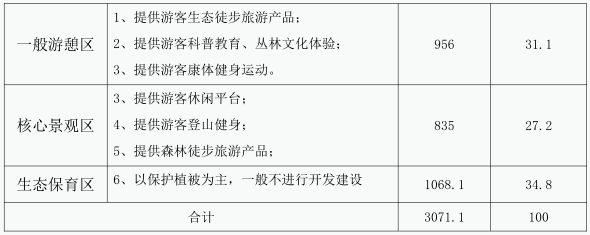河流是绝美之物。
异乡人顺着河道前行。那河道,有时流水潺潺,有时则只是绵延数公里的干燥卵石。
这是摩洛哥东南部的某个峡谷,婉延无尽的山路如饥饿巨蟒,磅礴的崇山峻岭则是被其盘绞的永远吞不下却也永远不肯放手的猎物。
一切都那么深:山峦的阴影、无花果浓密的枝叶,还有那个以手当秤掂量着卖巴旦木的老人的皱纹。
一头身披彩锦的骆驼突然出现在公路,一个身穿厚袍的男人正吃力地蹬着自行车在后面追赶。每当甩出一段距离,骆驼就停下张望,当快被追上,骆驼又赶忙跑开。看到这一幕,异乡人笑了,一辆汽车经过,减慢速度,里面的乘客也笑了。
笑声不大,却仿佛是这世界惟一的声音。
车在拐弯处消失了。骆驼终于停下。当男人经过,那粗重的喘息声成了世界惟一的声音。
他和它重回到巨岩下。地面的几堆香料和无花果干,原封不动。
这就是他一天的工作:等待。等车停下、等有人骑上骆驼照一张相、等那些灰扑扑的土特产被人领走。

可这儿不是游人如织的马拉喀什(Marrakech)。这儿甚至不能算是镇子。河道那边,几个古旧村庄零散地分布在谷地,河的这边,几家客栈和一间香烟按根卖的小卖部临街而立,其中那间写着醒目“WIFI”的客栈,三天里只接待了一个中国客人。
但总会等到的,不是吗?等到旺季,等到那些自驾而来、仿佛流动的欧元般的德国人或法国人,甚至,哪怕只等到一个省吃俭用的背包客,也不算虚度——在这荒疏大地,任何一张新鲜面孔都如同一份馈赠。
何况,这世上,谁又不是在等待中度过一生呢?等成长、等一份体面的工作、等一间温暖的房子、等着去爱和被爱……因着希望,人们心甘情愿,因着希望,人们望穿秋水,哪怕,“希望”不过是上帝用以安慰孤独人类的虚拟奖章。
一些黑点在山岗缓缓移动。

它们在那里很久了,由于遥远和缓慢,异乡人过了很久才察觉那些是山羊而非石子。一个骑着毛驴的年轻人出现:头缠白巾,满脸青春痘。
“bonjour”,异乡人说。
“bonjour”,年轻人说。驴子慢了下来。
这是法语的“你好”。在这个国度,英语不管用。管用的是法语和阿拉伯语。不过,村里的一些孩子会在“bonjour”之后,随即用也许是他们惟一知道的英语说“1欧元”、“铅笔”或“巧克力”。孩子有时等几分钟后离开,有时会远远跟上好一段路,偶尔,也会有孩子捡起石子充满敌意地投掷。
“bonjour”,异乡人又说。
“bonjour”,年轻人又说。驴子停下了。他眼睑低垂,满脸通红,完全不敢正视对方。
“祝你平安”,片刻沉默,异乡人微笑着用英语再说。她会的法语不超出五句。他没吭声,应该是没听懂。毛驴开始缓慢前行。她回了一下头,却发现他正在回头看她,然后,非常突然的,他从驴子背上跳下,目视地面,双手下垂——他以为她想拍照。
异乡人摆摆手,努力想让对方明白自己只是问个好。他羞得眼睛都快合上了。片刻之后,他抬头飞快瞥一眼,然后快速翻身上驴。这回驴子走得快了些。她回了两次头——每次都碰上他正在看她,随即又立即垂下眼帘,扭过头去。
一些孩子的笑声远远传来。

那个村庄,在半山腰,清一色的土黄,清一色的泥巴房。钢筋水泥是不存在的,在这古老山坳,泥浆混合某种干草杆茎,晒成泥砖,亲戚邻里相互帮助,一个个简单的“家”就出现了。

那是一个小卖部,昏暗、窄小,灰扑扑的货架上摆着些鸡蛋和便宜糖饼。异乡人要了一瓶水——瓶身留下她清晰的指痕。是啊,这样的地方,除了偶尔误撞而入的旅人,谁会买水喝呢?就算在非斯(Fes)那样的大城市,普通百姓也不会买矿泉水。许多街巷都有公共饮水处:龙头会有一根绳子拴着个塑料杯。人们渴了,就拿起杯子冲一下,接上一杯。也有老人推着大陶罐——里面盛着清凉山泉。人们要么直接瓢饮,要么拿用过的空瓶装,价格合约人民币五角。
几个孩子和妇女坐在小卖部面前,目光谨慎,但没有立即避离——对方不是男性。
“salamalaykom”,异乡人说。
“alaykomsalam”,人们回答。
这回是阿拉伯语。孩子停下来,安静地依在大人身边,黑溜溜的眼睛小草叶尖般不时瞟过来瞟过去。

傍晚的阳光变得可以忍受。人们在温柔的光线里静静坐着,谁也没再开口,谁也没离去。
异乡人掏出杏仁。她展开手心,向人们示意。而其他时候,比如那些用英语说出“1欧元”“圆珠笔”或“巧克力”的孩子,她通常摇摇头果断走过。
一位年轻的母亲试探着拿了一颗,接着,另一个女人也上前拿了一颗,接着,每个人都上前拿了一颗。她们在她身边坐下,安静地吃着,目光渐渐柔和。
又坐了一阵,一位中年妇女从小店走出,她笑声朗朗,毫不客气地从异乡人手中拿走最后的几粒杏仁,然后笑着示意:到家里喝茶。
那间房子,光线昏暗,一根没有灯泡的电线孤零零地悬吊在天花板,两张铺着花毯子的沙发、一张小茶几、一个小木柜。一位面目端庄、穿着得体的柏柏尔老妇人出现。她笑容腼腆,目光明亮。
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可以相互听懂的,但通过手势,异乡人仍是弄明白了:她们想看看她住的地方,看看她那在遥远国度的家人。于是她翻出一些相片。人们惊叹着:那些山林和湖泊,那些街道和商铺,是另一个难以置信的世界。

那个下午,异乡人留下了整个摩洛哥期间惟一被允许甚至是被欢迎的妇女影像。她们捂着脸不住吃吃地笑,相互打趣。她们的眼羞涩清亮如童贞。一位年轻姑娘开始翻箱倒柜——那张小小的身份证,用两层碎花布小心包着。姑娘对着证件一笔一划认真写下了一系列阿拉伯文。那地址,异乡人最终没用。第二天,她坐班车到一小时之外的镇子,将相片晒了出来。
这一次,人们不仅端来茶,还有面包以及珍贵的黄油。
老妇人怀揣相片,不断地看,然后小心放进衣兜,过一会又拿出来再看,再小心放进衣兜。这举动她至少重复了五次。异乡人留意到,老人那天的服饰相当华美,头巾也换过了,精心地围绕在苍老面庞。她甚至坐在同一张椅子,保持同一角度——照相的人曾表示,从窗棂射进的霞光使她看上去非常美丽。
老人不可能知道异乡人还会再来,但她准备着——为一个毫无把握的隐约期待,一个得以被关注的暮年片刻。
暴雨过后的天空云霞满天。

回客栈的路上,一段路被水淹没。急流从山谷奔下,经过路面,冲下山崖。几位柏柏尔妇女在路边等着,虽然水不过及膝。她们不可能提高裙襟。
几个男孩卷起衣袖,扎起裤角,从谷地搬来石头然后扔进水里。几个西方人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不时举起手中相机。
异乡人放下背包,卷起裤角,加入搬石头阵列。孩子们因此而更加热情高潮,搬的石头越来越大。
很快,一座“石桥”便搭好了。人们小心地踩着石头走过。几只山羊到来,不知所措地茫然四顾,然后也依次轻灵跳过。然后是一头驴子、一个背负山柴的妇女、一个抱着手鼓的年轻人、一个拎着袋仙人掌果的老人……
月亮升起来了。
异乡人走在空旷的泥土小路,步伐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