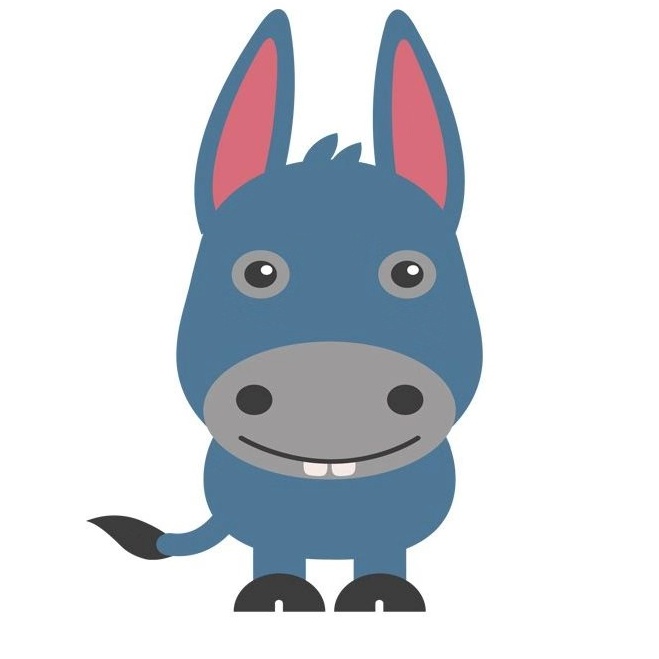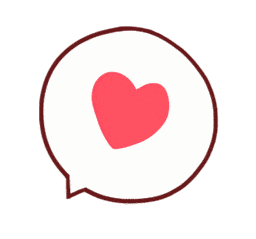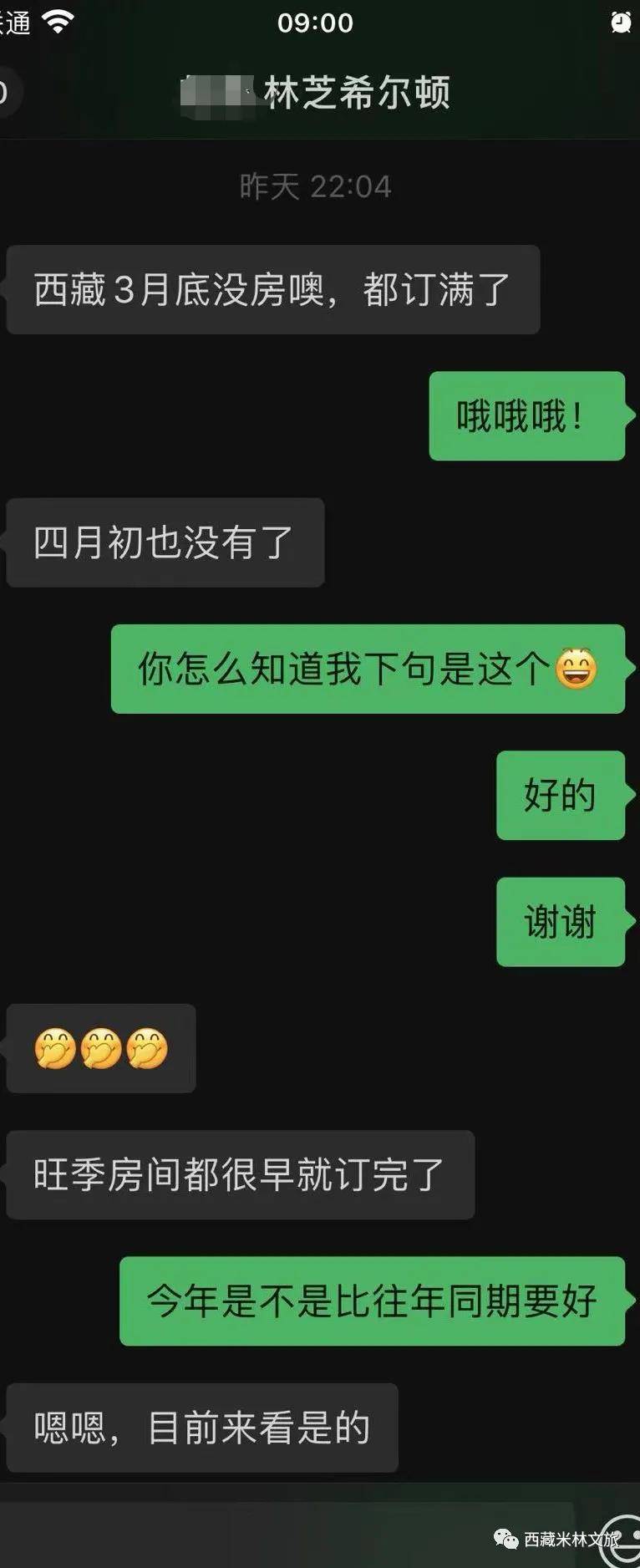常言说的“有故事”,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词。因为“故事”往往意味着是否有趣和有意义。有趣和有意义的事不仅令人长见识,更能启迪人的智慧。所以,古今中外,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莫不喜欢“故事”,喜欢“有故事”的人、事和地方。

康定城
提到康定人们并不陌生,一首广为传唱的《康定情歌》已让这座位于成都平原之西的边城闻名遐迩。康定处于传统的汉、藏分布边缘,也是汉、藏民族的结合部,是一座兼具汉、藏文化特点并有着浓郁特色的边城。康定给人的印象是喧嚣、拥挤但又充满活力。在纵贯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一条清澈、奔腾、喧嚣的河流以极快的流速穿城而过,这在中国的城市中恐怕独一无二,却是康定城最独特的一道风景。但若论康定之魅力,却不在自然,不在于其地为交通咽喉,亦不在于《康定情歌》所唱“康定溜溜的城”,而在于它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先从康定的跑马山说起。《康定情歌》第一句歌词是: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哟。
这句简单、悠远的歌词,激起人们对康定的无限遐想。上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康定,朋友带我去登跑马山,当时还没有索道,山很陡,但树木葱笼,风景极佳,我们沿着陡斜的山涧小路一路上行,狭长形的康定城全貌逐渐清晰地尽收眼底。当终于到达目的地,却发现被称作跑马山的“跑马”地方并非辽阔、空旷之地,更不是飘着“一朵溜溜的云”的一望无垠的草原,而只是一个山间小平坝,完全不适合“跑马”或“赛马”之类。或许为了与“跑马山”名称相符以满足游客的期望值,小平坝上确有商家弄了两匹马在坝子上转圈,这主要成为小朋友或部分游客的娱乐项目。下山路上,朋友告诉我,很多外地游客和朋友到康定,第一件事就是迫不急待地去上跑马山。对跑马山,康定人有一个很诙谐的总结:“不上跑马山会遗憾,上了跑马山也会遗憾”。“不上跑马山会遗憾”比较好理解,因为不上跑马山,就无法兑现我们被《康定情歌》所激发起来的对跑马山的无限遐想。但上了跑马山才发现,这并非人们想象的辽阔、空旷的跑马之地,故也会遗憾。
下山后,我一直困惑于一个并不适合跑马的山为何会被称作“跑马山”?专业习惯使我忍不住去查阅资料,一查才知道,所谓跑马山,当地藏人原称“帕姆山”,“帕姆”(phag mo)意为“仙女”,“帕姆山”乃是藏人的一座神山,因清代管辖康定一带的明正土司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在山腰台地供奉山神,时康定汉人已较多,汉人遂依其音将“帕姆山”称为了“跑马山”,这才有了《康定情歌》唱的“跑马溜溜的山”。
对这则故事,一般多认为是由汉、藏民族之间的“词语误读”引起,是汉人将藏人所称“帕姆山”读作了“跑马山”的一个有趣味的误会。从表面上看,这大体没有错。这也是我最初的认识。但后来,有关这类故事的一系列令人惊奇的发现,却让我改变了看法。我发现,所谓“误读”,其实是一个错误判断。
先从康定的地名说起。康定原来并不叫“康定”,而叫“打箭炉”。今天康定城区仍叫“炉城镇”,系“打箭炉”地名的孑遗。“打箭炉”地名由何而来?今作为康定门户的泸定桥头矗立着一尊高大石碑,这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泸定桥落成时,康熙皇帝亲自为泸定桥落成撰写的一篇“碑记”,全称是《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碑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
这说明,至少在泸定桥落成时已有“打箭炉”这一地名。且碑记中特别提到“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这是对“打箭炉”地名含义的诠释。也就是说,“打箭炉”得名是因为诸葛亮铸军器(即“造箭”)于此,而且此说法出自“蜀人”。这是我们从康熙碑记中得到的信息。

泸定桥

康熙御碑
那么,“打箭炉”真是因诸葛亮“造箭”于此而得名吗?查阅史料才发现,“打箭炉”的地名早在明代已经出现。《明实录》中记载了一件事,洪武十五年(1382年),元朝时曾任四川分省左丞相的剌瓦蒙(应为蒙古人)派一名叫高惟善的使臣前往明朝都城应天,目的是把元朝所授银印上交明朝,以示“弃元投明”,归顺新王朝。记载中提及高惟善一行是“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长河”指大渡河,“长河西”则指大渡河之西。文中提到了“打煎炉”这一地名。这一事件在《明史》中也有记载,称高惟善是从“其地打煎炉”来朝,确证“打煎炉”是一地名。可见,《明实录》《明史》中已出现了“打煎炉”地名。
清初,蒙古和硕特控制康区之时爆发了“三藩之乱”。割据云南的吴三桂势力延伸至滇西北,且与西藏多有来往,引起清廷不安。为此,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发了一道谕令,要求派员加强对“打煎炉”一带的侦察和防御。此谕令中,把“打煎炉”写作“打折卢”。由此可见,在康熙《御制泸定桥碑记》以前,仅写作“打煎炉”和“打折卢”,并无“打箭炉”的写法。
那么,“打煎炉”或“打折卢”是何意?显然,无论是“打煎炉”还是“打折卢”,均不存在汉文字面的含义。可以肯定,二者均源自藏语地名的译音,属汉字记音的地名。对此,民国时期学者已有一致看法——该词“系藏语‘打折多’之译音”。藏语称两水交汇处为“多”(mdo)。打煎炉正好处于源自折多山之折曲(即折多河,曲为“河”)与源自大炮山之大曲(打曲,即今雅拉河)交汇处,故被藏人称作“打折多”(dar rtse mdo)。所以,明代和清代早期文献中出现的“打煎炉”或“打折卢”,正是藏语“打折多”的译音。
打折多在明代兴起主要与两个背景有关。一,从明中叶起,青藏道因受西北蒙古诸部威胁,屡遭劫掠,明朝为“隔绝蒙番”,从明中叶起规定藏区僧俗朝贡使团一律须经由川藏道往返,川藏道必经打箭炉,这使打箭炉的交通咽喉地位开始凸显。二,明末蜀乱及张献忠入蜀,使蜀人大量西迁避险。避险的蜀人大量越过大渡河,进入打箭炉一带。这使汉藏茶叶贸易市场逐步从大渡河东岸向西岸转移,打箭炉作为汉藏新兴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
为何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谕令中尚称“打折卢”,时隔25年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却变成了“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的“打箭炉”呢?原因是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700年当地发生蒙古营官杀害明正土司事件,为维护当地政治秩序,清朝发动“西炉之役”,从蒙古和硕特部手中夺取了对打箭炉的直接控制权。二是康熙四十年(1701年),在大渡河上建成了泸定铁索桥。这两个因素导致大批蜀地汉人涌入打箭炉。正在此背景下,“打折多”开始变成了“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的“打箭炉”,故“打箭炉”的称呼显然出自迁入当地的蜀地汉人的“发明”。
既然“打箭炉”是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得名,该传说在蜀人中就被继续演绎。于是产生了诸葛亮曾派一名叫“郭达”的将军在当地造箭,郭达将军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打箭炉城中建起了“郭达将军庙”等一系列传说故事。为配合这些传说故事,使之更真切,城边的一座山被命名为“郭达山”,城中也就出现了一座“郭达将军庙”。

郭达山

康定城的郭达将军塑像
“郭达”何许人也?遍查《三国志》等史籍,诸葛亮麾下及同时代并无一位叫郭达的将军,可见“郭达”并非真实历史人物,而是出自虚构。既然“打箭炉”是一个望文生意附会而来的地名,何来“郭达”其人?稍做调查才知道,“噶达”(mgar ba)原是当地护法山神的名称,所谓“郭达山”原是当地的“噶达”神山,城中的所谓“郭达将军庙”,当地藏民称“噶达拉康”(mgar ba lha kang),是敬拜“噶达”山神的庙。有意思的是,有关噶达山神的来历,据当地藏人的传说,很久以前,一铁匠在西藏习法,奉命来打箭炉,修成正果,幻化为铁匠化身的神。藏语“噶达”正是“铁匠”之意。于是,噶达山神的“铁匠”身份成为汉人衍生郭达将军“造箭”传说的蓝本,也成为衔接汉藏传说、信仰的一个关键环节。

噶达大王
以上这些,均是打箭炉兴起过程中,因大量汉人移民进入而出现的独特文化现象。毫无疑问,无论是“打箭炉”地名,还是“郭达山”和“郭达将军庙”,均出自于汉人移民的主观建构。那么,这些主观建构有什么作用?对此,开始我不甚了了,亦未予深究,只觉得这些“故事”很有趣。直到2017年我在雅安一个藏茶厂的宣传栏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才恍然有所悟:
“雅安”是藏语,意思是牦牛的尾巴。如果把青藏高原比作一头牦牛,雅安就是这头牦牛的尾巴。由此可见雅安是当时藏区的边沿。三国时,诸葛亮南征与孟获交战,就在雅安。七擒七纵使孟获心服口服,双方商定,孟获退一箭之地。谁料这一箭却从雅安“射”到了200多公里以外的康定。这是诸葛亮谋略过人,早已暗中派人在康定安炉造箭,然后将所造之箭插在一个山顶上,孟获吃了哑巴亏,无奈还雅安于蜀国,退到了康定以西,所以康定会取名为“打箭炉”。
藏茶厂老板祖辈均从事藏茶生产,他是第七代传人。若按30年一代计,大体可上溯至乾隆时期。他称此传说系祖辈所传。因清代藏茶主要经打箭炉销往藏地,此传说当年在打箭炉地方流传甚广。这是一个典型的民间传说版本。“退一箭之地”是发生于诸葛亮征南中的传说,将其移植于打箭炉实属荒谬,但这个移植对我们理解当年进入打箭炉的汉人移民为何会围绕“打箭炉”地名附会诸多传说却十分关键,这些传说实际上在强调和隐喻一个事实——打箭炉并非“异乡”,早在诸葛亮时代就已是汉人的地界。这样做并非是要和藏人争地盘,而是对汉人移民可以起到化“番地”为“故乡”、化“陌生”为“熟悉”的心理作用。打箭炉的汉人移民主要来自蜀地,诸葛亮是蜀地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典型的汉人符号,把自己最熟悉的文化符号带到新的环境,是移民化解、疏导客居异域“思乡之愁”和弱势心理的一剂良方。对“打箭炉”地名的塑造并演绎诸葛亮时在此“造箭”、“让一箭之地”和“郭达将军”等传说,对汉人移民来说正有着这样的功能。

有一个现象极有意思,汉人移民中产生的这些传说,有一个共通点——均是借用藏人的词语来说事儿。无论是把藏语地名“打折多”变为“打箭炉”,把藏人的“噶达”变为汉人将军“郭达”,还是把藏人敬奉的“山神庙”变为汉人的“将军庙”,均无不如此。开始我对此并不理解,以为这纯属汉人移民牵强可笑的“误读”。特别是把当地山神“噶达”变为汉人将军“郭达”,二者虽然同音,却无任何史实依据。我曾经产生这样的疑惑,他们为何一定要“借用”藏人的地名、山神名和庙名来注入自己的诠释和意义?何不“另起炉灶”?但是,当知道这些做法产生的效果后,我渐渐改变了看法,开始明白这些看似牵强可笑的“误读”,实际上并非“误读”,它的背后蕴含着一整套文化逻辑,是汉人移民寻求与藏人整合,借以达成“共享”与“求同”的一种高超的民间智慧。
事实上,汉人移民把藏人的山神“噶达”称作“郭达”将军,进而把“噶达山神庙”作为“郭达将军庙”,均产生了奇特效果,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打箭炉一年一度规模盛大的“将军会”。“将军会”主要内容是抬着“将军神像”巡游全城。会期从每年农历六月十五开始,传说这一天是郭达将军诞辰日。会期持续三日,期间,整个全城都沉浸在欢乐气氛之中,盛况空前。民国时有人曾这样记载“将军会”的盛况:
“将军行身出驾。笙箫鼓乐,旗锣幡伞,扮高桩,演平台,以及各种游戏,装鬼扮神,陆离满目,绕场过市,万人空巷,亦一时之壮观也。”(杨仲华:《西康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59页)
又记:“郭达将军诞辰,俗呼将军会。是日午后一钟,神驾出行,前列各项戏剧平台,杂以鼓乐,次为香花水果茶食宝珠衣等供养,又次为火牌、执事持香,妇女与念经或奏番乐之喇嘛以及画装之剑印二使者,鱼贯而行,终则以四人肩抬将军神像,尾随其后,沿街铺户,秉烛焚香,燃烧柏枝,全城香风馥馥,观者塞途,一时颇称热闹。”(《西康消息》,《西康公报》1931年第20期)
“将军会”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从史料看,至少民国时期“将军会”已成为康定一年一度藏、汉民众“同祀共欢”的盛大宗教活动与节日庆典。该活动虽被冠以汉人色彩的“将军会”,却丝毫不影响藏人的参与热情,其性质既非完全汉式,亦非单纯的藏式,而是汉、藏信仰因素的杂糅。如“抬菩萨之人,皆为藏族青年。参与菩萨出巡行香之人藏族男女老少,要占总人数之半。”[《康定县炉城镇志(初稿)》,康定:康定县志编纂领导小组,1990年,第143页]由汉、藏共祀的“郭达将军庙”(藏人称“噶达拉康”)衍生出来的“将军会”,发挥着整合汉、藏关系的功能和作用。通过一年一度“将军会”的“同祀共欢”,极大消弥了汉藏双方的文化生疏感,使汉藏民族间的文化界线趋于模糊,民族关系趋于亲密、和谐。从清代至民国,打箭炉这座汉藏民族混居的“边城”,一直以民族关系的和谐著称,成为汉藏交融的典范。这不能不说与“将军会”所起到的文化整合作用有极大关系。
需要指出,把“打折多”变成诸葛亮“铸军器于此”的“打箭炉”,把当地护法神“噶达”称作“郭达将军”,或将“噶达”神山说成郭达将军造箭的“郭达山”,这些均不碍事,汉、藏双方均可按自己的认定与理解各行其是,相互可并行不悖。但难度在于,要把藏人祭祀“噶达”山神之“噶达拉康”同时作为汉人敬拜的“郭达将军庙”却相当棘手,同一庙宇,同一尊神像,如何能够成为汉、藏双方共同的祭拜场所?令人钦佩的是,汉人移民在这方面表现了高超的智慧、变通与灵活性。汉人的做法是,既不变更庙宇,也不变更庙中原有神像,而是仅在藏人敬拜的“噶达”神像前置一木牌,上书“敕封某爵汉朝郭达将军神位”。
民国时曾任康定第一完小校长的黄启勋对“郭达将军庙”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幼小时所见庙中住持,常年是一年老喇嘛,加之郭达神像着藏式服装、骑山羊,与喇嘛称之为骑羊护法神的‘当钦’酷似一人,这以汉式庙宇,塑藏式菩萨,汉藏民族共敬一人,恐怕也是打箭炉为藏汉杂居之地,宗教感情融通的地方特点的反映。”(黄启勋:《郭达随笔》,《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康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委员会编印,1989年,第146页)
从这段描述看,汉人虽视“噶达拉康”为“郭达将军庙”,但郭达神像却“着藏式服装、骑山羊,与喇嘛称之为骑羊护法神的‘当钦’酷似一人”,也就是说,汉人并未改变庙中藏人祭拜的“噶达”神像,庙中住持也是一年老喇嘛。事实上,清代民国以来,郭达将军庙始终维持着汉、藏因素混合的特点。清代咸丰、光绪年间及民国时期,当地士绅、锅庄主、秦晋商贾及藏人信众曾筹资对“郭达将军庙”进行过多次重修。重修后的“郭达将军庙”外观呈汉式椽斗建筑式样,庙内建有戏台、惜字库,庙的后殿塑有观音菩萨、李老君、川主像等汉式神祗,但这却并不影响藏人对噶达山神的供祀与虔信,原因是庙内始终供奉着骑山羊、着藏袍、“造形狞严”之藏式山神像,并置藏式转经筒,也以藏传佛教寺院来管理庙中的香火。这说明尽管汉人将该庙视为“郭达将军庙”,却很清楚其同时也是藏人的信仰场所,故对庙内供奉的藏式山神像始终予以维护和尊重。即便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将军会”,“抬菩萨之人,皆为藏族青年”。正因为汉人对“将军庙”的藏文化特质始终给予维护和尊重,才使其成为了打箭炉城内汉藏双方共同表达信仰之场所。清末任职于川边的查骞曾有这样的记叙:“汉夷民讼有不决于心者,两造各设油鼎汤釜,赴将军庙叩决,理曲者多却退。夷民过庙前,必拜而后趋越”(查骞:《边藏风土记》卷1,《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6函,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6页)。可见,清末“将军庙”在藏人、汉人心目中已具有同样神圣性与约束力。“将军庙”所以具有如此功能和作用,根本的原因在于“汉藏民族共敬一人”。此一人,在藏人眼中是山神“噶达”;在汉人眼中则是将军“郭达”。因二者完全同音,又均有“铁匠”身份背景,这就带来了极大的模糊性与交互性,藏人认为汉人是敬“噶达”神而感到喜悦,汉人则以为藏人敬“郭达”将军而感到亲切, 久而久之,便形成“汉藏民族共敬一人”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将军庙”遂成为汉、藏民族在信仰上发生链接和产生亲近感的重要纽带,并最终发展出一年一度藏、汉民众“同祀共欢”的“将军会”。
以上就是打箭炉的故事。这些发生于汉、藏民族之间的故事,不但有趣,还蕴含着丰富的意义,颇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和深入思考。
我国是一个史学传统深厚的国度,因传统史学对史实真实性的强调往往远大于史实意义,故清代民国的文人学士多从传统史学立场出发,认为这些故事纯属“齐东野语”、荒谬不经,多持不屑与排斥态度。如清末黄懋材认为:“(打箭炉之名)附会无稽。愚按唐宋之世,吐蕃入寇,斯为要道,或尝造箭于此,至于丞相南征,由雋入益。程途各别,非所经行也”。(黄懋材:《西輶日记》,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88页)任乃强也指出:“清乾隆时,始有人捏造武侯遣将军郭达造箭于此之说。世多仍之,荒谬之甚矣。”(陈渠珍:《艽野尘梦》,任乃强校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第9页)从其所用“附会无稽”“捏造”“荒谬之甚”等词语看,他们对这类传说故事明显持负面看法。在缺乏人类学及现代学术视野的条件下,这些看法原无可厚非,但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却影响了后人对“打箭炉的故事”背后之意义的思考和探索。
其实,历史从来就包含“真”和“伪”两个部分。前者指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后者指经过历史当事者或前人主观建构而呈现的历史事实。两者一个真,一个假;一个客观,一个主观,但都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前人遗留下来的那些明显属于主观建构的传说、附会,看似荒诞不经,却往往蕴含丰富的思想资源、观念和意义,同样是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重要史实和素材。例如二十四史帝王本纪中,有大量关于各朝帝王尤其是开国皇帝出生前后出现种种祥瑞的记述,它们明显出自附会。从传统史学观点看,肯定是“伪”。但这“伪”既是古人所造,也是当时历史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古人为何附会?这些附会有何功能?它们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根植于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与社会土壤?这些都是更具意味的问题,对理解当时社会及其思想观念同样是重要的史料。
毫无疑问,清代以来汉人围绕“打箭炉”进行的一系列主观建构,是近代汉藏大规模杂糅、交融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生动而有趣的文化案例。此案例非由专家设计,而是出于民间的自发,甚至可以说是民间自发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所包含的文化策略、智慧,尤其是其带来的巨大效果,却着实令人惊叹。细细思量,该文化案例至少蕴含了有关民族交融与文化整合的两个重要规则:
一,通过“借用”达成“共享”和“求同”。汉人的一系列主观建构并非出于“误读”,而是集体意识下的“有意附会”。这种借用藏人的地名、山神名来植入自己的文化因素,既能又满足汉族移民自身的心理需要,又能达成与藏人“共享”,并通过“共享”与藏人“求同”。这实在是与藏人进行文化整合的高超策略和民间智慧。我想,这也许正是汉人绝不“另起炉灶”,一定要借用藏人已有概念来说事儿的原因。
二,在“共享”和“求同”过程中,给对方以足够的尊重。汉人尽管称“噶达拉康”为“郭达将军庙”,却接受“郭达神像着藏式服装、骑山羊”的藏式样貌;尽管称“将军会”,抬神像出巡者必为藏族青年。也就是说,汉人在“借用”和“共享”的过程中,对藏人的信仰始终予以尊重和维护。如此,才最终形成汉藏同祀一庙(藏人的“噶达拉康”亦同时为汉人之“郭达将军庙”)、共敬一人(藏人之山神“噶达”亦同为汉人之“郭达将军”),正是有了这种宗教感情的融通,才发展出藏汉民众同祀共欢、使汉藏文化得以充分整合的“将军会”。
当然,有一点不容忽视,汉人的主观建构之所以能在汉藏文化整合及与藏人互动上产生巨大效果,与藏人的主观愿望有直接关系。打箭炉是因汉藏茶叶贸易而兴,从泸定桥建成以后,逐渐成为新的汉藏茶叶交易中心。汉人将茶从雅安运到打箭炉,卖给藏人,再由藏人将茶叶销往藏区各地。但是,打箭炉汉藏茶叶交易却不是通过沿街集市来进行,而是采取了一种独特交易方式——以“锅庄”为中心的贸易方式。这里所谓“锅庄”,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锅庄”舞蹈,而是指一种特殊的进行汉藏茶叶贸易的客栈。汉商将茶叶运到打箭炉后,入住固定的自己所熟悉的“锅庄”客栈,茶包也堆放在“锅庄”里,马也由“锅庄”照看喂养,汉商及其随员在“锅庄”里不仅吃住免费,还会受到热情周到的款待,他只需要告诉锅庄主自己这批茶的销售价格。锅庄主即为其八方寻找买主,买主找好后,双方进行交割,锅庄主按事先的约定“抽头”(提取佣金),藏商派人将茶叶运走。这是汉藏茶叶的主要交易方式。过去打箭炉曾有48家锅庄,锅庄主最初均为藏人(后来才有汉人“锅庄”),且多为女性,她们大都热情干练,熟知汉藏文化及习俗,人情练达且善于沟通,穿梭和游说于藏汉客商之间,如鱼得水,八面玲珑,人缘甚佳,成为汉藏客商之间特殊的联系纽带和润滑剂。这种以锅庄客栈为中心的汉藏茶叶贸易方式,不但是以信誉为基础,也以汉藏之间的情感沟通为纽带,是一种“和气生财”的典范。所以,这种以锅庄客栈为主的汉藏茶叶贸易的方式,不但造就了大批像锅庄主一样在藏汉商人之间如鱼得水、应付自如的“媒人”,也使打箭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呈现出汉藏民族及文化相互濡染、相互接纳的情形。民国时期对这方面情形已多有记叙,如称当地汉人子女多有“习于穿蛮装的”,“在这地方生长的小孩,差不多没有一个不会说蛮话、唱蛮歌的。其中有的一口蛮话,和康人没有分别”。(董兆孚:《徼外旅痕》,《边政》1930年第4期;曾昭抡:《西康日记(八五)》,《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8日第5版)又记康定藏人则多能说汉话,“富家生活也很优裕,家里用具,多同汉人”。(钱逋仙:《西陲重镇的康定》,《新华日报(重庆版)》1939年3月28日)事实上,打箭炉能够形成汉藏同祀一庙、共敬一人并在宗教感情融通基础上发展出藏汉民众同祀共欢的盛大“将军会”,正是以汉藏民族及文化的相互濡染、相互接纳为其社会土壤。
对康定的汉、藏混一情况,民国时曾有人发出“多数康人已经汉化,或是少数汉人已经康化”的感慨。(石工:《西康问题特辑:康定剪影》,《川康建设》1934年第1卷第2-3期)其实,这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汉化”作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交融之最终结果的一种思维范式,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打箭炉的故事”生动地证明民族间的交融与文化整合从来是双向性的。该案例揭示了民族之间交融与文化整合的三个核心要素——相互需要、相互求同、相互尊重。
历史上,汉人进入边疆地区并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交融与文化整合,是造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途径。但过去人们容易站在汉族中心立场,往往习惯于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融和文化整合简单归结为所谓“汉化”。其实,这种认识的偏颇与局限性不言而喻。台湾地区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早已提出应注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影响的双向性,他指出:“民族与民族接触之时,相互影响吸收和采借经常是双方面的事。汉族文化固然影响少数民族,但其间接受他们文化影响的也应不在少数。”(李亦园:《汉化、土著化或社会演化》,《李亦园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9页)顾颉刚先生亦指出:“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其实,民族的交融与文化整合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并非简单的什么“化”或“谁化谁”所能概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我们提倡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这正是基于民族平等观念的科学、客观表述,它表明民族交融的结果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对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接触,我们应跳出“汉化”、“夷化”的窠臼与思考范式。
以上就是“打箭炉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系作者依据其发表于《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的论文改写,由作者授权并提供澎湃新闻刊发。)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