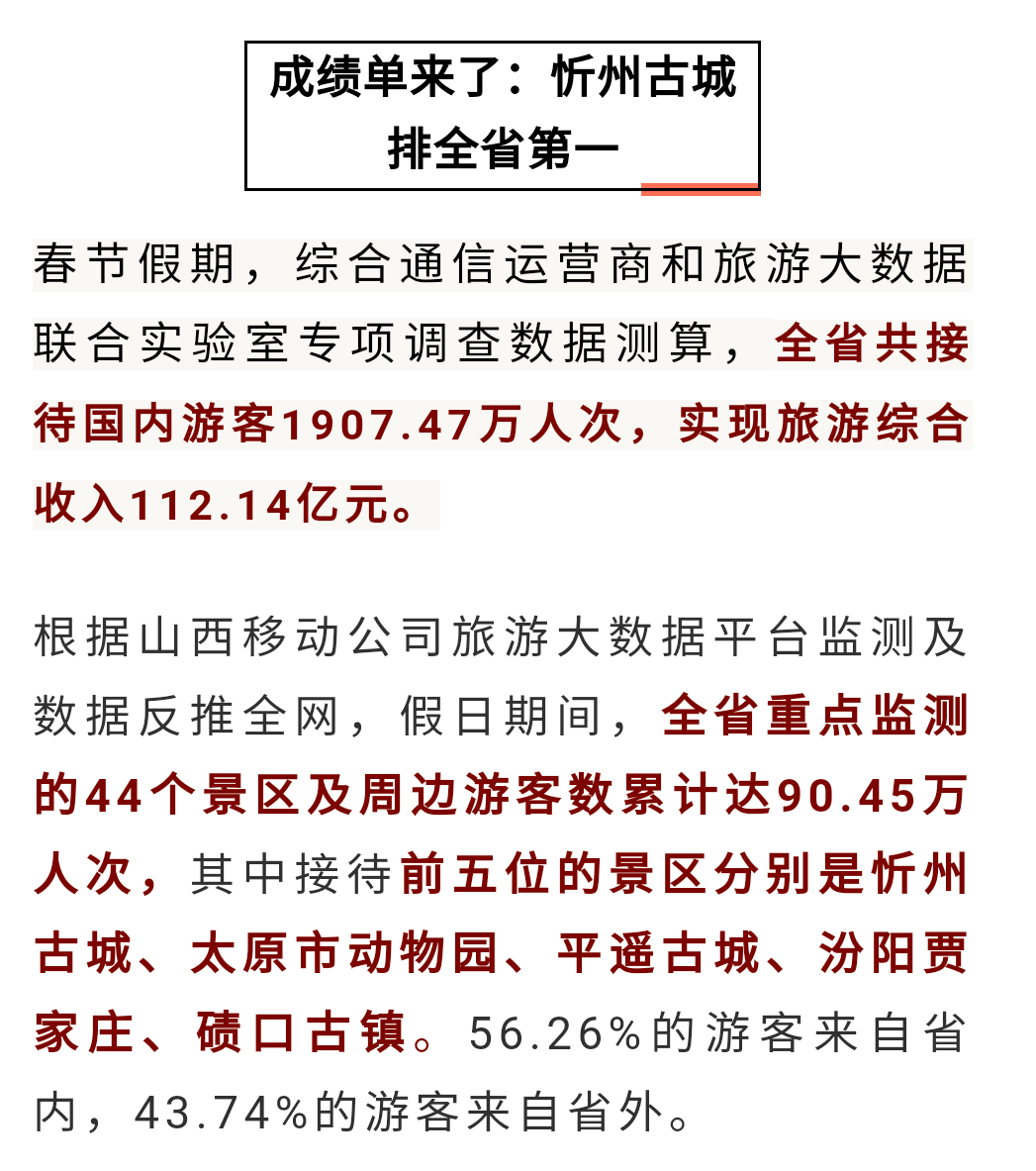在洛河南岸赵村镇西王村和方村之间,一条山河与洛水潺潺交汇。这地方叫山河口。山河口有几汪碗口粗的泉水,一年四季,长流不断,人们都叫它“野狐泉”。
“野狐泉”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从前,这儿芳草萋萋,树木茂密,十分偏僻,常常有许多狐狸出没。其中,有一只狐狸毛色非常漂亮,脑瓜也特别灵动。猎人遇到她想猎杀时,眼前就不由得恍惚出一个少女的影像,以致神志恍惚,捕捉不了。后来这只狐狸大约活了上千年,就修成了像“九尾狐”那样的狐仙……

再说,早年间西王村有米姓兄弟俩,兄长叫米财,爱财如命,长于算计;弟弟叫米来,心底善良,秉性勤劳。父亲死后,兄弟俩与母亲一起过日子。后来,米财娶了个财迷的媳妇,家里可就不安生了。那媳妇先是三天两头地指鸡骂狗,嫌弃米财他妈腌臜派赖,老而无用。不久,老人家就气得悬梁上吊。接着,她又和米财没窟窿繁蛆地摆治弟弟米来:重活脏活都嘿吓着米来去干,好饭好菜都悄悄背着米来去吃。就这还不算,她还在外人面前说米来一片子不是:今天说他柴禾拾得太少,明天说他饭食儿太大,吃得太多……反正是甜咸不对口,横竖都是叉。而米财媳妇一年到头,啥活儿也不干,成天游手好闲,东游游,西串串,这门子进,那门子出,东家长,西家短,说是道非,一屁股眼子白话,因此村里人都叫他“捣白脸”。
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天,天雾星着小雨,捣白脸吆喝着米来去拾柴禾。米来就到山河口树上扳干柴,谁知,天雨树滑,一脚跐空就从树顶上摔下来。好的是,米来正巧掉在一只路过的狐狸身上,因此只是脚脖崴伤了。而那只狐狸却吃了重,一条腿被砸得长流血。米来十分感激这只狐狸,顺手从布衫上撕下一条布,连忙给狐狸包缠好,直看着它渐渐走远,自己才拄着棍一瘸一拐地挪回家中。
伤筋动骨一百天。捣白脸见米来脚脖肿得明之溜溜儿,不能下地,天天窝在家里吃闲饭,壮“劳力”反倒成了大包袱,满肚子怨恨没处出,就成天黑丧着脸,指桑骂槐,抡勺子扳碗。

这船弯在哪儿,米财心知肚明。只是他深知媳妇中用,凡事总看着媳妇的脸色行事。米财咋能忘:当年,为了给自己凑彩礼,母亲狠了狠心,一下子卖掉了家里一头大老腱和一头老兕牛。就这,结婚那天媳妇还嫌“下轿封儿”钱少,硬是不出轿门,逼得米财他妈做不尽的难场——排村儿求爷爷告奶奶地借钱,直到凑够了数才下了轿。这些年,经过媳妇的调教,再加上做起了卖米的生意,米财的财心越发地重了。真真是,越做买卖越知道钱中用,越是有财越财迷。
村里人见米财的心思都钻到了钱眼儿里。背地里就把他的名儿倒着叫——“财迷”。眼下,媳妇嫌弃米来,财迷自然和媳妇合成一气儿,向弟弟开刀。
一天,财迷把拄着拐棍的弟弟叫到跟前,说:“你也十五六啦,老跟着我,也不是办法。你没瞅?你嫂子成天对我黑一眼、白一眼的。”米来一向听哥哥的话,就仰起脸问哥哥:那咋弄?财迷把右手握成拳,然后狠狠向左手掌一砸,说:“我看,咱俩趁早分开算了。”
“分家?”米来压根都没想过,可他知道如果哥嫂的主意已定,那就只有答应。况且自己成天地里活、屋里活没白没黑地干,吃不饱穿不上不说,还得挨嫂子的恶言毒语……“那咋分哩?”
“咋分?按理——”财迷把“理”字拉得老长老长,不知是不好意思说,还是怕引不起米来的注意,“按理说,‘父不在,听长兄’。分家的事应该我说了算,不过,咱俩到底是‘一奶吊大’,因此,还是商量着办。”
“中。你说咋分就咋分,省得叫你吃嫂子的气儿。”
“那——我可说啦,啊?”财迷卖完了关子,开始倒葫芦里的药,“咱父母就给咱俩只留下这十间房子,十亩地。这要给一个人生活还差不多,如果‘二一添作五’,那谁也过不上好光景。与其谁也过不好,倒不如起码能让一个过得好。我看,咱把家产按‘一比九’破开,俩人抓阄儿,抓住九份要九份,抓住一份得一份。公平合理,你看中不中?”
米来说:“反正我不识字,你说咋弄就咋弄。”
这话正中财迷下怀。他连忙趁热打铁,立马叫媳妇取纸取笔来。捣白脸在门外已等候多时,听到吩咐,急忙答应:“好,我这就给你们送去。”其实,纸和笔早攥在她手里头,已经汗津津了。

不一会,财迷把阄儿写好,用手捏了又捏,搓了又搓,然后两手捂住故意在米来脸前头晃了半天才把手伸开,说:“我制阄儿,你先抓,省得旁人说闲话儿。”
米来也不细看,伸手就抓了一个。打开一看,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个“一”字。
财迷狡黠地“嘿嘿”一笑,说:“米来,看清楚。你这可是一份啊。那我的不用看,肯定就是九份了。”说完,顺手就把两个纸球扔在了门旮旯儿。
这样,米来就可怜巴巴只分到了院门口一间又窄又潮的小屋和山河口一亩沙畔儿地。
有道是:天道酬勤。米来硬仗着自小手勤脚快:每天下地比别人去得早些,回来得晚些;去地时,挎篓里背着一路拾的粪;回家时,背的是在河滩拾的柴。因此,尽管地少土薄,但他年年庄稼都拾掇得齐齐整整,吃喝倒也满够。但只是黑来早晚,从地里头回来,一个人还得戳火燎灶地烧火做饭。
左邻右舍见米来这娃子心肠好,又勤快,不是帮这家担水,就是帮那家破柴,就常常端饭给他吃。可米来生性干板硬正,搬死不占别人便宜,往往是送来推去,死活不肯吃……
一天下午,天都黑暗暗了,米来才拖着沉困的身子往家走,肚子饿得“咕噜咕噜”怪叫唤,心想,到家孬好先弄点啥饭垫垫饥儿。谁知道,等他一推开院门时,迎面闻到一股扑鼻的饭菜香。起先,他以为一定是从哥嫂家飘过来的,但等他走进自己灶火,香味更浓。他揭开锅盖一看,“嘿!”一锅雪白雪白的大米饭,上面盖着喷香喷香的炒菜,热腾腾,还冒着气儿呢。
米来觉得蹊跷,这是谁做的饭?他想,大概是西院的李奶奶,因为他常年为她挑水;要不,就是南院的杨二婶,因为他总帮她锄地;还有,东边的香玲姑,他曾帮她担庄稼;还有……可是,问遍了四邻八家子,人家都说不知道。他实在太饿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狼吞虎咽地把饭菜都吃完了。

第二天,米来又是干到很晚才从地里回来。锅里照样又是香喷喷的饭菜。一连多天,天天如此。米来想:咱人虽穷,但志不能短,咋能白吃人家的?欠人家的钱好还,欠人家的情难填。趁早儿,得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
这天,米来吃过早饭,又背着挎篓象往常一样下地干活儿。可不到晌午,他就收拾好锄和锨,悄悄地回到家中,顺梯上楼,将竹篓倒扣,稳稳地罩住自己,严严地藏了起来。
一直等到半后晌,只听得灶火里传出轻细的叮当声,他才轻轻地将竹篓取下,小心地从楼窗口探头下看,“咦……”只见前檐低下,一位少女体态婀娜,奇服旷世。再细一看: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光润玉颜,明眸皓齿。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米来直看得有点发呆。只见她干净利索,三下五除二,饭菜就做成了,然后洗手整衣,看看院内无人,就从容地向门外走去。
米来看到这里,才忽然想到赶紧下楼。他扫视了一下灶火,只见锅台上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两行字,可惜不认得。他连忙叫哥哥念给他听,只听财迷阴阳怪气地念道:“西沟西,东方东,老槐树上吊金钟。打一下,嗡三嗡,自有来人做接迎。”米来听了,仿佛马上神领心会,急忙从后面撵了去。跑到村边,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眼看离那女子只有十几步远,但就是撵不上。一直追到山河口,那女子突然间就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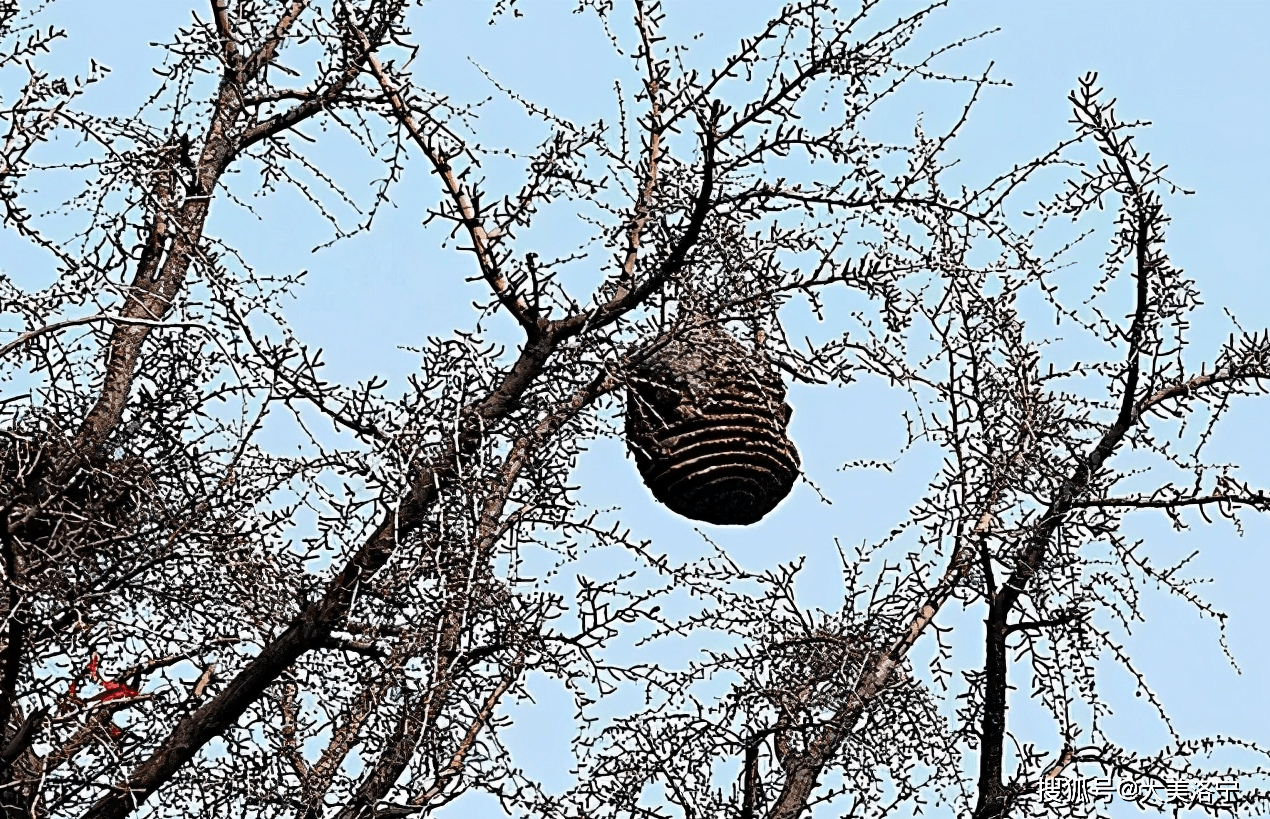
米来正在纳闷,只见那棵一搂多粗的老槐树上吊了一个大“葫芦包”——马蜂窝。米来顺手拾起一块石头,照着“葫芦包”扔去,只听见“嗡”“嗡”“嗡”三声,群蜂炸飞,遮天蔽日。米来正要躲闪,一转身,那少女又站在了面前。她一把拽住米来的手说:“闭住眼,跟我来。”米来闭上眼睛,约摸只走了三五步,就听那女子说“好——唻”。他睁眼一看,已来到一座清堂瓦舍的四合院。
那女子顺手从水壶里倒了一碗清清的凉泉水,说:“赶快喝点水吧。”米来因为追赶,正是口干舌燥,就一气儿把水喝完了。立时,他觉得甘甜无比,肚子不渴也不饥了。他忙问:“这是啥幌子水?”女子说:“这是我家修炼千年才得到的济世甘露。”米来说:“我们素不相识,你为啥总是给我做饭呐?”这时,只见那女子的脸倏然泛起一层红晕,然后“嘻嘻”地一笑,扭向一边,羞羞地说:“还不是为了报答那年你的救助之恩?……”
且说米来在这里住着,每天吃的是白米细面,山珍海味;睡的是用南海珊瑚做的阁子床,铺的盖的尽是绫罗绸缎。白天,女子教他识字读书、唱歌跳舞;晚上,教他翻看方圆十几个村子的花名册子,识别册上哪个是善良的百姓,哪个是歹毒的恶人……
有一天,米来独自在院里转悠,忽听到后头院子里有人 “哎呀、哎呀”的怪叫唤,并且声音十分耳熟。他轻轻推了推后院的木门,从中间的门缝中隐约地看见,一妇人脖子上戴了一个铜钱模样的大木枷,身子贴墙而站,呲牙咧嘴,表情十分难堪。

米来用手揉了揉眼睛,再定睛看时,只见这妇人矮矮的个子,瘦瘦的身材,短而扁的脸盘上镶着一双三角眼,塌鼻梁下,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这长相简直与他捣白脸嫂子一模一样。他刚想喊着询问,只听得那女子在背后说:“这是一壶‘济世甘露’,你带回去好赐福百姓。它不但能浇地,而且还能医治疑难杂病。”米来正想问这壶水咋会有恁大的用场,抬头看时,那女子和房院已全然不见了。霎时,他又回到了那棵大槐树底下。
米来只好提着壶往家走。走着走着,他潜意识地把壶里的水往地上一倒,谁知,地上立时咕嘟地冒出一股碗口粗的泉水。他很好奇,又试着一连倒了几处,处处都咕嘟咕嘟地冒出了清清的泉水。
从此,天无论多么旱,这里的泉水总是旺旺地日夜流淌。泉水流进庄稼地,庄稼就长得格外茁壮;流进竹园,竹子就长得茂密修长;流进菜地,白菜连菜膀子都又脆又甜没有筋。水泉儿旁边长满又粗又高的苇子,破出的苇篾又白又薄又结实。有一年,遭上百年不遇的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其它地方都闹饥荒。只有这儿因有野狐泉水照应,几千亩庄稼依然水灵茁壮,获得了好收成。西王村的白菜、粮食,方村村的苇席也从此在方圆数十里出了名。更神奇的是,这股泉水还治好了很多疑难病。附近村里的人得了病,凡吃药无效的,无论多么离奇,多么严重,只要一喝这里的泉水,不是痊愈,就是转轻。为了感谢这位狐仙姑,人们自发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在野狐泉边盖了一座庙。每逢初一、十五,虔诚的香客络绎不绝,烧香参拜,感谢狐仙姑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那天米来往家走,还没有走到大门口,老远就听到嫂子“哎呀、哎呀”地大声叫唤。他一进院儿,财迷就气急败坏地一把拽住他,说:“好兄弟,你咋得回来了,赶紧来看看你嫂子。她脖子上活像压了个磨扇儿,肩膀骨上红青黑蓝,从早到晚,困疼得死活不下。”
米来心想:自打分家后,哥嫂又雇了两仨人干活,整天吃不愁,穿不忧,小腿压大腿,养尊处优,福还享不完呢,咋还会得这病那病?但他忽然想起……难道那后院里受刑的果真就是嫂子?于是,他就把自己所看到的给哥哥述说了一遍。
财迷听了,暗自称奇,连连敦促着米来说:“不管是不是,眼下救人要紧,救人要紧……你嫂子已经病了多日子。我是有病乱求医,做生意的钱都快花干了,腿也快跑折(she)了,还是不济事。好弟弟,‘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们兄弟的情份上,你无论如何得去求求狐仙姑姑,兴许只有她才能救下你嫂子的命……”
米来持不住哥哥一篮儿两筐儿的好话,第二天一早,就又来到山河口老槐树跟前,照着先前的法儿进了院子。

他一见那女子就赶忙说:“你们惩罚的那个妇人不是别人,是我嫂子啊!”那女子听了,收了脸上的微笑,鼻子冷冷地哼了一声,然后不耐烦地说:“知道,知道,当然知道。这方圆邻村的人谁不知道?你嫂子那人奸心魔道,有名的‘捣白脸’,既识戥子又识称,啥黑心钱她不敢要?你没有看,她的头都被钱眼挤扁了:南村黑娃弟兄俩给她做了半年的活儿,拿到的工钱原来是张‘假票子’;西边明善老汉走路不小心碰了她一下,她讹了人家两布袋黑豆钱;后地墁巧女她妈,说起来还是她远门子姑哩,借了她二升米,大年下她两手一抻,挡住路不叫人家过,立逼时拷叫连本带利地还米钱。巧女她妈没办法,去下沟底儿借了一遭儿钱,还清了账黑洞洞才回家……你们弟兄俩分家,鬼主意就是她出的。两个阄儿上写的都是‘一’字,不信,你看看。”说着,女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兜儿,从里面倒出两个小纸蛋。米来把她手里两个纸蛋蛋儿仔仔细细拆开,一看,上面果然都是先前哥哥写的那个“一”字。女子哈哈一笑,说:“只是怕你不信,我才一直存着它。”
可米来到底是心底善良,明知嫂子奸诈,但仍向女子苦苦求情。女子说:“‘人在做,天在看。’好坏报应只是迟早的事。心肠黑、钱心重的人,在这儿受的是‘钱枷刑’。为啥叫你嫂子受这刑,就是因为她花的黑心钱太多。天怒人怨,我也是不得已啊!等到啥时候她的黑心钱花得差不多了,病才可能慢慢好转。”说到这儿,她看见米来一副难堪的样子,又怕他回去没法交代,就转口说:“好吧,今儿个看在你的面上,暂且放她一码。但日后她若旧性儿不改,继续作孽犯条,那咱可有言在先,定要加倍惩罚。”米来听了,连忙替哥嫂满口应承。

果然,等米来回到家时,嫂子的病已经好了。米来把向仙姑求情的前前后后对财迷夫妇说了一遍。捣白脸自知自己以前对弟弟、对亲戚和乡邻们做过许多背良心的事,因此,羞得脸从额颅盖一直红到了脖子根。这会儿,她的头像鸡叨米一样地点着,哪儿还敢有半句的分辨。
从此,财迷夫妇二人初一、十五到野狐泉庙里虔诚进香,不敢有半点怠慢。
米来长到二十来岁,一直没有成家。有一年七月初七,他巴明起早去山河口种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家。
后来,人们都说,米来与狐仙姑成了婚。因为有人黑地里看见过,他俩在野狐泉湖面上,脚踩着荷叶,手挽着手,浅吟低唱,翩翩起舞……
人们都说,即便现在他们还一直在护佑着这里正直、善良和勤劳的人们。

作者简介:山子,1950年生,洛宁县人,大专学历,曾有军旅生涯,历任班长、排长、政治指导员,转业后,曾担任副乡长、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喜爱文学,1996年开始在杂志和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