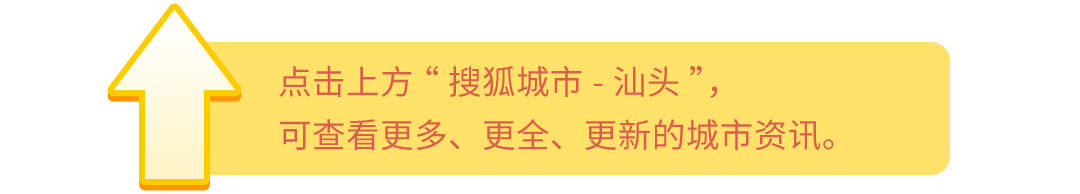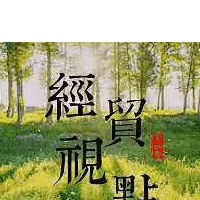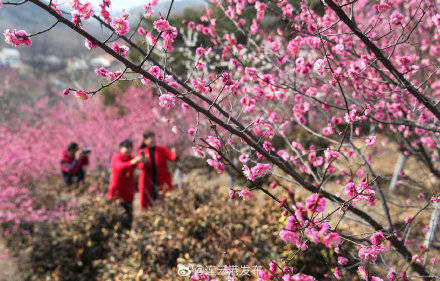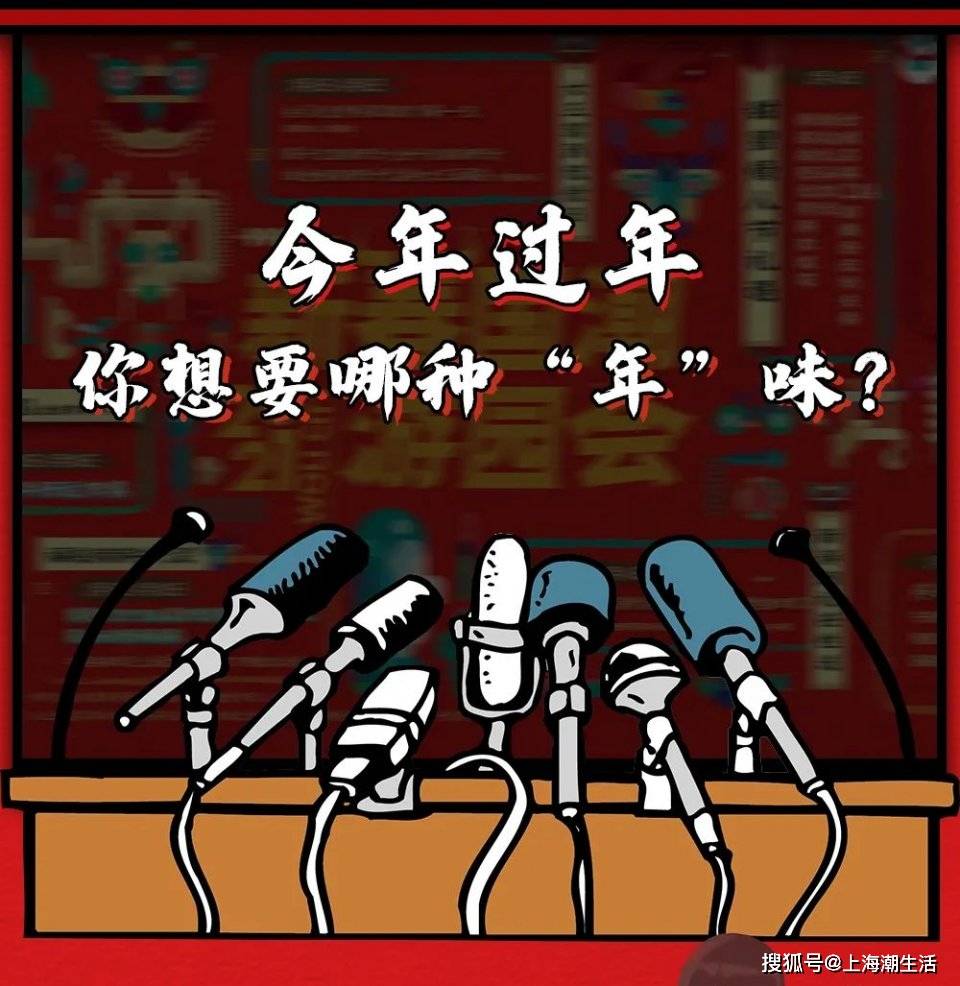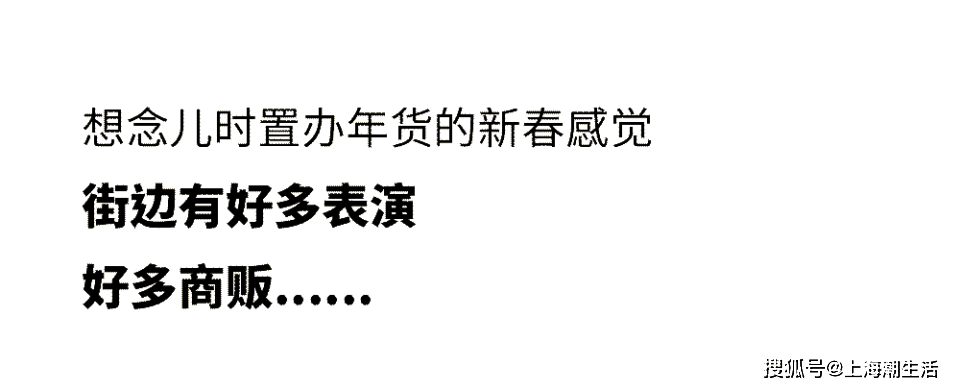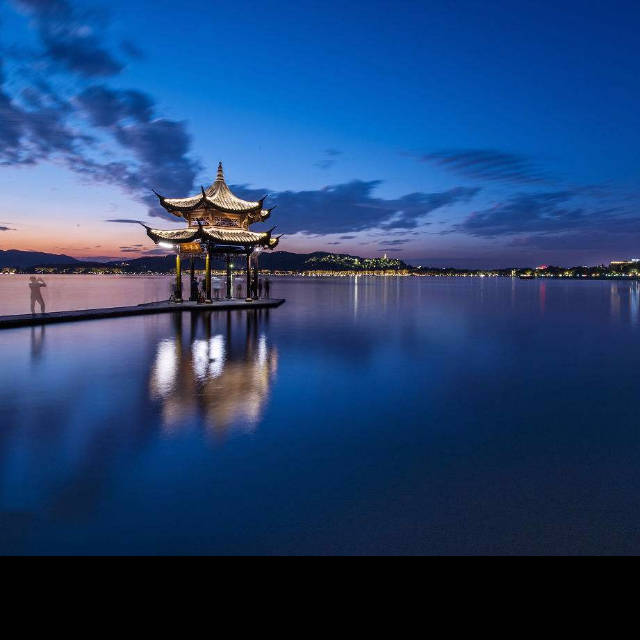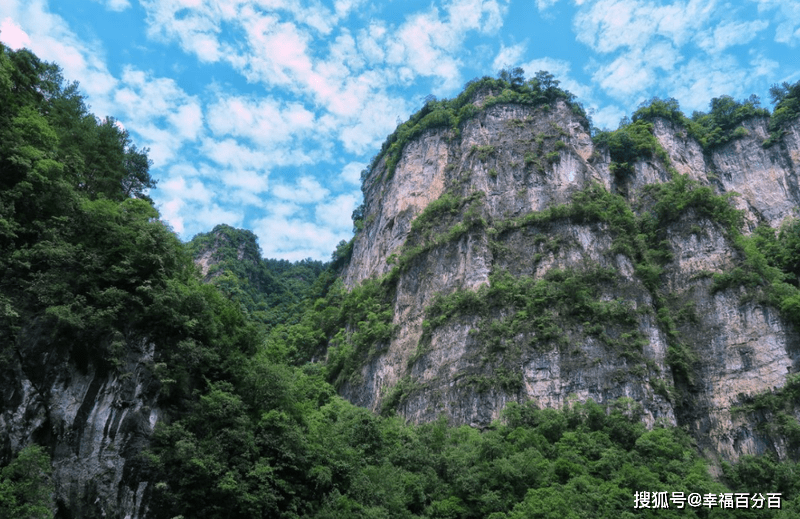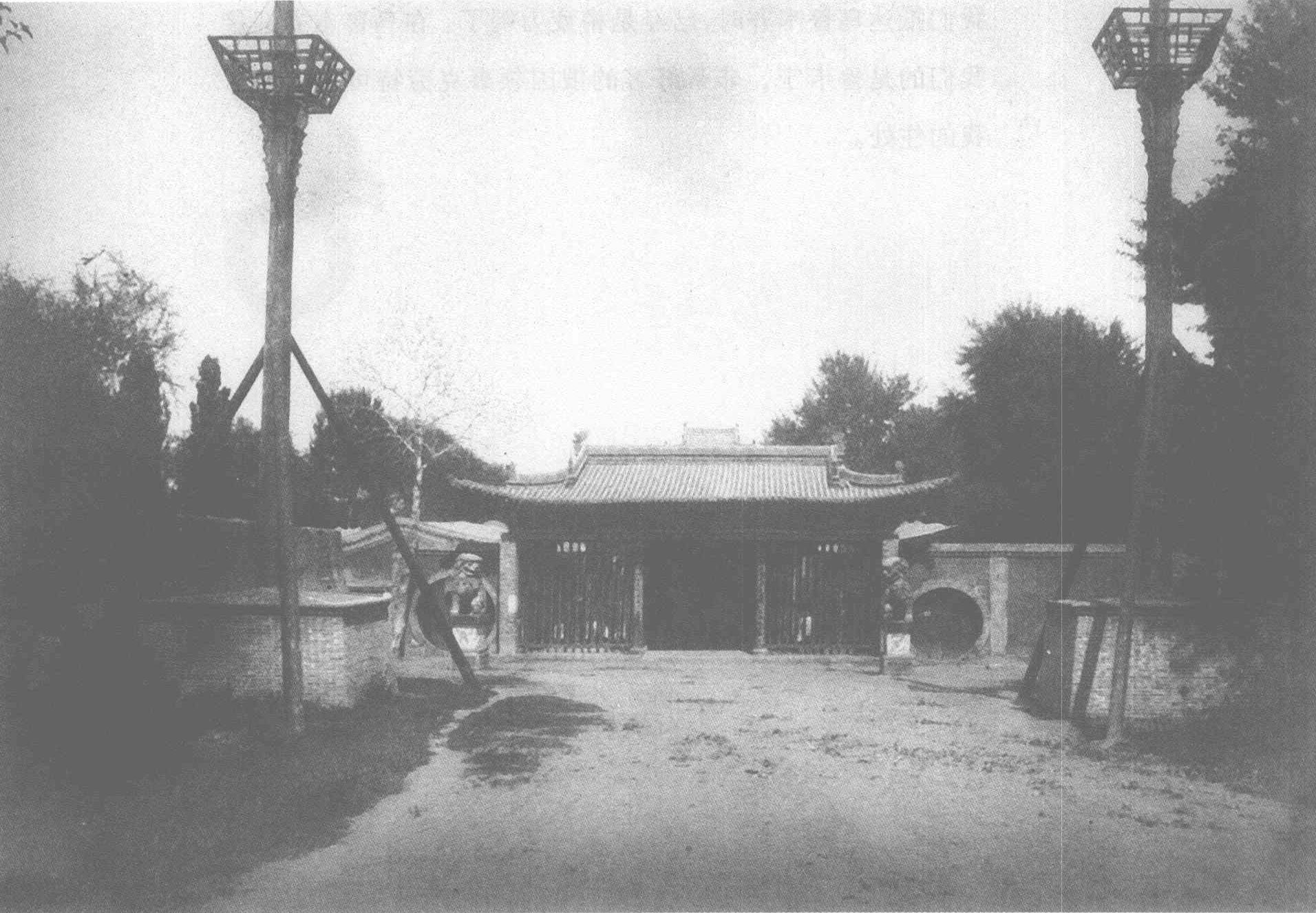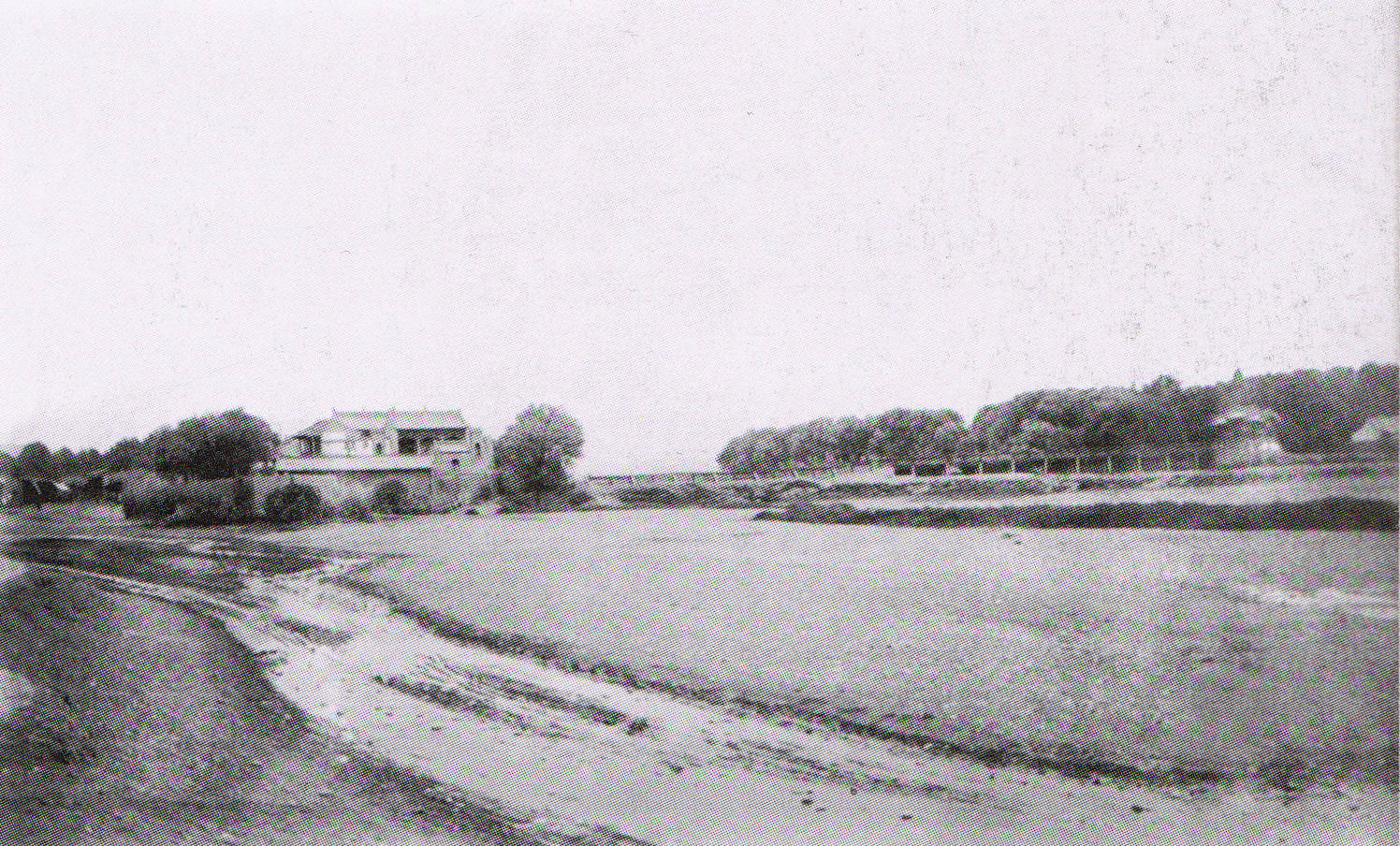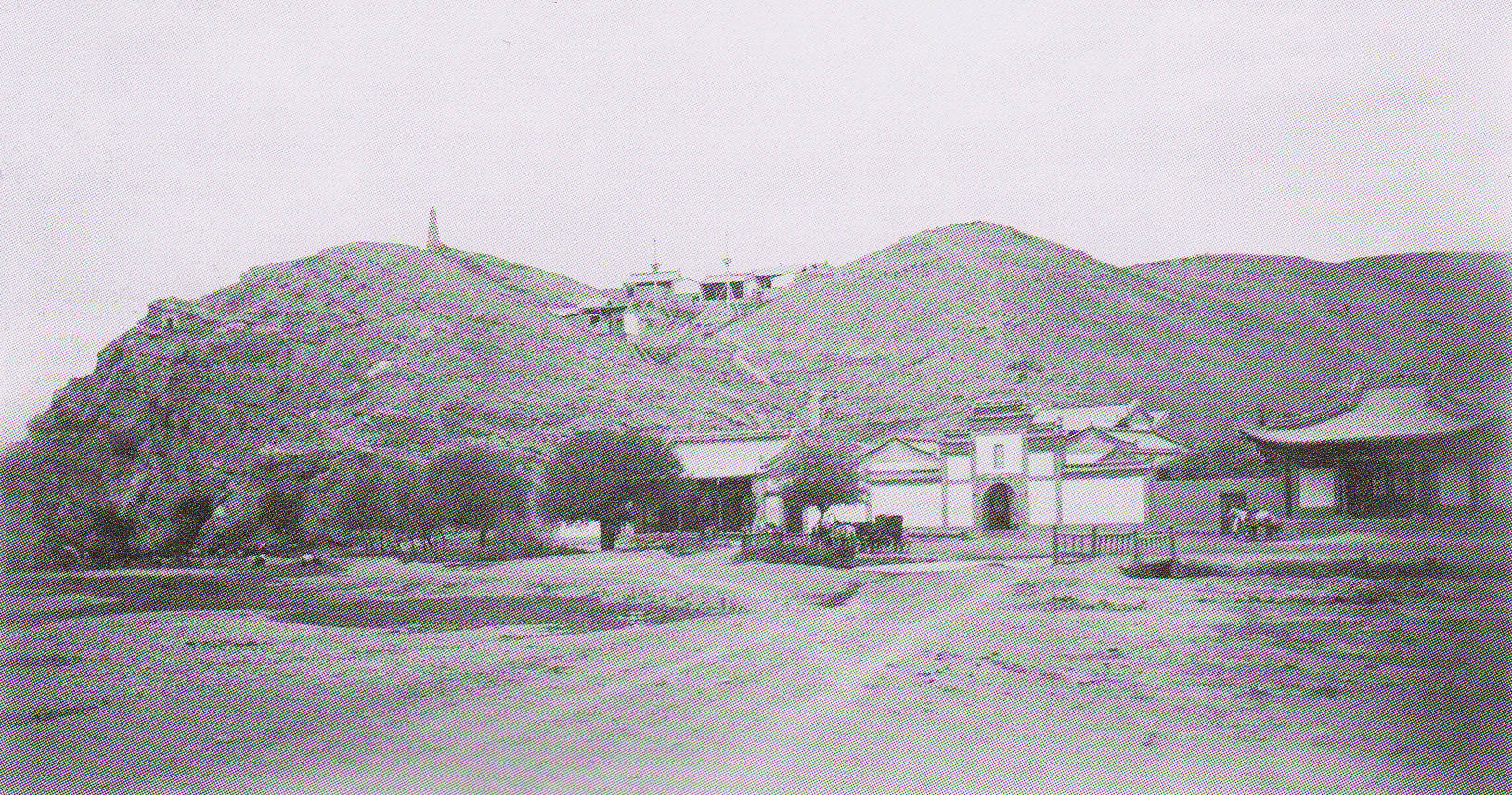故乡火铺
姚明祥
寒冷的冬时,让我想起故乡山寨的火铺。
故乡渝东南土家苗寨,家家都有火铺。“树大要发桠,儿大要分家。”成年子女分户另居,新炉升火冒烟的吉日佳期,前辈必“包火”。老火铺上,一把茅草包一粒坚硬的红炭,端一碗衣禄富贵米,跑去递给新居恭候的儿子。儿子搁米于桌,置火包于新火铺内,俯身嘟嘴一吹,焐着冒烟的柴火砰然而亮,火焰高燎:“引起了!”可谓薪火相传。火铺是一脉香火的延续。
火铺,离地两尺高,泥夯火心,插三脚,凳鼎罐;四方木板铺就,各方宽窄不一。最宽的一方称之为“上面火铺”,正对此方的就是“下面火铺”。火铺上摆放了“草墩”,干枯稻草卷制的圆圆坐具,软和耐用。整个火铺可容坐十多人。“上面火铺”还可当床临时使用。扫灰除尘,铺上棉絮被子,就可歇客。所以不叫“火炕”“火塘”而叫“火铺”。
只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和尊贵的客人,才能享有坐上面火铺的权利。咯吱一声木门开,主人笑脸迎出来:“快请上火铺向火!”待客人刚落座,男主人就双手捧来一匹牛肉色样上好的毛草烟:“抽杆耍!”女主人说一声:“烧口开水喝!”就抱柴架锅,站在地上靠着下面火铺忙开了。知道风俗的人,就晓得是弄吃的。
山寨过年,一屋老少必在火铺上吃团圆饭。团家气,圆族梦,拧紧传统孝和,抖落一年辛尘,吸纳新春热能。
雪天里,大家团团围坐火铺上,家长里短,吹牛扯谈。火心里烧着钢坚铁硬棒棒柴,牛头马腿树疙蔸,哔叭炸响,火星飞溅。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十分粗糙而又兴奋的脸。小细娃挤在大人两膝间,红火灰里刨出童年乐趣,焦糊的烧红苕,甜润浆厚了小黑嘴。年轻妇女规矩端坐,穿针引线,织爱编情,不时招呼跷二郎腿的男人:“都片臭了还不晓得?烧烂了你不心痛哟?”自然有人接下句:“人家扎鞋子的,可痛在心尖尖上去了!”男人就扬眉吐气,显出格外的得意来。汉子们嘴角叼着“黑武器”漫不经心地吸着,白烟灰寸长也不掉落,无言地彰显男人的坚韧与阳刚。老人们喝够了火边茶罐煨着的老荫茶,嘴里徐徐拖出长长的竹节烟竿,一拍膝盖,抢过话题:“嗨!我们见过的阵仗摆出来,要骇坏好多人······”就开始重复一个遥远而又古老的故事。
记忆中,听得最多的是表伯伯的龙门阵。他姓冉,我祖母姓冉,弯来拐去依起辈分叫他表伯伯。他好像什么故事都有,妖魔鬼怪的,忠烈尽孝的,强悍凶猛的,勤劳善良的,仁义慈爱的,哪样都讲。他高大的身躯坐成一尊大佛,扯了几句闲言过白,言归正题:“上次摆拢······”
确实是个摆龙门阵的高手,现在乡里民间很难再找到他这样的人了。一字不识,口若悬河,三天三夜不打重台,而且精彩纷呈,让人久久难忘。正在大家聚精会神,洗耳恭听时,他突然吱的一声踩了急刹车,把满屋男女老少的听兴甩挤一团撞向他!
“‘那热’(地方土语:哎呀)不摆啦,晚上又来!”他摇头摆首,起身欲离。
火铺上的听客赶忙扯着他的军大衣不松手:“后头啷个啦?摆完起!摆完起!”他仍把腰身弓着,屁股翘着,保持随时跳下火铺离开的姿式:“肚皮唱空城计了!”母亲也拦着劝说:“快坐起,摆完起,我来弄晌午。”
“那好嘛,你们硬要听,我又接着往下摆嘛!”他这才坐回原处,重拾话头。
母亲架耳锅,炒阴米,拿出家中“奢品”,米籽泡泡冲糯米酒水喝。一人一碗,一饱二醉。
我惊异于表伯伯的口才。也许他旧时在龙池老场茶馆听过说书,也才有那么多的龙门阵可摆,也才学会摆到惊险处、把人胃口吊起、故意卖关子求充饥的鬼把戏。其实,他至死不知,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他无意之中也填充了我们老老少少寨民的“饥腹”。
现在,山寨都修了二三层楼的新房,楼房也不想柴火熏黑,就在屋顶搭建了火铺屋,依然保持寒冬烤柴火的老习惯。这火铺也由地火铺升高为楼火铺。只是坐得更高,谈得更远。
而今,火铺上打堆的人少了。我越过千里冰雪,伸出一双赤手拥抱故乡,仍感火铺的祥和温暖,还有什么世间严寒不能挺过呢?
(作者单位:酉阳自来水公司)

版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