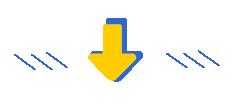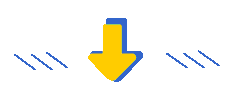梦境中酣睡的原始森林。

阳明山以竹海为生的劳动人。
去探寻身边的“诗和远方”,往往有着经意,也有着不经意。经意是虔诚与披荆斩棘,不经意是随喜与漫不经心。“二月春光好,阳明日渐长。柳垂金屋暖,花发玉楼香。”吟诵着唐代长沙窑诗文壶上的明媚句子,在“小寒”这个一年之中几乎最冷的节气,我来到了北望衡岳、南近九嶷的阳明山,竟看到了日暮途穷处的绝美晚霞。
寻着唐人的足迹看山水
阳明山是“潇湘之源”永州境内的一座山,“朝阳甫出,而山已明者,阳明山也”。虽然它“秀齐九嶷”,但也许因为“荒蟠百里”,并未留下与它的美丽足够相称的名人轶事。连永州司马柳宗元都只是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极不情愿地匆匆路过、并未登山,今人若游永州山水,也是先去人迹更盛、开发得也更多些的九嶷山。
说柳宗元极不情愿地经过阳明山,并非言过其实。虽然身处“元和中兴”时期,他的个人际遇并未改观,而经过阳明山的这一年,又恰逢大旱,不信鬼神的他,作为下属却只能随永州刺史韦中丞前往黄神祠求雨,自然也非本愿。但即便这样,他还是见识与感受了阳明山的山水之美,所以笔下的“永州九记”之《游黄溪记》,一如他写景的非凡功力,奇秀之美令人神往。
我寻着唐人的足迹,来到阳明山却是本愿。所以尽管不是它最为称道的时节,我依然看到了比预想还美的胜景。
奔着有着1625米海拔的主峰方向,潇水穿山而过,我绕山而行。“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颏颔龂齶”,在阳明山中穿行,没有一处山体不是有着落石的警示牌,盘山的路上频频看见似乎刚落下的碎石。然而我携着最喜欢的,燃着最欢喜的,内心只随着马达奔腾,却也无比的笃定。
也许是太冷了,又是黄昏,山路也崎岖蜿蜒,一路上只需偶然会一会极少极少的车,也不敢彻底松懈。也并未见到一个游客,除了以竹为生的手艺人。这时候的温度应该在零下了,我下车拍照时,往往不出1分钟,手便冻僵,然而那些以山中竹海为生的人们,还仿佛不知季节与温度般,气定神闲处理着竹子,不疾不徐,依照各种工序,井然归类。虽然感动与敬意油生,但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嘘寒问暖反而是种打扰,正如“沉沉无声”在柳宗元的眼里是一种深厚的“有声”。这些劳动者的身影也是风景,我默默驻足行礼,简单记录后便悄然离开。
雾凇和杜鹃花还不是最美的
阳明山似乎更适合春和景明时节去看的,故长沙窑诗文说的是“二月春光好”,而且一天之中,去观赏朝阳更是符合其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却是到了日暮时分,依然想着在天黑之前尽力前行。
也许总是怀着虔诚之心不设限的行走,山水往往给我一些意外的褒奖。这一趟来,既不是大小长假有着充裕的时间,雾凇也不是被风光摄影师心心念念的最好看时段,更不是杜鹃花漫山遍野怒放吐艳的季节。
但整个阳明山,似乎都被我包了场,让我独享保存完好的数万亩原始森林,一种旷古绝今、天地悠然之感油然而生。
如何肆意行走?赏山水,历人生,要追求无为还是有为?竹林七贤第一的阮籍是“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他的本意是潇洒随性的,但在常常忧愁焦虑的世人眼里却是不怎么好的标签。
我却在“日暮途穷”这种时空坐标里,看到了瑰丽无比的晚霞与仿佛做着一个奇幻梦境的森林。当我终于登到万寿寺的时候,正好寺门“哐当”一声落锁,山体中是不是有华南最大的黄杉和红豆杉群落已不可辨,有多少野生品种的杜鹃也不可数,我甚至来不及去探寻那始建于宋的寺里是否还有什么珍贵遗存。这倒利于正好省下多余的力,用极简的目光,专注而纯粹地欣赏那大自然神笔不经意呈现的奇观。
小寒这一天的太阳落山前依然缱绻在云层里,如送别千里不忍告别的诗人,它把最绚丽的热情与光芒,为云层镀下几段闪着金光的边,边界锐利,暖色在冷调里柔和渐变,并继续往下投射了一股无限深情的光束,在黄昏的蓝灰色天空里极为瞩目。那光束点亮了一盏柔和的灯火,云层下的山峦与森林,睡意阑珊,仿佛做着一个奇幻梦境。
最好的行走与收获,便是如此吧。美是无处不在的,美也其实是不设限的,既在山河里,也在心胸中,于众人非优先之选,在我处为独树一帜。
文、图/溪客(专栏作者,插画师,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