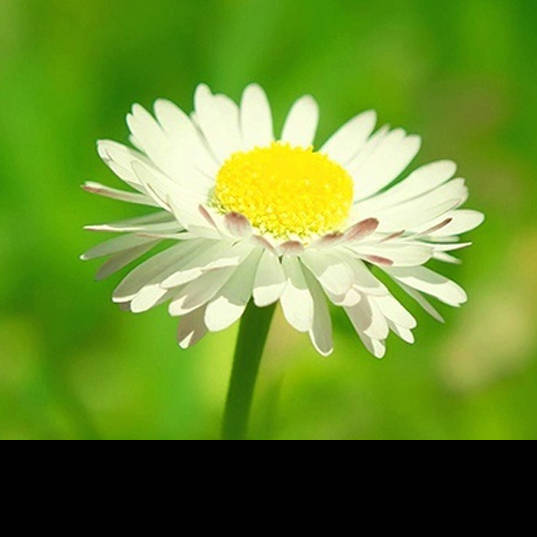自从美国的新冠疫情严重以来,湘西凤凰的朋友们陆续在微信上询问我和家人是否还好,什么时候回国探访。这其中包括龙大哥。龙大哥家里四兄妹,他是老大。最小的弟弟和他同住龙村,与我年龄相仿,很是熟络,我管他叫“三哥”。我上次见三哥时,他已经处了一个女朋友小胡。这天和龙大哥报了平安后,我问他,“三哥和小胡结婚了吗?结婚要告诉我哦。”龙大哥回复说,“三哥和小胡两个自己当是结了。结婚嘛,就是自己认可的人就行了,也不请客吃饭怎么的。”
湘西凤凰的这些朋友,包括龙大哥和三哥都曾是我在湖南凤凰做田野调查时的受访者,但更是我的朋友。我第一次去凤凰是2002年春节,正是凤凰旅游快速发展的前夕,近二十年来,我前前后后去凤凰做了九次田野调查,见证了在旅游语境下凤凰的个体化进程,也亲历了凤凰的朋友们在其中的聚散离合。
当下,个体化在全球普遍存在。凤凰也不例外。根据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的阐释,个体化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从早前的无所不在的工业社会中的社会范畴(比如家庭、亲属关系、性别、和阶层)中脱嵌而出,标志着个体和社会二者关系的类别转变。我在此以凤凰为案例,探讨因旅游加剧的个体流动性对当地村民与之家庭关系的影响。
凤凰旅游和个体流动性
凤凰县地处湖南省西部边缘,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角。凤凰曾是全国贫困县之一。2000年,凤凰县的人均GDP仅为全国人均GDP的29%。2001年11月,凤凰县政府把当地的八大主要旅游景点的50年经营权以8.3亿元转让给了黄龙洞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县政府陆续把其他旅游资源的经营权转让给了别的发展商。从 2002 年开始,凤凰的旅游经历了两个阶段:1)集中于凤凰古城,由黄龙洞公司主导;2)扩散至凤凰山区,由其他私人老板开发的“苗寨游”。

2002年的凤凰古城北门码头。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2005年,旅游旺季时的凤凰古城北门码头
凤凰的旅游带动了交通基础设施的飞速提高。凤凰山区交通一直不便,只有镇上才有公交小巴。以龙村为例。龙村在2002年前没有机动车道,村民们去镇上赶场一般要徒步一个多小时,往返不易。随着机动车道的修建,摩托车、旅游车和村民自购的用来接送游客的面包车越来越多,龙村的村民流动性大大提高,即便日日往返于村子和镇上也不为奇。
凤凰的旅游给土地带来极大的增值。凤凰古城沱江边的小店铺租金从九十年代末的几百元涨到如今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越来越多的村民从事与农活无关的生计,因而愿意把土地使用权长期租给私人老板。生计与土地的剥离更加快了村民个体的流动性。
凤凰的旅游同时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就业机会是以流动性或愿意离家为前提的。劳动力市场是个体化的背后推手。正如乌尔里希·贝克和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 (Elisabeth Beck-Gernsheim)所说,只要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就必定经历流动。灵活的但同时缺乏保障的就业机会(短期合同、兼职、半职等)快速增长。凤凰的旅游无疑给当地村民带来更多非农业收入来源,而他们当中很多人本就急于摆脱土 地的束缚。
三哥和小胡:结伴不结婚
三哥有女朋友了。大家都很高兴。十几年前,三哥老婆和三哥在杭州打工期间跟别人走了,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凤凰旅游发展起来后,三哥从杭州回来,一直努力谋生:在村里开过接送游客的中转车,也在龙大哥的家庭餐馆帮忙,后来自己也开了家庭餐馆,又学着自己酿酒卖酒。龙大哥一直盼着他再找一个老婆,村里的大嫂们也热心介绍。那时他总是说,“我现在就只想挣点钱。我也没时间和钱来娶老婆。”
小胡比三哥小两岁,是嫁到龙村的。小胡的丈夫几年前在外打工时遇到矿难去世,留下一对儿女。小胡和她哥哥合伙在凤凰古城的沱江边经营一个铺面,卖凤凰特产。小胡以前也在村里开接送游客的中转车。村里最多时有十几台中转车,每个车每天排了号接生意。小胡去凤凰古城开店后,就把自己中转车的号给了三哥,等于把分到的生意给三哥。
上次去凤凰是2016年暑期。刚到的第二天,我就央着三哥带我见小胡,我请他俩吃饭。三哥那时刚学会酿酒,白天在村里酿酒喂猪开中转车,傍晚开车到凤凰古城给店家送酒。送完酒后,有时就在凤凰古城的小胡的出租屋过夜,然后第二天清早在批发菜市场给龙大哥的家庭餐馆买好食材运回村;有时连夜赶回村里。天天忙得像个陀螺一样。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三哥送完酒后带我去小胡的店里找她。夏夜的沱江边游人如织。小胡站在店门口,身边摆着两盘姜糖,忙着招揽顾客。小胡舍不得放下生意去吃饭。三哥提议就去隔壁的餐馆吃。我和三哥先去提前点好菜,菜上齐了再叫小胡来吃。小胡三五两口吃完就回店里了。我和三哥吃完后,回小胡的店里坐了会,看她张罗生意。因为游客多,店要午夜后才打烊。小胡让三哥带她在店里玩的小儿子先回她的出租屋。起身前,三哥从柜台上取了一包香烟,递给小胡五块钱烟钱。三哥说他们两个“分得很清”。

2016年,三哥和小胡在小胡的店铺里
第二天一早我搭三哥的顺风车去龙村时,我问他为什么昨晚在小胡店里没帮忙,只是在那坐着。三哥说:“我以前也帮她,然后我自己太累了,睡觉的时间更少,第二天影响我自己做事。”他接着解释道:“我现在不帮了,主要因为她的生意是和她亲戚合伙的。帮她相当于帮别人。事实上,我给他们店里做了摆货的木板架,花了我两天时间。如果他们请人做的话,要花几千块。我没收他们的钱。我本来也可以收钱的,然后把这个钱单独给小胡。”我问他,“那你怎么不告诉小胡?”他答道:“我说了,但她说我怎么这么小气。”
三哥继续说道:“她也没到村里来帮我忙。我虽然没在店里帮她,但我去她出租屋时扫地、做饭、洗衣服,让她回来时能休息。”我想起来在小胡店里看到的三哥做的酒,说: “那小胡帮你卖酒了哦。”“她不是替我卖。她从我这里用批发价买去在自己店里卖,”三哥澄清道,“我们的钱是分开的。我的钱以后要给我的两个小孩的。不然,他们能依靠谁?等我老了,我也要依靠他们。对了,不要等我的结婚喜帖。我不会结婚的。”
吴海的一家:家庭为个人
2005年我认识吴海时,他们一家仍在吴村。这些年来,吴海、他老婆和他们成年的三女一子陆续搬到凤凰古城,从事和旅游相关的小生意。小女儿吴霞嫁到凤凰古城后,先是在街头出租苗服给游客拍照;然后在沱江边租了一个小门面卖服饰围巾,把给游客拍照的生意转给了她二姐吴云做。接着吴海两口子也搬来凤凰古城,接手一个江边客栈来经营。吴云也在吴海两口子的客栈帮手。
因为经营客栈太累,而且生意也不好,吴海两口子没两年就结束了客栈的生意。在沱江边一个酒吧的下层租了个巴掌大的地方卖旅游纪念品。吴海老婆看店,吴海送饭。吴海近年身体不太好,一个月内就因为支气管炎住了两次院。
吴海两口子暂时和吴云住在一起。吴云没做事了,在家照顾父母和小学六年级的儿子。吴云刚买了一个旧的单元房,在凤凰古城中心,旁边就是超市和医院,很方便。吴海告诉我说吴云的丈夫在湖北做照相生意,近来挣了些钱。
吴海两口子在凤凰古城买了商品房,当时借给他们的儿子、媳妇和媳妇的父母住。吴海的儿子在镇上的交管所工作,在吴海看来是“体面的工作,但工资不高”。吴海两口子经营客栈的初心是想以后交给儿子打理。儿子的岳父母在凤凰长途客运北站附近有一栋楼,租出去了。儿子和媳妇两人自己也买了商品房,正在装修。吴海和我说,他和老伴更愿意和女儿住,不愿和媳妇住。
吴霞和她丈夫也买了商品房,和八岁的女儿还有公公婆婆一起住。在那之前他们都住在公公婆婆的老房子里。现在老房子翻新加建了一层,签了十年租约给人经营旅馆。我近年每次暑期去凤凰,都会挑一个午后去吴霞店里找她,午后是一天中生意最少的时候。上次去找她,店面没人。我叫了几声,她才从里间的帘子探出半个头来。她趁着游客少在里间的躺椅上午睡。

2014年,吴霞(右一)在店里帮助游客挑选围巾
吴霞从里间抱出个大西瓜。她去对面小铺借了把刀,麻利地把西瓜切块,给左右邻铺送去些,然后我俩一边吃一边聊一边看店。后来吴霞的丈夫来店里,吴霞把店子交给他,一定要拉着我去吴云家吃晚饭,说是我难得来一次,她大姐刚好也回来了。吴霞大姐早年就去了上海打工,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没在凤凰见过她大姐。
从吴霞的店走到吴云的住处只要十几分钟。吴云的新居在一个老院子里,以前是县粮食局的宿舍。尽管院楼外观破旧,房子里面恍然一新,新刷的墙漆衬着簇新的家具。我和吴霞到时,吴云正在厨房忙着。客厅里的沙发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她们的大姐吴丹,另一个是她们的堂姐妹。吴丹离婚后最近再婚了,并在丈夫的老家湖南湘潭买了房。吴丹怀孕了。考虑到大龄孕妇的风险,吴丹决定从上海回到凤凰父母这里养胎。吴云做了一桌子的菜。她白了点,也胖了点,可能是不再出去做事的缘故。我们四个年龄相仿的妇女就着这一桌菜聊了个尽兴。
有“根”才有“翼”:家庭的新重要性
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在1948年发表了《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这一经典著作;半个世纪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人类学者刘新在2000年出版了《在他自己的影子下: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状况的一个民族志》。从“祖荫下”到“在他自己的影子下”的变化反映了在中国乡村的个体化的进程中,个体从完全活在祖辈的阴影下,到为自己而活,追求个体自由自治,反抗家庭的掌控。
然而,中国乡村的年轻人对于个体化进程的反应不是简单的自我放纵和摒弃家庭。在对中国乡村年轻人的工作、爱情和家庭观念的研究中,挪威奥斯陆大学中国研究学者Mette Hansen与其合作者Cuiming Pang通过对年轻的村民和农民工的访谈留意到他们强烈的个人责任意识和对家庭关系的看重。
家庭和亲属关系依旧是个体的安全网。通过所谓的“链式移民”(chain migration),吴海的一家一个接一个从吴村搬到凤凰古城。一方面,成年子女在他们离乡背井从传统的村落家族关系脱嵌而出后还能依赖父母家庭;另一方面,逐渐年迈的父母也能得到成年子女的照顾,特别是在生病的时候。吴海两口子与二女儿吴云暂住一起,不做事的吴云能照顾生病的吴海;怀孕的吴丹选择从上海回凤凰,因为这里有家人的照顾。
婚姻,在前工业社会中曾经是一种高度刻板的被安排的结合,如今已经转变为 (即使是在偏僻的山区)两个个体的自愿结合。正如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所说,当代婚姻中牵引两个伴侣的是他们对对方的感觉, 几乎完全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随着个体化进程,过去的二三十年来,伴侣双方对财产的共同持有的兴趣在不断消减。
三哥和小胡各自有自己经营的小生意,他俩在钱财方面分得很清。他们的亲密关系只体现在情感上,与经济无关。然而,他们的亲密关系为他们提供了一张安全网来缓冲他们本小利微的生意上的风险:小胡把她在村里中转车的生意让给三哥;三哥帮她在凤凰古城的铺子做木板架,并且每次在她那过夜时替她分担家务。小胡买三哥做的酒放在她的铺里卖。小胡从低廉的进价中受益,而三哥有小胡这样一个靠得住 的位于游客最多的沱江边的小商家来向他进货。
无论是在婚姻关系还是代际关系中,个体不再是为家庭的延续和需要而活。恰恰相反,是家庭为满足个体的需要而改变。借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者阎云翔的表述,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供给中心已经由祖辈转变为孙辈,即“家庭下行主义”(descending familism)的产生。当代家庭的现代化体现在个体处于家庭关系中的越来越重要的中心地位。
然而,这是“去个体主义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和亲属关系不是变得不重要,而是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成为个体抵御风险的最后堡垒。因而,作为个体,我们需要有“根”才有“翼”:在个体化的进程中,家庭纽带(是为“根”)一方面成全个体的流动 (是为“翼”),另一方面帮助个体应对他们远离家庭后遇到的风险和挑战。
(作者丰向红系美国东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副教授。文中村名和受访者名均为化名。作者借此感谢凤凰的朋友们多年来对其研究工作的支持。望大家平平安安,待疫情结束后再重聚。故土家国,叶落归根。)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