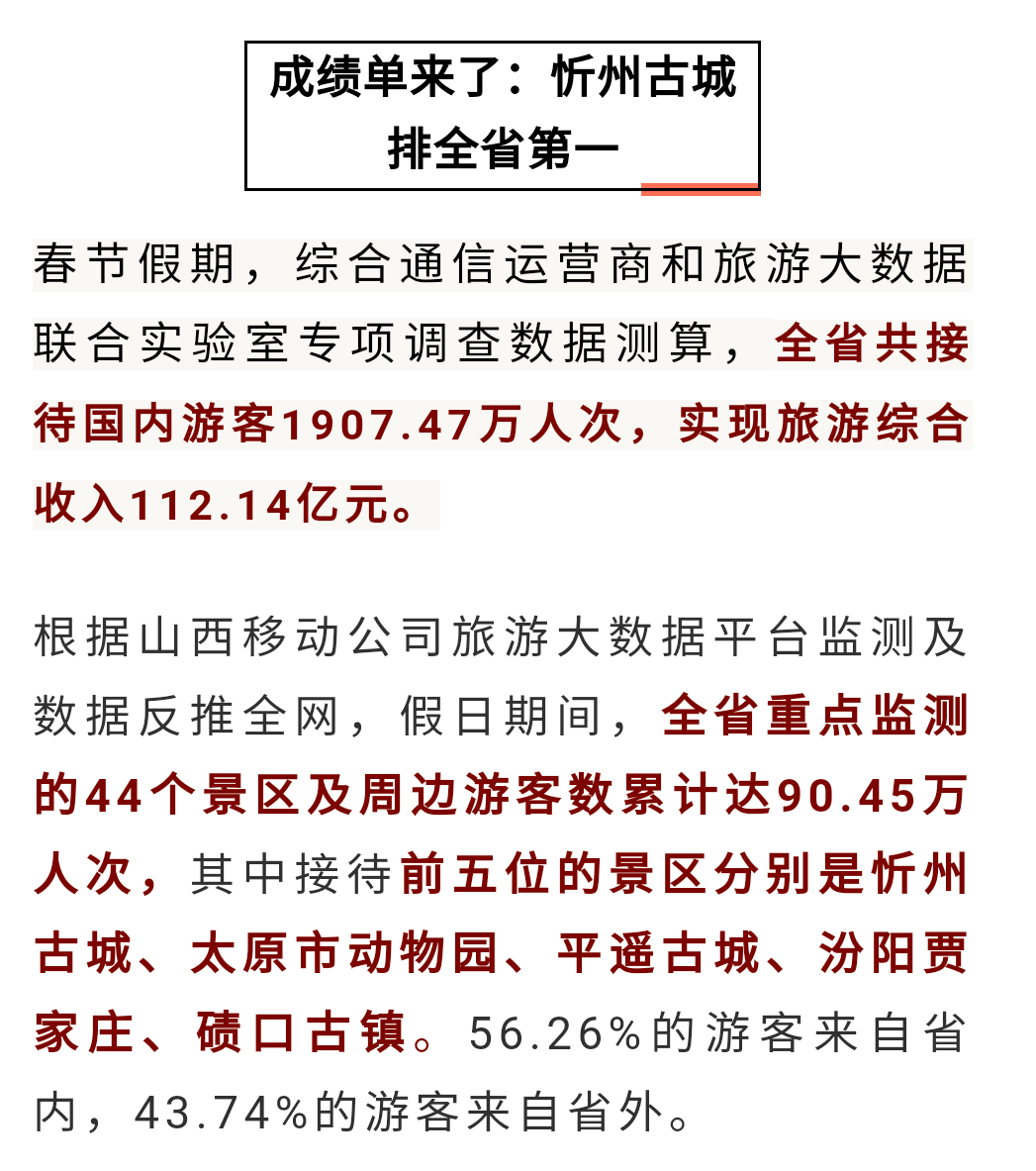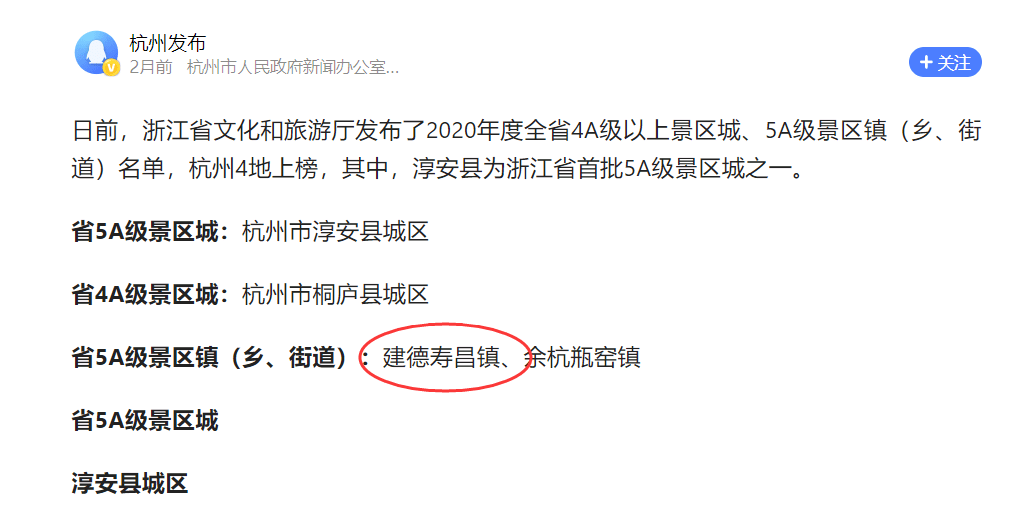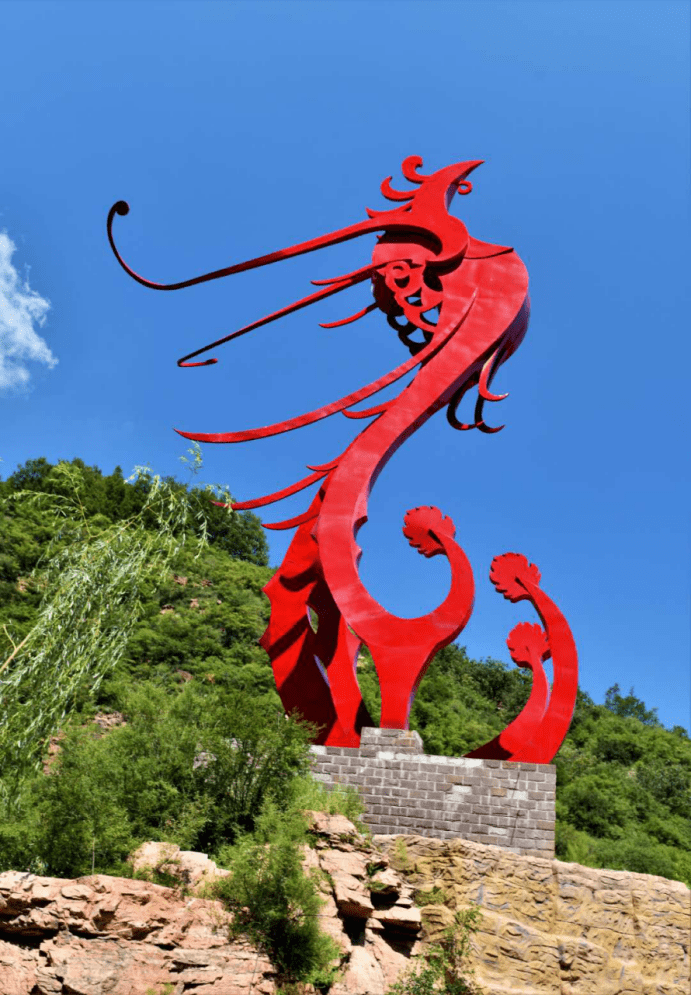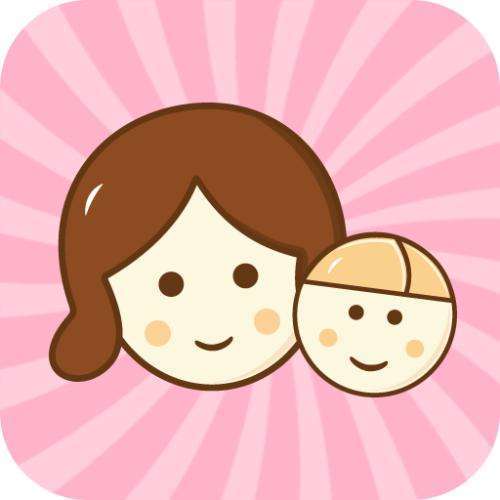人总是要去不同的地方,想去的,不想去的,想到的,想不到的。
在二中读书的时节,恭门,听起来很遥远的地方,过张川,隔着婉转千回的水,隔着冷冽高昂的梁。逃课去看其他中学运动会回来的男生们总会挥汗如雨,说张川的一中,说马关的四中,遗憾他们没去过的恭门三中。嘴边的杨梅雪糕,粉紫,颜色像极了二中校门内两排梧桐的花咕噜,每一口有每一口的软糯香甜,只吃了两次,就没有了,别的雪糕总没有了那粉紫的味道,虽然知道早没有了,却总抱有幻想。就像恭门,以后数年,去了多次,每一次的心底暗流涌动,澎湃,起伏,熟悉的不熟悉的砖瓦,熟悉的不熟悉的巷子,都是我的恭门,我的三中,却再也没有踏入的理由。
我反反复复站在木楼下,大门,门柱,年代久远,还原了木质本来的黄白色,镂空的花栏木窗,花枝柔美,花蕾欲绽,祥云绣集,随时可以雨声萧索数年月,随时可以绣针簌簌映红妆。那个淡蓝色上衣,青色裤子的女子,空荡的衣衫在恭门的十月更显单薄瘦弱,眼神空洞恓惶,脚底下堆放着被褥、锅碗瓢盆、绿色的煤油炉子,放学后蜂拥而出的学生们,和学生们张望打量的眼神。多年后,我总是清晰的记着这一幕,用烟雨木楼下的一个我去看三中门口守着锅碗瓢盆的另一个我。
九月,迁徙的月份。有人坐着绿皮火车奔赴远方寻梦,有人从马关,从龙山,从张川,从恭门,从西到东,从东到西,十五个乡镇穿插迁徙。避开母校复读,逃避是每个复读生50%的选项,人的一生中,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以一种怎样的身份踏上之前想也没想过的土地。木楼下,刚出锅的小花卷,麦香味卷上二楼镂空的牡丹花枝,对面的三中,左手呈直角修建的教学楼颜色嫣红,总有好奇的小家伙伸长脖子眨巴着眼睛望向校门口,右手的一排土坯瓦房是教师宿舍,经过前面的办公室,水房,教师灶,最后一排土坯瓦房就是高三的教室了,无论教师还是学生,穿着朴素,笑容真诚,无论是凤翔口音、付川口音、马鹿口音……都有一样的实诚与热情。
煤油炉子淡蓝色的火焰一点一点舔着小钢精锅底,怎么也揉不好的面像和了一滩稀泥,稀泥委屈地爬在放在炕沿的案板上,再加面试试,终于把一滩面连捏带拽揪进锅中,锅里已经分不清面片和面糊汤,放上盐,倒进醋,挖勺辣椒,在刺鼻的煤油味中,狼吞虎咽吃下一大搪瓷碗白面糊汤,真是难吃的要命。其实,从高考结束,好久没有好好吃饭了。渐渐的,我习惯了在煤油味充斥的房子中做饭、做题、,睡觉,从十月去等待下一个六月。
三中的冬天是个难耐的季节,老师的旧西服下,毛衣同样经了年成,颜色像教室右侧的土城墙,线衣的袖口磨开线,朴实的老师在自己逼仄的宿舍中打好面糊,乐呵呵地拿旧报纸粘好教室门窗的缝隙,粘好破玻璃,乐呵呵地怪你耍单衫穿得太单薄,乐呵呵地把学校分给自己的煤炭搬到教室填补。我就想起了我在二中时的物理老师张锦科,张老师从三中刚调到二中时教我们,几色混合颜色编织的毛衣,也是看着年代久远,同样显旧时颜色的西服,还是乐呵呵的样子,乐呵呵地上课,乐呵呵地讲题,在培训高中物理奥赛的那段时间,从下午放学到晚上十点,张老师拼了命地讲,我们尽力地学,奥赛的题实在难得离谱,我们每次想放弃时,再看看张老师疲惫中依然乐呵呵的一遍又一遍地讲解,告诫自己再坚持再坚持。三中的时节,不能想二中,想起二中,心痛。我最终迷失在自己选择的路途中,去撞撞不完的一堵堵南墙,把自己烧成灰烬。
滴水成冰的日子,没有火炉,没有热炕,和衣而卧,被子上加上棉衣,瑟缩一晚上,老话说冻得头疼,确实冻得头疼,到早起闹钟响,脸和鼻尖冰冷僵硬,晚上呼吸的气息在棉衣背部结了一层薄冰壳,提起来,除了袖子是柔软的,背部像洗过后挂在屋外冰冻的衣服,穿时“咔嚓嚓”响,从学校打的一壶开水在前一天下午做饭喝水时已用的差不多,砸半天砸开水桶的冰,控出一点水洗脸刷牙,背上书包提着空水壶赶到学校时,同学们已经陆续开始出教室跑操了,暗夜的黑还没有完全扯去,黑压压的操场,黑压压的队伍,显眼的只有麻老师崭新的白球鞋,青色的运动衣,黑色的无沿棉线帽,年轻的麻老师总是三中的一抹亮色,我们的语文老师。与麻老师崭新的白球鞋遥遥相望的是渐亮天色上闪亮的启明星。
恭门是乍寒微暖的,寒霜落草木的味道,你要问我这是什么味道,是麦草香和落叶衰败的味道,是生机和亡魂的味道,淡蓝色,不卑不亢,真诚可生存。要说恭门是一床薄被,那也是倾其所有来暖热你;要说恭门是一碗鸡蛋清汤,那也是必死之人的回生汤药;要说恭门是一个人,那也是以他命换你命的死士。
长期不回家,米米送来她从家带来的蒸馍馍、包子,带我去压麻辣条,带我认识新同学,带我去她租的房中教我做饭。腊月,周末学校没开水,同学在他租的房中的火炉上烧好开水,老远提来两壶。想吃饺子时,聚到同桌的租房中包顿素饺子解馋。晚自习后,七八个同学一起爬月光轻笼下的南山,看南山对面的学校和万家灯火。打打闹闹欢声笑语下,压抑所有的悲伤,覆上一层又一层的白纸,来暂掩冰冻的墨痕。
五月的一个星期天,煤油炉子怎么点火也点不着了,下在锅中的面泡成了糊糊,我满手煤油黑墨,修了一个中午,终于,我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大声痛哭,无所谓同院租住的学生们笑话不笑话,我克服了不会做饭,吃了一年没有菜的辣椒面拌白面片,寒彻的冬终于熬过去了,戴鸭舌帽捂口罩穿过流言蜚语,独自拔掉吊瓶的针头无视从针眼飚在地上的血,最终,面对这绿皮煤油炉子,重压下的线,总有奔溃的瞬间。我没去上晚自习,蒲来时,我刚哭完,或者是他等我哭完了进来。
“哭了?”
“没有。”
“煤油炉子坏了?”
“嗯。”
蒲查看一番,出门买了新灯芯,蹲在地上拔旧灯芯、穿新灯芯、换煤油。我靠在炕沿前看他摆弄,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就像我们坐了多半学期同桌,两人很少说话,却总有他默默地关心和理解,蒲是我第二学期的新同桌。
“煤油炉好了, 你中午没吃吧?赶紧吃去,别哭,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灯芯和煤油多少钱?我给你。”
“不要,我走了,早点来上晚自习。”
蒲穿的褐红色的西服,温文尔雅,写难懂寒痛的文字,笑容有阳光,举手投足有别样的气质。第二天,蒲叫我和同学一起去毛磨峡,看生病辍学的女同学,毛磨峡,漫山遍野的紫荆花,淡香拂面,时隔多年,依然如梦似幻。同学拿的相机一路拍照,已经24日了,一路的欢声笑语缓解了考前的烦躁,最终我们俩没有合影,合影预示着分离,分离最终还是会分离,静静地坐完剩下的半个学期,自此再没有见过,有些人,一别就是永远,是你不想要的永远。
说的有些悲情,确实,恭门是我的悲情,我是恭门的悲情。人看我是恭门的过客,其实,恭门之于我,以第二故乡而居,他的温情和实诚撑得起一个失魂落魄之人,一杯烈酒敬恭门,只是少了那对坐之人。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无论你心多不甘,留下的都是那旧时的颜色,旧时的恭门,旧时的三中,旧时的师生,我见过你的泪,落在我心里,温润成玉,够暖我,很多很多年。
□王志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