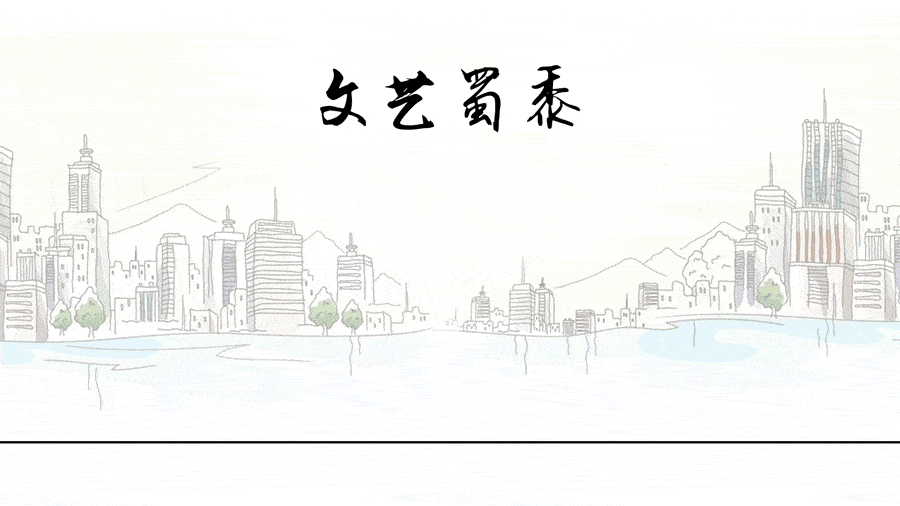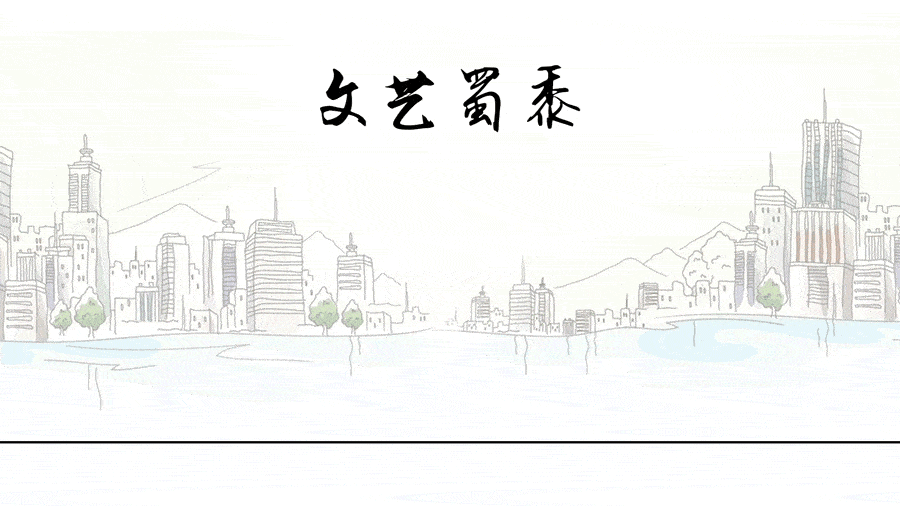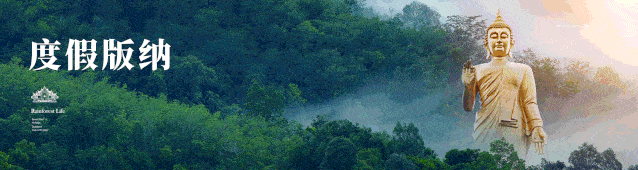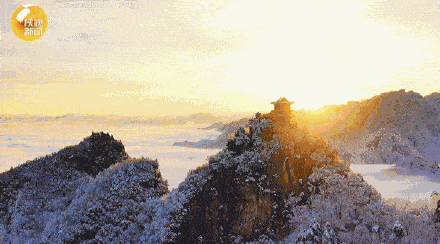—03
额尔古纳地处草原向山林过渡区,被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林区和额尔古纳河谷合围。这三者,都是得天独厚的好去处。三个得天独厚加在一起,哪个地方能消受这样的厚爱。
附近有个山坡,那里能看到亚洲最大的湿地。从高处看,有个地方像个马蹄印,人们说这是成吉思汗留下的马蹄印。
再往北走就到了莫尔道嘎。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这是岔路口一块牌子上的标语,也是这个地方推出的形象口号。其实,莫尔道嘎完全不用攀西双版纳这根枝。
它本身已经是个高枝。
莫尔道嘎的蒙语意思,是出发。当年,成吉思汗在这里一声莫尔道嘎,蒙古大军滚滚而下,铁蹄过处,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马背帝国。
我一直疑惑,成吉思汗起兵出发的地方,不应该是让人想归隐山林的莫尔道嘎,那里细腻静寂,适合普鲁斯特写《追忆似水年华》。大汗点燃狼烟之处,更应该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强光耀眼,大路坦荡,策马飞驰中,令人豪情陡生,血脉弩张。即使是猥琐之人,此时也能发出啸声。一代天骄,当然更会气贯丹田,势若长虹。可以想象,八百年前,铁木真弯弓射大雕,铁骑一泻千里,在历史中呼啸而过,何等彪悍。
对这一段历史的评说,自有公论。我只是觉得,在草原,不仅能感受自由,也能感受厚重,还有忧伤,还有悲壮。
千百年来,草原,拉开了多少历史大幕,上演了多少大剧。蒙古族“化铁出山”,驰骋千百年。突厥控弦四十万,东西万余里。霍去病铁骑猛封狼居胥,金戈狂扫焉支山。

多伦曾经是蒙古大汗国的上都,现在已是废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夕阳西下,废墟上全是黄草萋萋。有些石头做的指示牌,标明这里曾经是第六街,小东门,大安阁。
当年的人和事,都烟飞云散。
有旅游的女孩走过,对男友说,都是破土堆,有啥看的。
回来的路上,农历十七的月亮刚从草原上起来。从草原看过去,它显得更像月亮。当时那些马上的征战将士,看的也是这同一轮月亮。他们看它的心情,应该与我不一样。
我咀嚼那些边塞诗,口中都是风霜味道。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暮天沙漠漠,空碛马萧萧。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
车上,有人唱起《鸿雁》。
江水长,秋草黄。天苍茫,雁何往。
—04
我有个遗憾,我喜欢草原,也喜欢葡萄酒,不过,在令人醉意朦胧的草原上,总会觉得,这地方不适合葡萄酒。
这里适合摔跤、赛马、叼羊这些娱乐,适合烤全羊、手把肉、血肠这些食品,适合“宁城老窖”、“河套王”,“闷倒驴”、“套马杆”这些烈酒中的烈酒。
广袤的新疆有冬不拉,沧桑的黄土高原有秦腔,狂野的南美有巴萨诺瓦,高冷的北欧有后摇,粗犷的非洲有节奏极强的鼓,虽然这些地方的音乐都很独特,我也都能为它们配上合适的葡萄酒。
而在马头琴和长调里,能听到马群涉过河流,寒风从北方走来,草原在天边消失,它们是如此苍凉悲怆。葡萄酒可以厚重,可以忧伤,但似乎不适合苍凉和悲怆。
那天下午,路过一片草原中的白桦林。我独自走到林子深处,林间有很多野玫瑰。
林中有一片空地。我站在树下,闭上眼,风抚全身。
我站了很久,让全身细胞感受阳光和风。我发现,静下心来与自然接触,能听到一些过去听不到的声音,感受到过去一些没有的触感。
林子里很安静,似乎没有被惊扰过。也许,草原,山水,植物,岩石,都不爱说话,天生沉默,它们不像人那样需要表达。
也许,只有随着岁月流逝,沙漏到底,才可以真正放下红尘里的事务,在高山顶上看云起云散,在森林里拨开藤蔓,在没有路的草原上随意走,旁边有一群白的或者红色的马。
也许,那时我会更加懂得草原,为它找到那只属于它的葡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