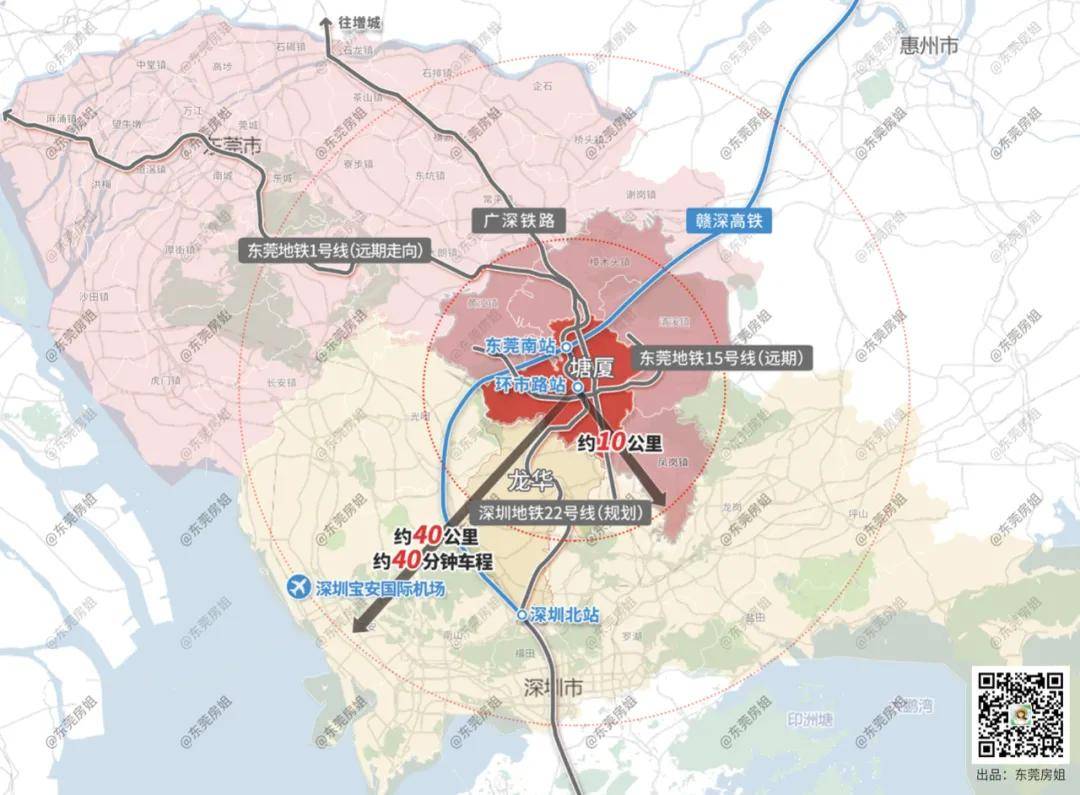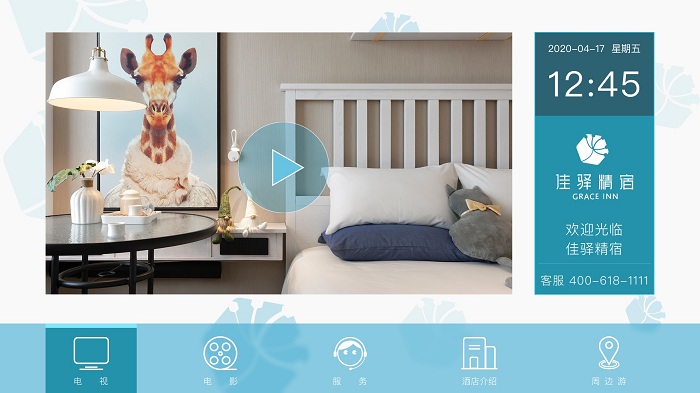从德国到伊朗,穿行东欧诸国之后,可以有两条路,一条经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另一条经乌克兰、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凯尔曼尼选择了后一条路

《沿坟墓而行:穿越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 [德]纳韦德·凯尔曼尼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旅行并不只是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在不同景点、路段构成的空间中移动,它常常也是在不同人群、文化、习俗之间的穿行,特别是在那些历史底蕴丰厚的地方,会让人心中涌出复杂深邃的时空交织感。也正是这种与自己所熟知事物的差异,可以为我们打开反思自身的机会,进而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何以如此。
几年前,德国作家纳韦德·凯尔曼尼历时54天,穿越东欧前往伊朗古都伊斯法罕——那也是他祖辈的故土。虽然他本人从小在西德富裕的环境下长大、接受良好教育,也早已融入主流社会,但这趟旅程对他而言,某种程度上既是重新认识那个被西方主流所遗忘的世界,也是重新认识自己。这本身就是旅行的意义:那些平时未能进入你视野的事物,将会迫使你思索那些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因而它既是指向过去的,又是指向未来的,始终透露出某种可能性。
耐人寻味的是,他选择的第一站是什未林——倒不是这座前东德土地上的城市有什么特殊的景致值得一看,而是因为近年来这里新兴的一个反移民党派“德国另类选择党”。即便两德统一已有长达一代人的时间,但有形的边界消失之后,无形的隔阂仍然存在,而所有经济、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最集中地体现在对移民的态度上:东德人更排斥外来者。仅仅对他们加以道德谴责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到实地去看看,才会发现,他们担心的其实是自己的养老金现在正被人拿走,“那些语句中流露的不是憎恨,而是恐惧,他们惧怕成为自己国度里的失败者”。
很多时候,人们彼此憎恨,并不是他们自己想象中的善恶对决,倒不如说是根深蒂固的误会——误会使得人们拒绝对话,而无法对话又进一步加剧误会。有时这甚至谈不上是刻意的,只不过是忽视和冷漠,即便在同一个国家之内都是如此:“在德国西部腹地出生长大的我们,眼睛总是看向法国、意大利、美国;就算是(中东意义的)东方,我们了解得都比我们自己国家的东部更多。”但这也不仅仅是德国这样经历了长久分裂的国度才会犯下的错,像伊朗,哪怕长期被西方封锁,地理上无疑也更靠近东欧,但讽刺的是,“东欧对伊朗人来说比巴黎、伦敦或者美国还要遥远”。因为人总是本能地更多留意那些占据自己视野中心的主流,我们中国人难道不也一样吗?
对德国人来说,“西方”才是更文明的,他们即便不能算作是“西欧”,至少也是“中欧”,总想着与那些“东欧”的邻居划清界限,德国的知识分子所思考的往往也是“是什么让自己国家与西方分隔开”。这种冲动其实与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很相像,只不过在欧洲由于边界本身就无法这样清晰地划定,因而带来了更为残酷的政治实践。但如果说德国已经多少接受了历史教训,在东欧所看到的却好像还在过去:波兰不仅竭力想摆脱自己的“东欧”标签,而且还在夸耀自己民族传统的同时坚定地拒斥移民,尽管它几乎没有移民进入。这说到底是一种“蹬梯”行为:在向上爬的同时,又蹬掉梯子,阻止更后面的人效仿。
这看似荒诞,但其实平常,在中国社会恐怕也会得到很多共鸣:“他们珍惜欧洲带给自己的富裕生活,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看不到这种多样性带来的积极方面,取而代之的都是些多样性只能制造冲突的各式新闻。”他们希望那个更好的世界对自己开放,也愿意拥抱它,但却不愿意向别人开放,因为他们其实惧怕社会的多元化所带来的身份认同混淆,也把市场上的机会看作是一场你赢我输的零和游戏。在经历了那么多战乱与苦难之后,人们所在意的,仍是一个内部整齐划一的民族共同体,抱着一种防御性的心态小心翼翼地看待外部世界。
在这一意义上,东欧仍然并未迈向未来,倒不如说它是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像敖德萨这样曾经充满包容、开放精神的世界主义大熔炉,早已随着两场世界大战(如果加上冷战则是三场)而消逝,取而代之的则是不同的群体在各自的旗帜下隔着有形无形的边界相互瞪视。但这并不可笑,应该说,这里的人们经受着西欧人无法理解的矛盾:他们既追随那个开放包容的欧洲理念,却又支持正在威胁、撕裂欧洲的民族主义,因为他们既要加入欧洲,又要捍卫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生怕邻居探过头来把自己吃干抹净。现实是:“融合”的大同梦想需要一个自由、安全、充满机遇的宽松环境,否则即便是那些进入了欧洲的移民,也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而反过来拒绝融入。
恰是在西方已感到陌生、难以索解的这些地方,才能在主流视野之外的历史与现实时空交错中,洞察到当下蕴藏的可能。那些波兰的、俄罗斯的、格鲁吉亚的年轻人,既塑造、捍卫着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整个的行为做派和对世界的了解又代表着自己所反对的全球化。这乍看是矛盾的,但其实却是落后地区共有的心态,即人们“想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因为那个可欲的更好未来既是机会,又是威胁,他们本能地想要好处兼得:既被接纳,又不至于失去自我,而如果不能被接纳,他们就将转身激烈地回归自我。
这并不仅仅是关于“他们”,也关乎“我们”,甚至涉及“欧洲”究竟意味着什么——更进一步说,“世界”到底应该是什么样,以及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说那些东欧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将欧洲看作一个精神世界,这个世界的本质恰恰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让不同的、本真的东西和平共处、互通、混合”,那么这早已不只是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倒不如说是一种理念,一个有待实现,也有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实际上,这很接近于未来的“大同世界”梦想。
有哪条路可以通往这个世界?历史上,法德之间也曾是世仇,但对现在这两国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仅仅是历史课上的一个概念了。当然那是经历了惨烈教训之后才得到的。不过,民族主义也并不必然只是狭隘地献身于自己所属的群体,进而将本民族置于他人之上,在近代历史上,它原本也曾是具有世界主义的底色,可以建立在多种文化之上,作为一种反对压迫的解放力量在社会上起作用。否则,一种狭隘、封闭的民族认同乃是双刃剑:它拥抱了自身,却拒绝了世界。
虽然书中讲到了很多惨痛的历史往事,这本书原作书名中的Gräben其实并不是指“坟墓”,而是“壕堑”,译者的误译是其对全书主旨的误解所致。因为它原本是隐指从东欧到伊斯法罕这一路上看到的种种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分断体制,无论是热战、冷战还是断层线战争,还远不像欧洲那样已消弭了内部边界、阻碍和对峙,边境线两边甚至同一个国家内部的深刻差异都到处可见,那不仅仅是族群、语言的不同,还是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和经历方面的差异。只有跨越这些分断的边界,才有交流、融合的可能,也才有未来。
这何尝只是东欧?反观东亚,其实也是一样,边界两边的坚冰也就刚开始融化没多少年,隔阂与误会仍然到处可见。在这个意义上,跨边界的旅行是可以打破边界、促成对话的一种努力,书中这句话可为题眼:“边界必须被打开,否则人们根本无法了解这些差异,也无法了解自己。”的确,在全球化陷入困局的当下,年轻一代的选择和行动将尤为关键,为了在这个拥挤的世界上更好地活下去,我们不仅需要对话,需要通过了解他人来了解自己,还需要一种最根本的想象力,想象一个可以因此变得更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