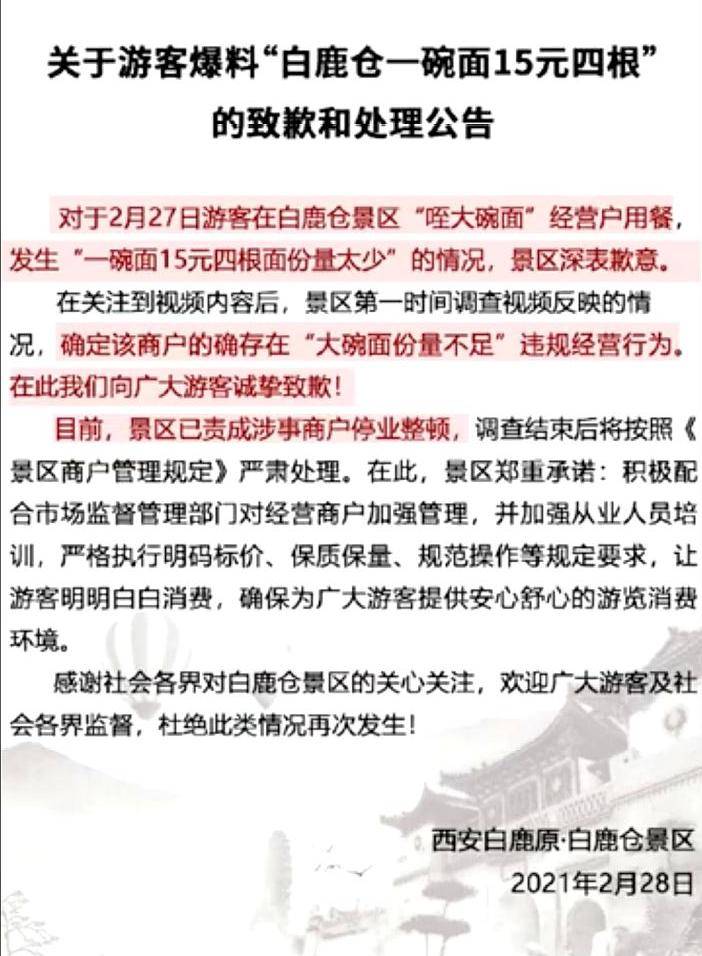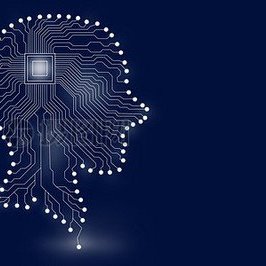朦胧的初恋
□袁斗成
川南一个叫丹林的小镇,狭长的青石板街道,两旁的茶馆一家挨一家。那是厚重乡土最平常、最热闹的一页。
我曾在故乡一带不下十个乡镇喝过盖碗茶。或许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也许是长期的耳濡目染,我只要上街,必定到茶馆坐一阵,在幽幽茶香里品味一份独特的人文情怀。
那年,由于偏科严重,英语和数学的总分还不及政治一科,即使我做梦都渴望跳出农门,高考名落孙山仍是意料中的事情。有“长舌妇”断言,我要是娶到老婆,她们“手板心煎鱼”。
我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老幺,个人婚姻问题成了母亲的心病。恰巧,母亲的干儿媳有一个亲妹妹,也正为待嫁犯愁。于是,嫂嫂自告奋勇当媒婆,约定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就在镇上的一家茶馆。
我和母亲早早在街头等候。嫂嫂领着那个叫阿宣的女孩和她母亲来了,一行人走进一家茶馆,挑了一个相对偏僻的位置坐下来,一人叫了一碗五毛钱的盖碗茶。
大家不时品一口各自面前的茶,淡淡清香里闲谈起来:家境怎样,田土多少,有几个兄弟姐妹。这些内容往往在此之前相互“访人户”就已经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了。
其实,相亲就是看看人怎么样,高矮胖瘦,脑壳机灵不。如果满意,男方就请双方亲戚摆几桌酒,打发女方的彩礼,就算定亲了。要是分歧过大,付了茶钱拍屁股走人,花费不了几个钱,从此再无瓜葛。
阿宣念高中时比我高一届,不过,她是在县城的两所中学念的书,毕业后在一所小学教书。据说,她的眼光高得很,好些小伙都被她拒绝了。
我一直怯怯地低着头,脸红得发烫,母亲和阿宣母亲以及嫂嫂到底说了什么,或许还没进我的左耳,右耳早就出了。后来与母亲步行回家,她才告诉我,相亲成功了,阿宣鬼使神差地一眼看上了我。
事实上,阿宣的确对我很好,主动约我玩了几次。可惜,我由于要到北方某部队服役,家里的经济条件差,就没按照阿宣母亲的意思举办定亲宴。当我千里迢迢到了部队服役,阿宣母亲固执地棒打鸳鸯,我们两人最终分道扬镳。听说阿宣一气之下到城里打工,几年都未回家过年。
初恋总是留下最美好、最纯粹、最深厚的记忆,即使是朦朦胧胧的。我至今还记得阿宣的模样:麻花长辫,圆圆的脸蛋,怯怯的眼神。
初恋仿佛是那缕茶香,始终烙在我的脑海里,穿过旧时光越来越清晰。
2014年底,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记忆乡愁”征文里,我的那篇《喝盖碗茶的岁月》获得一等奖,在《乡村夜话》节目里谈乡愁,我特地提到了那次相亲,心里悄悄掠过一丝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