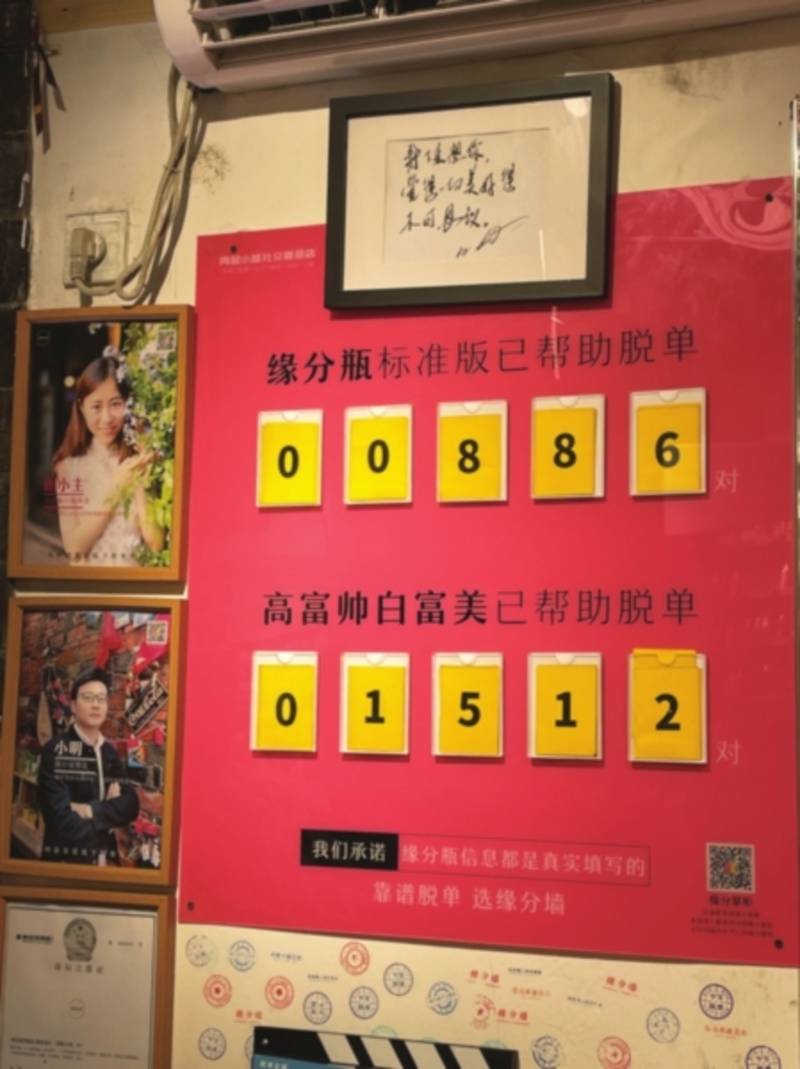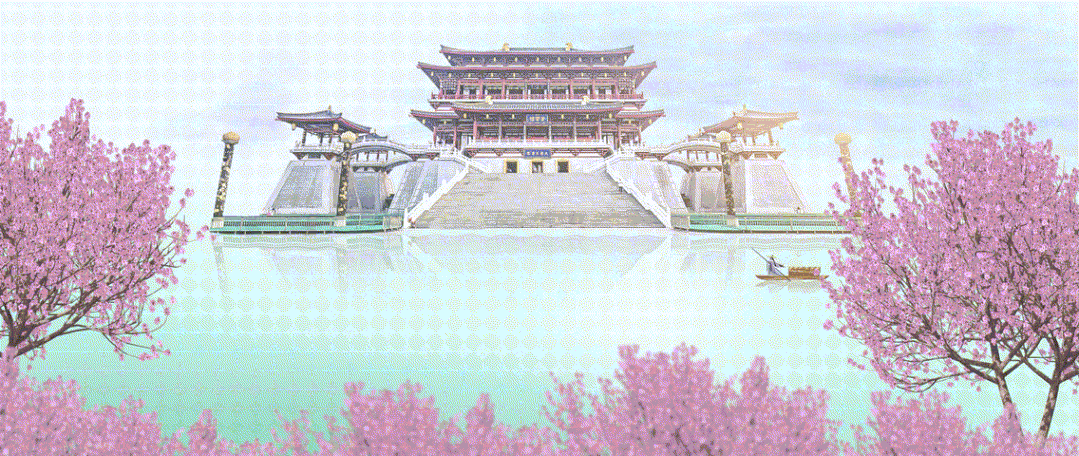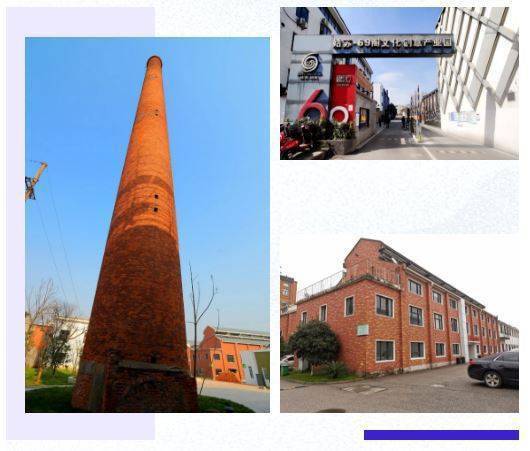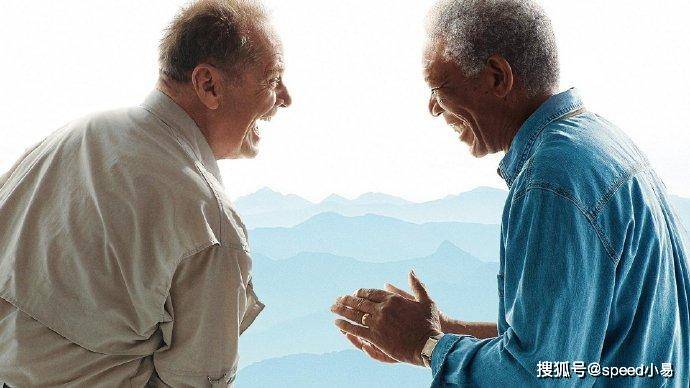摘自《丝路·皇会与天津妈祖》第八届妈祖文化旅游节论文集
另见《文学与文化》 2018年第4期《海洋中国:妈祖信仰的传播——以天津为中心考察》
by 侯杰 张鑫雅
摘要:妈祖信仰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人祈求航海平安的保护神。元代,天后信仰经过漕运传播至天津,在此扎根并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天津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天津,妈祖信仰非但没有衰落,反而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俗、文化广泛结合,对天津社会文化、日常生活以及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不仅是记录天津近代城市发展进程的重要载体,而且对妈祖信仰也格外关注,予以报道和评论。作为近代中国四大名报之一,《大公报》有关天后宫、皇会以及天妃、天后的诸多记载,已成为研究妈祖信仰在近代天津传布的重要史料。搜集、整理和发掘《大公报》中的相关史料,不仅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空间,而且有利于推动妈祖信仰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
关键词:妈祖信仰;皇会;天津;近代;《大公报》
妈祖是中国传统时代的著名海神。起初,妈祖只是一个地方性的神灵,受到民众的崇拜。后来因为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得到很多朝代统治者的青睐,并随着商人、船工、华侨等人口的流动,沿着江河湖海,向四面八方传播,甚至传布到海外。至今,妈祖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广大华人、华侨信奉的神灵。那么,她在近代天津又是如何传布的呢?具有哪些新的神职、神能呢?在近代报纸媒体中又是如何呈现的呢?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妈祖信仰在天津的传播
妈祖,又名“林氏女”、“神女”、“默娘”、“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等等。事实上,这些名称并非一时形成,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不断累积、增加,甚至离不开诸多朝代的帝王封赠。在中国传统时代,妇女无名是通例,妈祖也不例外。她是福建湄洲岛上一个林姓渔民的女儿,因此,人们一般都称之为“湄洲林氏女”。“妈祖”一词虽然出现得较晚,但却是人们对她的一种尊称,表达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她的无比崇重。此外,不同地区对妈祖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妈祖是福建、台湾及广东潮汕地区的习惯称谓,而天津、山东、辽东等地则习惯称为“娘娘”。而天妃、天后则与帝王对其封赠的名号有关,被打上时代的烙印。
妈祖信仰作为中国沿海地区的重要民间信仰,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有关妈祖的较早记载,是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四引述的《艮山顺济圣妃庙记》:“妃姓林,莆田人氏,素著灵异,立祠莆之圣堆……其妃之灵著,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船舶,其功甚大,民之疾苦,悉赖帡幪。”[1]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指出的那样:“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庙坛,久而愈进,文物遂繁。”[2]妈祖从渔村的一位巫女一跃而成为沿海地区的海神也经历了这一过程。妈祖作为中国乃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保护神,其神灵属性却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似乎是有这样一个变化趋势:“宋代的认识还没有超出神的范围;郑和时期形成了神道说;至明末清初则出现了《显圣录》所持之佛、道、神三位一体说;到清中晚期又恢复到神说;现代民间则多持道家说。”[3]无论如何发展、变化,就其本质而言,妈祖是从福建沿海地区的一位普通人家的俗女子,逐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沿海地区华人信仰的神灵,神职、神能也不断扩大。
自古以来,天津作为北方经济重镇,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内河航运和海上运输均极为发达,成为沟通南北运输的重要枢纽。当元朝统一中国后,定都大都,其所需官俸银两,军需粮草等均要从江南地区运来,仰仗于发达的漕运和海运。但水上长途运输风险极大,不仅船工们祈求妈祖降恩赐福,施展法力,保佑平安,就连朝廷、官员为了水上运输安全,也对妈祖极为尊崇。据《元史》之《英宗本纪》记载:“海漕粮到直沽……遣使礼海神。”[4]这一时期,元朝统治者对妈祖的加封则更显隆重,超过前代。由宋朝的“夫人”(1156年所封之“灵慧夫人”和“妃”1190年封为“灵慧妃”),升格为“天妃”即(1278年加封为“护国明著灵慧协正善庆显济天妃”)。据史料记载,由漕运改为海运之后,元朝统治者对妈祖的官方祭祀更加隆重。运粮之前,省臣漕臣必向天妃祷求平安,然后船只才能启航。粮船快到直沽的时候,又须祈求天妃。粮船平安到达,更要大肆酬谢天妃保佑之功。随着妈祖信仰的繁盛,天津曾拥有大大小小的祭祀场所16座,其中的两座大庙,一处在海河东岸大直沽,俗称“东庙”;一处在东门外的海河西岸,俗称“西庙”。西庙还为敕建,体现了元朝统治者借重民间信仰,稳定社会等意图。不论是大庙,还是小宫,也不论是统治者的意志,还是民众的信仰力量,都是为了隆重地供奉妈祖,满足各自相同或不同的神圣与世俗的各种需要。
明朝初年,漕运、海运并举。永乐帝即位后,天津的地名不仅得到确认,而且在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的地位也随着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得到进一步提升。为确保朝廷漕粮等物资供应,大运河被修浚,漕运日渐兴盛。妈祖虽然仍是承担漕运的河工们敬奉的神灵,但是其神职、神能开始悄然发生变化。由于天津人对妈祖十分热爱,所以也为妈祖信仰的繁荣、发展创造出新的机遇和可能,并形成地域特色。
清代,妈祖信仰出现显著变化。康雍乾时期,清王朝采取开放海禁、优惠商船税率等一系列措施,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天津社会、宗教、文化进一步繁荣。天津人对妈祖娘娘的信仰也从保护航海,扩展到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安宁、健康、婚姻、生育等社会习俗的诸多层面。最初为海神的妈祖在天津天后宫内,也化身为子孙娘娘,手抱小儿,身背口袋,袋内装满小孩。这些泥制的娃娃,成为来此求子的妇女们的目标。她们求子心切,在向妈祖供奉、磕头、许愿之后,偷取一个泥胎娃娃到家中供起来。如果以后得子,这个泥娃娃便被尊为大哥,自己生的小孩叫老二。久而久之,天津人养成“拴娃娃”的风俗习惯,即婚后无子的女性,为了求子,便去天后宫即娘娘宫烧香许愿,从那里偷偷地拴一个泥娃娃回家,作为自己的长子。如果生了孩子,要塑99个泥娃娃到天后宫还愿。对“娃娃大哥”,民众不仅要每天供应饮食,四季还得给他变换衣服。随着时间的延长,“娃娃哥”的年龄也在增加,于是人们要不断地去换一个年龄相当的娃娃,继续在家中供奉。随着岁增年高,泥娃娃也要由小换大,最后成为长胡子的娃娃大爷。[5]天津民众在接纳妈祖信仰的同时,还赋予其越来越多的职能,并使之分身为“子孙娘娘”、“癍疹娘娘”、“耳光娘娘”、“眼光娘娘”、“送生娘娘”、“千子娘娘”、“百子娘娘”、“乳母娘娘”、“引母娘娘”等,接受人们的敬仰和供奉。
由于妈祖主管了很多与女性相关的事务,所以到天后宫进香的女性信众也日益增多。天津女性民众进香,也有与其他地方不同之处。每逢大年三十的晚上,风尘女子多穿红衣进香。而良家妇女则要等到正月初一才能身着红衣入庙进香。传说妈祖诞辰为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各地民众从不同地方赶来参加庙会。他们不仅参与由社会各界人士共同举办的隆重庆典仪式,而且还成为妈祖出巡的主要观摩者、参加者。
场面宏大、精彩纷呈的庙会活动由于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嘉赏而有了“皇会”的美名,吸引众多民间团体——花会等前来迎神赛会,并衍生出大家共同遵守的祭拜流程。三月十六日“送驾”,即把妈祖送到娘家,十八日“接驾”,把妈祖从娘家接回娘娘宫。据传说,二十日和二十二日乃妈祖巡乡散福之日。在十七、十九、二十一这三天,分属不同花会的民众便涌到各个街巷去表演,俗称“踩街”。二十三日是妈祖诞辰,各道花会或齐集在娘娘宫内外,尽情表演,或在庙前戏楼演戏庆寿。各会均遵循多年来形成的序列,有条不紊地进行。前有门幡引导行进,后面是捷兽、龙灯、中幡、跨鼓、老重阁、拾不闲、鲜花会、西园法鼓、庆寿八仙、五虎扛箱、道众行香等会。各道花会一边走一边表演,敲打拉唱、吹耍斗趣,各自使出浑身解数,以博得沿途观众的喝彩。接着就是抬着“送生娘娘”、“癍疹娘娘”、“子孙娘娘”、“眼光娘娘”的4个宝辇,妈祖的华辇以及各种仪仗,井然有序地沿着“会道”行进。同时,善男信女则进庙烧香,祭拜妈祖,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直到二十四日凌晨,持续数日的庙会才告结束。[6]
近代,妈祖信仰与天津人的日常生活更加贴近,除神圣性不断加强外,亦保持世俗性特征。妈祖信仰所具有的经济、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世俗方面的力量与宗教、神灵崇拜所产生的神圣力量相得益彰。天后宫有大殿、后殿、中殿及十八处配殿。天后宫供奉的神灵以妈祖为主,但是其他的神灵也不少。在妈祖所处的大殿内,依然有眼光娘娘即眼光明目元君、子孙娘娘即子孙保生元君、耳光娘娘即耳光元君、癍疹娘娘即癍疹回生元君、千子娘娘即千子元君、引母娘娘即引母元君、乳母娘娘即乳母元君、百子娘娘即百子元君等。此外,还有王三奶奶、南海大士、曹公、马公、报事童子和马夫。在大殿后楼上供泰山娘娘、散行瘟疹童子、随胎送生变化、逐姓催生郎君、兼管乳食宫官、救急施药仙官、散行天花仙女、送浆哥哥、挠司大人以及白老太太。天后宫中大殿、配殿内所供奉的神灵有100余位。事实上,天后宫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浩浩荡荡的神仙队伍,许多配殿和神都是陆续增设的。当然增设的神都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关心的事情密不可分,如保佑子嗣,去病免灾,得财增福等,而这其中也就包含着人们多神崇拜的宗教情感。[7]
由于天后宫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娱乐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天津城市发展的中心区域之一,而皇会的不断举办,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包含商贸交易、文化娱乐、民俗信仰及旅游观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庙会。与此同时,报刊媒体作为受众极广的新闻媒体,每逢皇会举办期间,总会有大量的版面来宣传祭祀妈祖,特别是举办皇会的各项活动,在推动妈祖信仰的传播与发展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二、“皇会”与《大公报》的媒体呈现
妈祖信仰从宋代开始出现,元代传入天津,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其超凡神力得到诸多统治者的肯定,不断受到册封。如前所述,妈祖初封“夫人”,继为“妃”,后称“天妃”,再加封“天后”。在天津,人们普遍称天后为娘娘,并早已融入当地文化之中,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信仰。妈祖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发生了一些变异,不再局限于保护航海安全,更成为保护社会各界人士生产、生活的万能之神。皇会作为祭祀妈祖,表达信仰诉求的社会活动,在天津具有悠久的历史,形成文化传统,即使是在近代,仍然焕发生机,促进当地和周边地区之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与变化。报纸媒体的出现不仅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时局变化、国计民生等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使妈祖信仰以及皇会活动等更快速、便捷地传播开去,与妈祖信仰在天津的传播形成多重互动的关系。
《大公报》[8]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出版,由英敛之创办。作为记录天津城市发展历史、社会各界人士日常生活变化的重要载体,该报有关天后宫、皇会等关于妈祖信仰的大量记载,就为我们研究报纸媒体与妈祖信仰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毋庸置疑,透过官方的大力宣传,持续的褒扬,定期的祭祀,妈祖信仰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对民众的信仰习俗的养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不能否认,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有关妈祖的神话,有助于妈祖在天津社会各界人士的心中扎根,使之从保护航海神扩展到祈求子嗣,消灾祛病,百姓心目中不可缺少和须臾分离的精神主宰,乃致天津地方的保护神。因此,本为祭祀妈祖的皇会也被官府的介入,为官府所用。
皇会,最初为天津地方社会各界人士联合举办的祭祀妈祖的活动,因为官府的关注,也赋予皇会以另外的意义。1903年和1904年慈禧太后过生日的时候,要求天津官府仿照举办皇会时的各项经济政策,豁免厘捐,为慈禧太后诞辰庆典增添万民同乐,节日喜庆的气氛。对此,《大公报》多有记载。
在1903年11月9日推出的中外近事本埠栏“免厘续纪”中就写道:前纪皇太后万寿圣节期内前后,循照天后宫皇会之例,分别豁免厘捐一则。顷闻此节系由商务公所绅董禀请天津府沈太守,会同天津县唐大令代行,详由直督批行,海关道、天津道各宪会同厘捐局宪核办示遵[9]。11月27日,《大公报》在本埠栏“举办皇会”中进一步披露:“十月初十日恭逢皇太后万寿之期,商务公所绅董等藉此盛典,禀请举办皇会,豁减厘捐,以便疏通市面,业蒙直督批行,司道府县会同厘捐局核议等情形,均记前报。闻现已妥议详准,饬经该绅等邀集天后宫扫殿会首,及阖津四季水会会首等会议,照例举办皇会。奉宪谕,预于初九日起至十一日止,凡出入零星货物在三十两以内者,一律免厘。拟于初十日在天后宫列摆陈设,悬灯结彩,华辇黄轿出巡,并有法鼓、跨鼓、大乐、童子京秧歌等会”[10]。次日,则先后刊登新闻报道:“本日为皇太后万寿之期,邑侯唐大令预先谕行津邑城厢内外,居民铺户均悬挂龙旗一对,并在门首张灯结彩”[11];“昨报闻于本日下午三点钟出会,路行宫北,过榷署前铁桥,督署前铁桥,至督辕而返。走单街,估衣街,或走针市街,或走北门,西马路,进西门,出东门,由宫南进庙”[12],记述了天后巡游路线。
本来在这次皇会举办之前,天津官府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举办皇会,遥祝万寿盛典,并免厘金各则,均纪本报。闻所出者共二十一会,皆预先有谕,不准敛化钱文,扰累铺商。是日一切会中需费之项,皆由总理办会某某筹备,并奉由海关道唐观察饬行,府厅县拨发官款五百两,以充各会之需”。出乎意料的是,“是日出会之际,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居然太平歌舞”,似乎达到了“遥祝万寿盛典”的目的[13]。可是在11月30日,同样是《大公报》就报道了皇会中的种种不如人意之处:“街市观会人等拥挤不堪,东门外马路一马车之马忽被惊,跳跃,撞倒路旁立灯,将坐洋车一幼童头颅砸破,鲜血淋漓,后未知所终。此次看会人等,不但男子填街塞巷,而妇女亦混杂期间。”这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担心,报人借他人之口,道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其间有稍明时局者谓:‘看此次之会,不过为聊作纪念,以后我天津尚不知成若何景象也’。闻此次跨鼓等杂会,多蒙官场赏给洋银或十数元,或数十元不等”[14],一语道破天机。此时,主《大公报》笔政的英敛之素与反对光绪皇帝变法维新的慈禧太后不睦,其天主教徒的身份也使其对民间信仰形成自己的认知。[15]
为给慈禧太后过好70大寿,天津官府不管天后宫住持刘希彭心存顾忌,继续操办皇会。1904年11月10日,《大公报》在中外近事本埠栏中就刊发这则消息:“预纪恭贺万寿事”:皇太后七旬万寿圣节,阖城官商庆祝,已记前报。兹闻届期龙亭演戏一台,督署内妥备戏台两座,署后之操场摆设戏台一座,洋务局前一座,银元局前一座,均于是期演剧庆祝。兹约各学堂教习学生同往观看。纲总约集之皇会,亦属不少。其南头窑之法鼓等会,已然料理矣。督署并有电影戏一台,拟由新铁桥至老铁桥接设电灯,以照行人。阖郡各署及官所地方,均搭灯棚。沿马路各商所设之灯棚,约有数十座之多,想届时必有一番热闹也[16],可谓话中有话。11月17日,《大公报》在中外近事本埠栏中刊发消息“皇会出赛”,进一步披露:昨日皇太后万寿皇会奉上宪谕,于是日出赛一节,已记本报。是日该会进东门,出西门,皆兴高采烈。观会者亦纷纷如蚁,兼之,各处悬灯结彩,高揭龙旗,其情形颇为热闹[17]。对于此次皇会,当代学者做出比较深刻的阐释:1904年举办的皇会,是一次颇受政治侵扰的皇会。当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岁大寿,天津地方官府为庆祝“皇太后万寿圣节”,便借花献佛,将这次皇会变成了单纯给慈禧个人祝寿的活动。为了阿谀媚上,不仅将以往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之前出会的日期随意延后,改在十月——即与慈禧诞辰同月份举行,而且连名称也随意改变,称皇会为“皇太后万寿皇会”,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次皇会的性质,将以酬神(天后)为目的的活动,变成在酬神招幌下酬人(慈禧)的活动,导致本次皇会的政治色彩十分浓厚。一般的皇会行会路线一经确定,即不得随意变动。本次皇会的出巡路线有所调整,概因官府要求途中必须进出北洋大臣衙门的东、西辕门所致。[18]
由此可见,这两年的慈禧太后生日,都因颁行举办皇会时的各项经济政策或皇会主力——南头窑之法鼓等会的参加庆典,而显得与众不同。慈禧太后和天津官府的这些举措无非是要将以酬神(天后)为目的之祭祀、经贸活动,变成在酬神旗帜下酬人(慈禧太后)的活动,从根本上转移了皇会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太后和天津官府通过借用皇会之名、之实,丰富慈禧太后生日庆典活动,将政治统治与民间信仰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统治的稳定。
三、皇会与《大公报》的媒体呈现
那么,《大公报》又是如何报道近代天津举办的另外几次皇会的呢?
1907年5月4日,《大公报》在“皇会纪胜”中明确写道:是日“为天后宫行香之期,由前二日各会在街拜客者颇多,沿街高搭看棚,游人如织,至日更必热闹异常矣”[19],描写了皇会期间市井的繁荣。1907年举办皇会,缘于1903年诞生的天津商务总会。天津商会为振兴民族工商业,将目光瞄准天后宫,锁定皇会。为此,他们与天后宫一拍即合,借助皇会对商家和民众的影响力,推销劝工会,发展工商业,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皇会举办期间,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如关税减免,“庙捐减半”等。这对于商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推动各商家踊跃参加皇会。而此次皇会因劝工会的召开,会期得以延长,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妈祖信仰对社会各界人士的影响。
关于1908年举办的皇会,《大公报》记载虽然不多,仅有3月14日的“皇会出赛之预闻”[20]和21日的“皇会照章请会”[21]两则,但仍可以断定1908年皇会延续了1907年的许多做法,继续影响着天津经济社会的发展,满足着妈祖信仰者神圣与世俗的多种需要。同时,商家的利益也得到维护,实现双赢。
1915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国内、国际市场受到巨大冲击,发生深刻变化。为提振经济,天津商会根据1907年皇会与天津第一次劝工会同期举办,获得成功的经验,计划劝工会和传统皇会同时举行。因呈送公文复函需要时间,周转较慢,又遭到警察厅杨以德厅长的婉拒,筹办并不顺利。可是参与筹办的各界人士热情未减,继续磋商,想方设法促成此事。4月27日,天津商会召集工厂董事开会讨论举办劝工会一事,最终达成缓期举办皇会的协议,皇会“不得过旧历三月,商业劝工会定期一月,此次设摆国货均在天后宫内,皇会日期在劝工会中间,每早八点钟开厂售货,下午六点钟收摊。皇会圣驾出巡之期,停止销货一日。限定时日,分别男女游览。”[22]4月28日和29日,《大公报》对商董开会的情况及其结果进行了报道,并发布“两会同时并举”的消息。5月3日,再次发布“劝工会布告”,提倡两会并举,复请减税。5月18日,“研究所开会”再发“再请举办劝工会禀稿,其文大致须九月间开办,遂通过工商联名上书,以期畅销国货……”[23]此后再无相关消息,此次皇会举办的具体情况从此缺席。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持续进行,妈祖信仰也成为了破除迷信的代表。天津县教育会明确提出希望永远禁止迎神赛会[24],反映了民国初年天津乃至全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妈祖信仰尽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一片反对声中,1924年还是举办了皇会。
1924年,在筹办皇会期间,“虽经省教育会举代表谒请省长禁止,因已至期,无可挽回。”但在皇会举办期间,“警务处长杨以德以藉皇会活动市面,虽允众商所请然,以地方治安关系,已限制十六、十八两日之皇会,至晚以下午七时为止,不准逾时。”[25]此外,皇会还受到了教育界及知识阶级的极力反对。他们召开评议会,“请议永远禁止迎神赛会之提议,书□文,迎神赛会妨害公安,影响教育会,应设法呈请禁止,以防将来,”[26]并呈请省长严禁此种赛会之举。尽管如此,终因妈祖信仰在天津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所以《大公报》不仅披露“近日杨柳青镇又将有出会之举”,而且也记述了妈祖信仰在天津的传布情况:“本埠天后宫历年旧历年关,由十二月一日起,至正月二十日,为香火最盛之时期,善男信女大烧其香,一耍货摊大卖其钱,流氓大逛其庙,老道大发其财。今年宫南宫北一带,因警厅折退马路,该宫山门未能及时竣,于是该宫住持在山门遗址,雇用京彩手,搭起五座京式彩牌楼,以代山门,颇壮视瞻。闻今日即可竣事,故一般善男信女无不眉飞色舞,喜形于色云”,[27]呈现出一幅人流涌动、香火旺盛的景象。
1936年,天津市政府在越来越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为振兴百业、繁荣市场,在酬神的名义下,重新举行已经停办12年的皇会。对此,《大公报》等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为皇会的举办制造舆论。3月7日,《大公报》在第六版刊登题为“停办已久之皇会今岁将举办”的新闻通讯:“本市举办皇会之说,自经市商会,暨钱业,绸布纱业,呈请市府批准后,日来甚嚣尘上。按津俗三月娘娘庙出皇会之举,自逊清乾嘉以来,盛行逾百数十年,与四月城隍庙之鬼会,同为民间所乐道。当时迎神赛会,四乡八镇,皆来赶趁庙会,香火船来津者,河为之塞。庙会期内,凡由香火船上携带货物,概免捐税,以是市面繁荣,民生活跃。至各种赛会,如门旙,中旛,抬阁,节节高,狮子,高跷,秧歌,杠箱等等,名目繁多,统共不下五六十种。其后为五架宝辇,前随通纲全副灯銮驾。与会者,率多钱,盐,当商,富丽堂皇,竞尚奢华,以较量富贵。其时出皇会以讲究穿章为争竞,多备单夹棉及珍珠毛全套衣服,招摇过市。会期以三月十六为送驾,十八日为接驾,二十、二十二两日出巡。送驾自天后宫出发,至西头如意庵,沿途皆于巷口搭架看棚,为终年不出门之妇女解放时期[28]。自1852年如意庵发生火警,焚毙男女百余人后,嗣即逐年冷落,至清末二十年来,又因外患频仍而停办。1920年代曾一度重出皇会,惟已无复当年旧观,略具雏形而已,详细述说皇会在天津的发展、变迁,先期造势,吊足读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胃口。直至4月底,《大公报》仍在刊发有关皇会的漫画,以及与天后娘娘相关的神话传说。皇会在天津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皇会期间,与此相关的各种见闻都成为天津新闻媒体每日竞相报道的主要内容。《大公报》也不例外,不仅用大量的文字记述皇会的各项筹备活动,而且将各种营销广告塞满报章多个版面,唤回读者乃至市民的历史记忆,配合皇会的举行。在1936年3月至4月间,该报接连刊载“法鼓——皇会里的重器大众化的乐队”、“皇会忆旧录”、“皇会声中灵慈感旧记”等,为皇会造势。众多商家借着皇会的举办,妙用经营策略,千方百计推销自己的产品,竞逐广告版。如4月5日《大公报》上刊载了《天津游览志》附“皇会考”的广告云:“天津游览志一书,将津市之沿革、河流、交通、名胜,以及娱乐场所、工商各业,莫不详载无遗,并附皇会考及天津详图。在此皇会期间莅津游览者,固宜人手一编,即津门人士,亦当先睹为快也。原价五角,现售特价二角五分,北马路直隶书局发售。”[29]
三、结语
纵观妈祖信仰在近代天津的传布,与其具有的神圣与世俗的多种功能密不可分。也离不开《大公报》等报纸媒体持续不断地关注和连篇累牍的报道、评论所形成的舆论和社会影响力。这已然成为妈祖信仰在近代天津的传布,特别是皇会筹备组织以及举办的重要力量,推动着天津城市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妈祖信仰特别是皇会活动的主办,受到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制约,《大公报》等报纸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也不会是空穴来风,一定会不同程度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还受到报人们宗教、信仰、文化、观念等等制约。然而,这一切又何尝不是妈祖等民间信仰在近代天津,乃至中国社会传布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众所周知,妈祖信仰在天津早已深深植根于社会各界人士的心中。历经数百年的兴衰演变,妈祖信仰依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天津传播发展,直到今天仍深刻影响人们的观念和生活。在这过程中,有众多媒介发挥着各式各样的作用。《大公报》在近代天津妈祖信仰的传布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一定的价值。发掘《大公报》中的相关记述,研究妈祖信仰在近代天津的传布不仅有助于挖掘妈祖信仰的新内涵,而且有利于促进近代天津社会生活、信仰生活的研究,促进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今天,我们在此举办妈祖信仰论坛,也是妈祖信仰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大家不仅交流了海峡两岸、东南亚地区妈祖信仰及其传播情况等学术成果,而且对探讨中国传统信仰的现代发展规律有一定的作用,对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与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 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 杨强:《天妃信仰之属性及其他》,《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
[4]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
[5] 参见侯杰等:《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92页。
[6] 参见侯杰等:《民间信仰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135-136页。
[7] 参见侯杰等:《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8页。
[8] 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大公报>序》,阐明报纸取名“大公”的旨趣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10年,以敢于议论朝政,反对慈禧太后、袁世凯著称,成为引人瞩目的大型日报。1916年10月,由王致隆全面接收继续经营,聘请胡政之主笔政。1925年11月25日,《大公报》停刊。从1926年9月1日起,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接办,并在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著名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1937年7月抗战爆发,8月日军侵占天津,由于《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遂移至上海、汉口、重庆、香港等地出版,在国内舆论界很有影响力。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1日在天津复刊,后改名为《进步日报》。它与《申报》、《益世报》、《民国日报》一起,被称为近代中国“四大名报”。至今仍在香港出版,是出版时间最长的华文报纸。
[9]“免厘续纪”,《大公报》 1903年11月9日。
[10]“举办皇会”,《大公报》1903年11月27日。
[11] “张灯结彩”,《大公报》1903年11月28日。
[12] “皇会再纪”,《大公报》1903年11月28日。
[13] “官助会款”,《大公报》1903年11月29日。
[14] “皇会余闻”,《大公报》1903年11月30日。
[15] 详见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1-362页。
[16] “预纪恭贺万寿事” ,《大公报》1904年11月10日。
[17] “皇会出赛”,《大公报》1904年11月17日。
[18] 方广岭:《环渤海地区妈祖史料辑解》,出版社第?页。
[19] “皇会纪胜”,《大公报》1907年5月4日。
[20] 《大公报》1908年3月14日“皇会出赛之预闻”:“闻天后宫皇会订定于二十二日茶会,其赛会日期均经妥定,仍于三月十六日将偶像送至吕祖堂供奉。是日出庙仍进旧城之东门西行,于十八日送还,绕针市街、估衣街及宫北大街入庙。二十日出庙游行,进旧城之北门南行,经闸口南斜街回庙。二十二日复为游行,由东门入西行,越双庙、铃铛阁、针市各街回庙。二十三日祝寿云。”
[21] 《大公报》1908年3月21日“皇会照章请会”:“前纪天后宫皇会照旧出赛一则,闻日前经会首等已缮帖照章请会,以便届期巡行。”
[22] “两会同时并举”,《大公报》1915年4月29日。
[23] “研究所开会”,《大公报》1915年5月18日。
[24] “迎神赛会将永久禁止欤”,《大公报》1924年4月28日。
[25] “皇会未了又鬼会”,《大公报》1924年4月19日。
[26] “迎神赛会将永久禁止欤”,《大公报》1924年4月28日。
[27] “天后宫旧年景之大点缀”,《大公报》1924年1月30日。
[28] “停办已久之皇会今岁将举办”,《大公报》1936年3月7日。
[29] 《天津游览志》附“皇会考”的广告,《大公报》1936年4月5日。
by 侯杰 张鑫雅 摘自《文学与文化》《丝路皇会与天津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