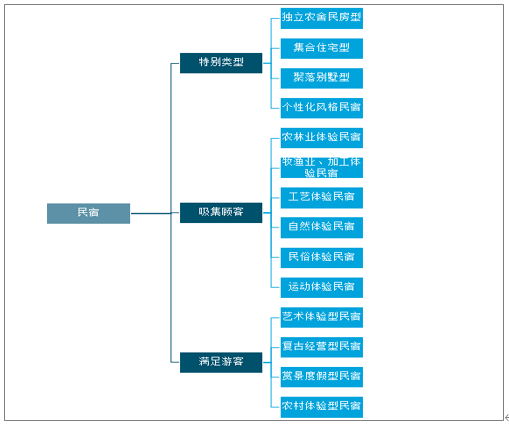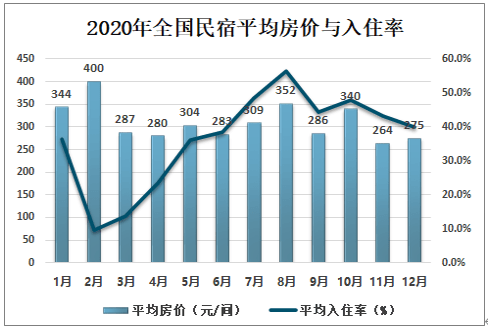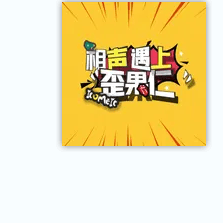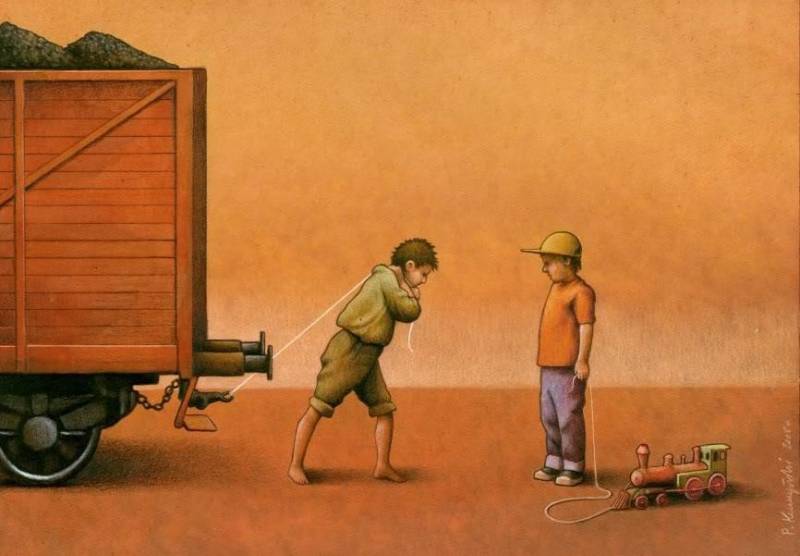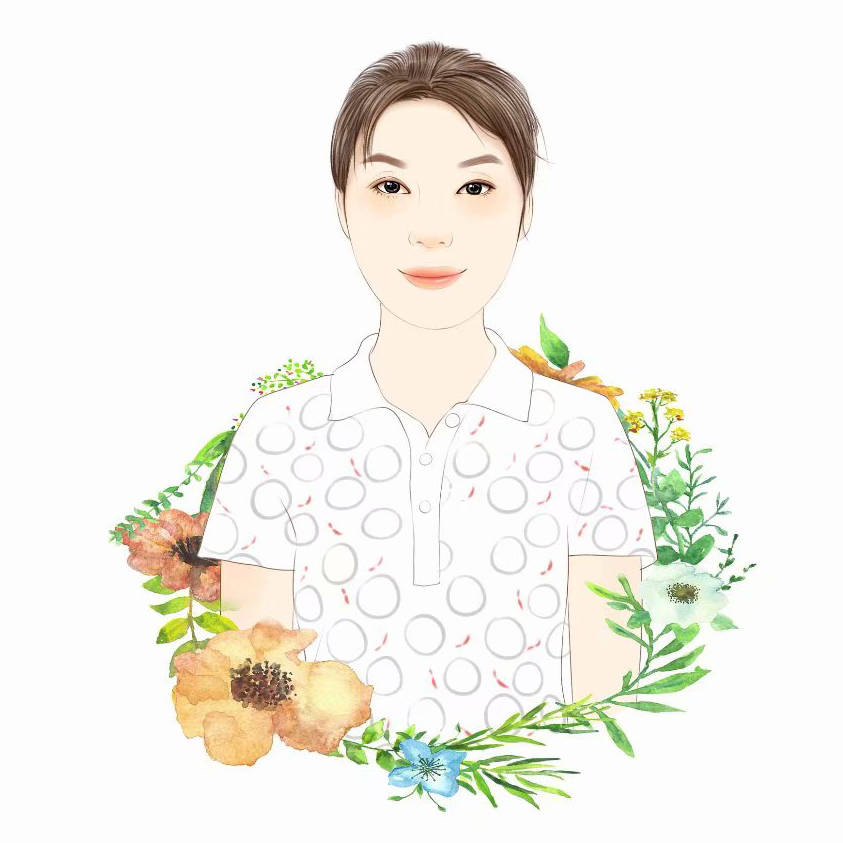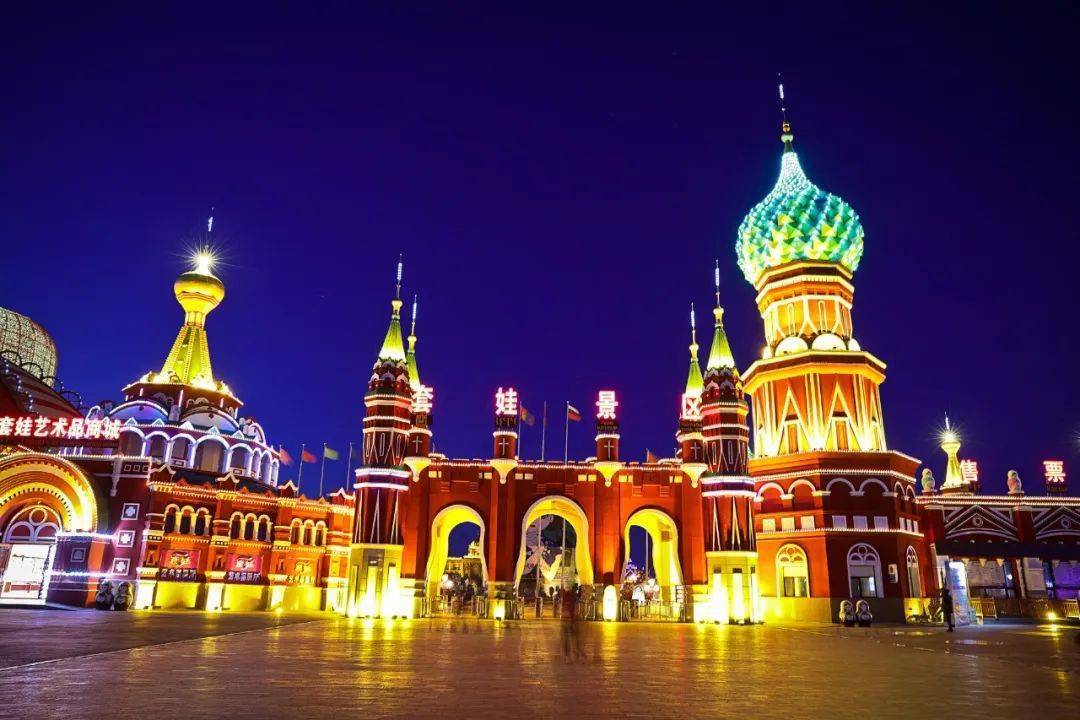如果没有去长岭岗,看云起雾涌,我可能不会对“波谲云诡”四个字,有这么形象的理解。
凌晨5点半,我和羊青出门,窗外还是黑暗一片,除了偶尔“簌簌”驶过的车,街上寂静一片。羊青问我:“我们这里的日出,是不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夕阳?”我说“是!”

朝阳初升,云海弥漫到无限远的天际
云,可能是这世间最善变换的物质了。它并没有特定的形状:在天上,它可能成片;也会独立一朵;有时候连缀起来,把整个天包裹起来,那就不是云,成了抽象的阴沉沉。云在蓝天里独立成朵的时候,消涨聚散,各种形状后,最后都被吸进蓝天里。天上的云是天上的云,我现在要说的,是“长岭看云”。
长岭岗在六枝县城的西南面,出城40里。黎明,开车,车灯在弯曲的公路上直直地指向前方,不管左转右转,它一直坚定地指向前方。透过车的左窗,远处起伏的山梁线上,已经有隐隐的鱼肚白,那其实是淡粉色的天光。我指给羊青看,以为他摇晃中睡着了,其实没有。

沟谷间民居错落,山民生活在云雾之中
2019年的夏天,偶然路过长岭岗。雨后,乍晴,天边的云彩被忽然出来的太阳,镀上金色的边;而近处,在高高的长岭岗上,我们看到的,是雨后蒸腾而起的、氤氲在山间谷地的、白而黏稠的云雾。一眼看去,那些云雾弥漫消散,牛奶泄地一样,荡漾到远方。
看云,有很多好的去处,但都太远。我以前并不知道,离我这么近,驱尺20分钟,只要时机得当,我就可以看到美丽的云海。所以我要常常跑,看天,看时间,之前是,现在也是……

观景台上,可以平视远近的云海
夜晚来临,天地间随着热流跑了一天的水汽,慢慢凝结,抱团,继而下沉。山间,林地,谷壑,旷野,它们挂在草叶上,附在枝柯间,结在润土里。然后就睡着了。
我和羊青到长岭岗的时候,天已麻灰了。在我们到来之前,那些沉睡的水汽,仿佛被微微的天光叫醒,在谷底,白盐浓霜一样静静地,等着太阳翻山越岭带来的温暖,给它们热闹的激荡。

群山如牧,奔涌到天边,一直到远处波澜壮阔的牂牁江
开始,那些云雾,只是沿着低处的山谷,慢慢流淌发散,淹没沟谷里的山居,绿树,田野,小路。但这时,太阳出来了,从身后的无数并列的驼峰山梁上升起来。温度上升,气流慢慢流转激扬起来,山谷里的云雾慢慢往远近各处的山腰上爬,它们抚摸过低处的楸树,翻过一道道的梯田,蒙上民居的窗门,很快,翻过那些低处的山梁,连成一片。从高处的观景台看下去,云涌成海,翻卷拍岸。脚下到天边,一点点孤立的,一条条成线的,那些山头和山梁都浮在海里。眼前有海,有风声呼呼,有鸟鸣布谷,但并没有惊涛拍岸的声音。
云海翻涌,让风有了具体的形状,目力所及,群山如牧,而风,是那只翻覆的巨手。人俯瞰着云海,仿佛忽然就伟大起来,高高在上的样子。其实不管是从下,还是从上,你并不比一棵杂树伟岸,也不见得比一丛野草显眼。云海的激荡,在你短短经过的一瞬,并不显现。

山脉呈纵向排列,山间的沟壑,云雾弥漫
可是,我还是被云海吸引,来了,想:人为什么会感慨人间仙境啊?云雾把低处的尘世蒙蔽,每个山头被孤立起来,悬在云海上,看上去彼此不能交通。它们之间,踩踏的泥泞,交接的道路,倏忽之间被抹去了。光辉满天的时候,山下的小路,才是通向坦途的指向。
那些云雾,从清早的丝丝缕缕,连缀为团,奔涌成片,给你看金色阳光乍现时,短短的人间蜃景。蜃景从巨兽的呼吸里肇生出来,倒映人的一切美好妄念。可蜃景还是要看,因为什么?因为土地上的生活、门窗、田畴,和抬眼看见的楸树花,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想,如果有可能,我愿住在“半山寺”里,上去可看云海,下来能观凡俗。

远近高低的山头,如漂浮在云海之中
春夏相交之际,夏秋承接之时,晴天的早晨,或者骤雨放晴,如果有时间,我还会跑去长岭岗,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站在观景台上,看云,或者不看。看,就看它翻涌;不看,我就独自激荡。那些暗涌潮动的波谲云诡,是尘世俗常的激扬点缀,淡看,不在其中。羊青,远处那些云雾里的山脊,等云雾很快散去,只要你肯开上你心爱的小车,不过须臾,就能够到达。

云海和天际没有界限
文/王飞
刊头设计/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文字编辑/邱奕
视觉/实习生 卢钱沙
编审/李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