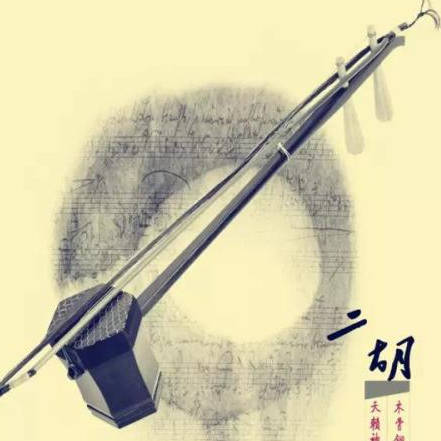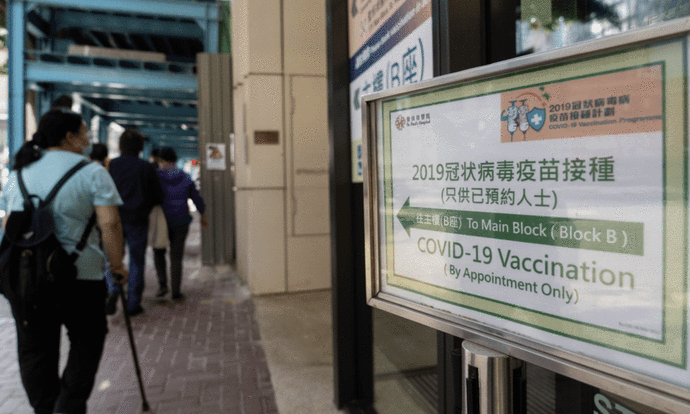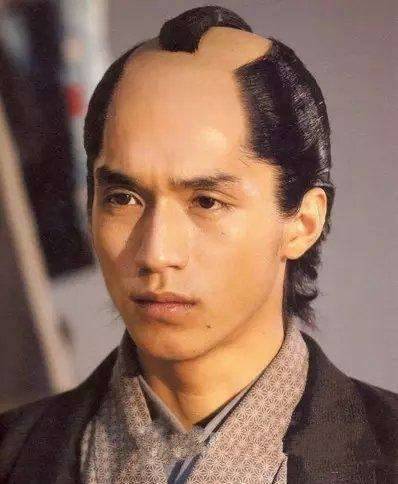大约没有人会比温弗里德·塞巴尔德更懂得旅行的意义了。他的旅行可以是过去的,也可以是当下的;可以是文学的,也可以是现实的;甚至,它从未真正发生,只是一种美妙的想象。但无论如何,塞巴尔德的旅行都有一个事先确定的路线。他从未走远,更无意离开,总是从他喜欢的书本中选取相似的场景,展开一次文学意义上的远行。换言之,他有多么热爱阅读,就有多么热爱旅行。仿佛小说不是别的,正是搭建在阅读与旅行之间的桥梁,把原本迥然不同的两种事物,牢牢地连接在一起。
《眩晕》即是如此。塞巴尔德打破了时间的边界,把过去与当下、现实与想象杂糅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行程。小说由四个不同的片段组成,每一个片段就是一次独立的旅行,合在一起则是对经典文本的致敬。《贝尔,或爱之奇异事实》写的是司汤达。1836年,他53岁,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无限追忆中。1800年,他17岁,名叫亨利·贝尔,跟随拿破仑的大军一道穿越大圣伯纳德山口。此时,年轻的他从未想过要将写作当成毕生的志业,更不会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一场怎样的恶战。
只是,塞巴尔德并没有细致入微地描述这场大战,有关战争的一切,都像蜻蜓点水一样轻轻拂过,没有留下太多痕迹。他很清楚,记忆从来不是牢不可破的。直到多年以后,曾经鲜活的一切都成了黑白照片上的光影,我们才会懂得,原来记忆说到底就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眩晕”。36年后,司汤达重返17岁时的战场,终于明白眼前的一切并不真实——在他看来,记忆就像叠床架屋。我们看着房屋一层一层地盖了上去,却不知道记忆也完成了它的更替:新的记忆覆盖了旧的记忆,新的印象取代了旧的印象。
好比画画。尽管画师一再声称自己画的是如假包换的现实,但在明眼人看来,“一切总是迥然不同”,就像安哲罗普洛斯镜头里的“雾中风景”。的确,一切总是迥然不同的,包括现实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忆。似乎要与《贝尔,或爱之奇异事实》形成巧妙的呼应,塞巴尔德很快就开启了另一次旅行。而这一次,他要效仿的是卡夫卡。《海外》里有两次旅行。前一次发生在1980年,后一次则是7年后。一开始,“我”离开居住了将近25年的英国,独自来到维也纳,之后顺路去了威尼斯。但不管“我”到了哪里,“我”的旅行仍然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令人“眩晕”的。
比如“我”在大街上一眼认出了诗人但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明显比其他行人高出许多,但完全不被注意的他离我只有几步之遥,头上戴着熟悉的防风帽,然而当我加快脚步想要赶上他时,他拐进了海因里希街,待我追到拐角处时,他已经不见了”。但这又能代表什么呢?套用塞巴尔德的话来形容,所有的一切(包括他作品中提到的很多次旅行)都是“与过去的不期而遇”。《归乡》中,1987年“我”回到了阔别数十年的家乡,在儿时的小镇寻找过去的痕迹,却没料到往日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而“我”呢,就像卡夫卡小说《猎人格拉胡斯》里的人物一样,注定要“在尘世的河流上无休无止地航行”,与过去的一切不期而遇,却又辨认不出曾经有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