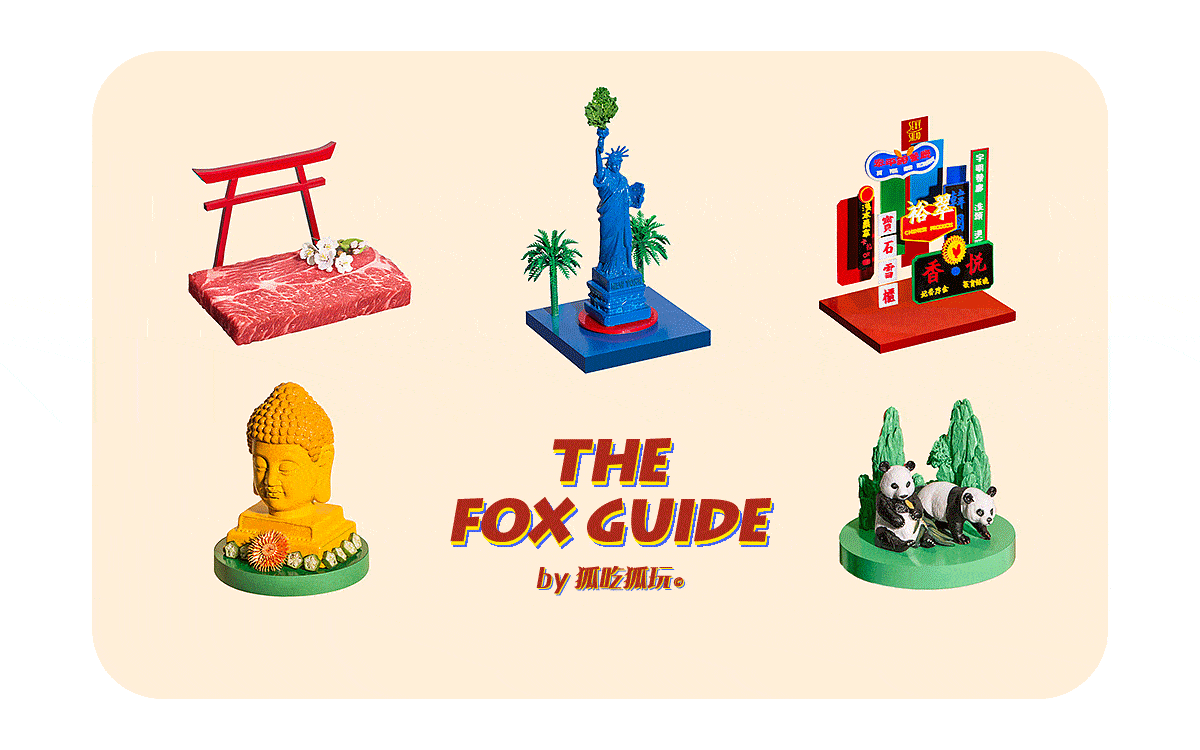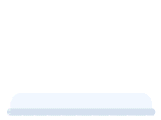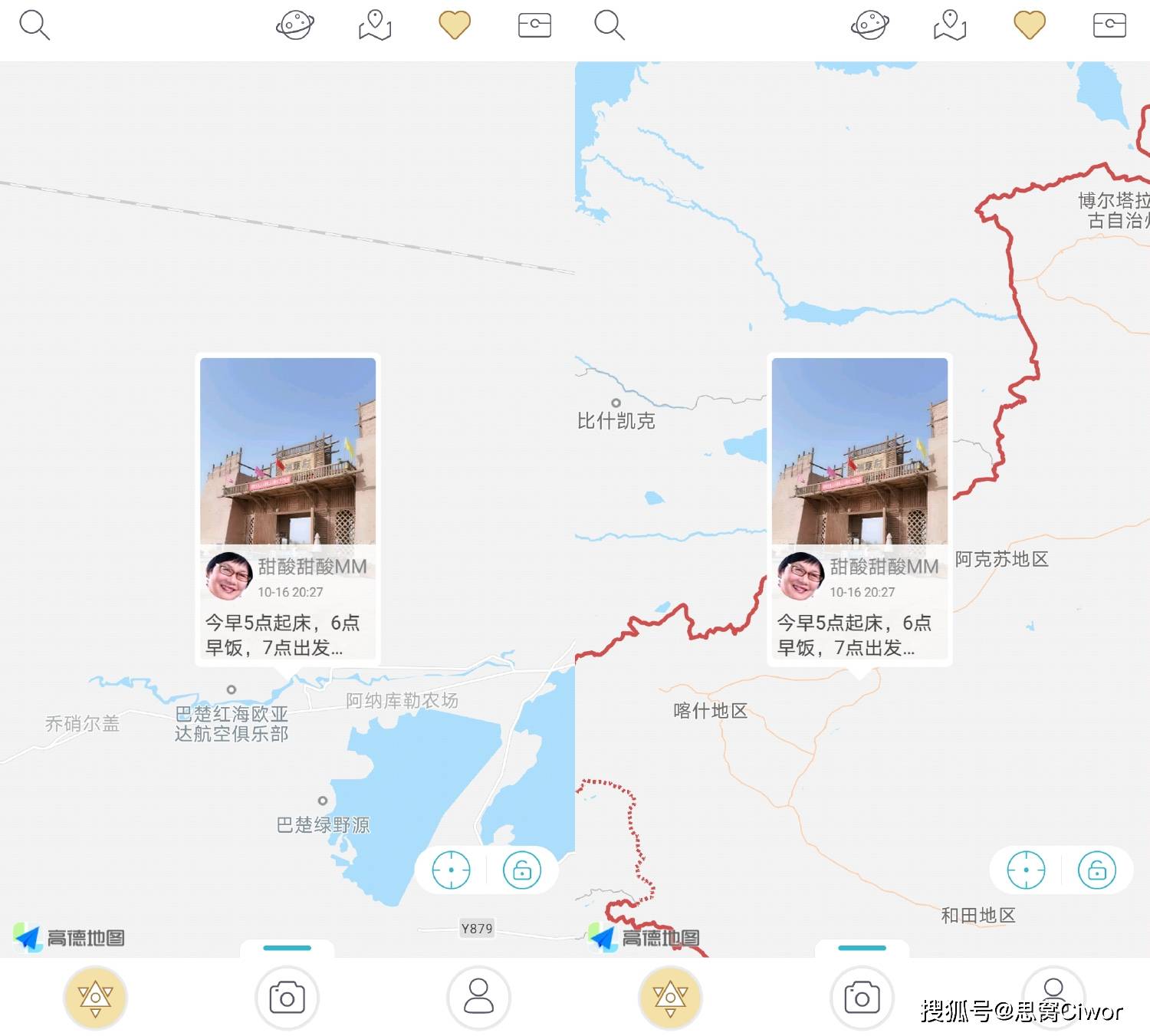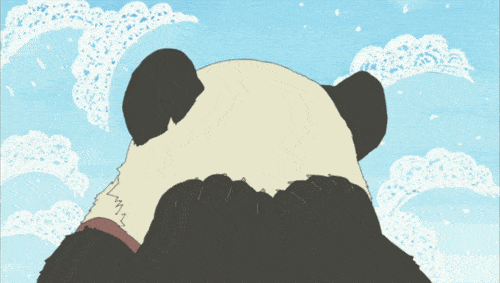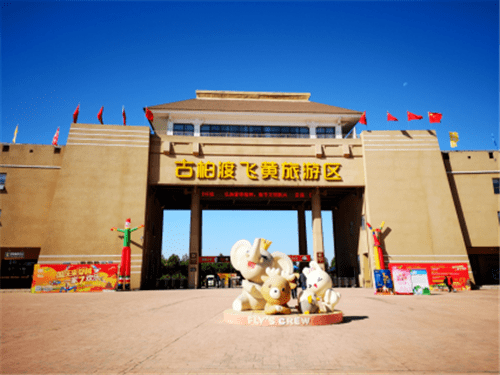江南馆街街坊遗址为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位于成都市江南馆街北侧,东为大慈寺片区、西与红星路相邻,北为蜀都大道,面积约50000平方米。勘探工作从2007年10月26日开始,勘探揭露面积1300平方米,唐、宋堆积最为丰富,发掘面积共4800平方米。共发掘唐、宋时期大小排水渠16条、铺砖面路4条、泥土支路4条、房址22处,明、清时期道路1条、房址8座、井3口。唐宋时期主次街道、房址和与其配套的地下排水系统是本次发掘的重大发现。成都在唐代经济十分发达,誉称“扬一益二”,在宋代诞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无不昭示成都在唐宋时期中国经济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遗址是繁荣发达的唐宋成都城重要的实物见证。遗址发现纵横交错长达数十余米的铺砖街道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在现代化都市中心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独一无二。
遗址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层,分布较均匀。第1层,近现代文化层。第2层为明、清时期堆积。第3层为南宋晚期-元时期地层。第4层为南宋中晚期堆积,L2、L3、L5等道路遗迹叠压于此层下。第5层为唐末-北宋时期地层。第6层为东汉时期地层。第7层文化遗物少,为西汉时期地层。第7层下无文化遗物。由于原址保护的需要,现揭露大部分停于第5层层表,发掘区的东部小部分揭露到生土。
遗迹现象多露头第4层下,由于原址保护的需要,只揭露出发掘区东、西部6层层表遗迹,重要遗迹有房址4处,土路4条(位于L2、L3、L5和L9下、只作了解剖,未揭露),水道3条。5层层表遗迹全面揭露,重要遗迹有铺砖街道4条,土面支路4条,房址21间(套),大小排水道16条。
铺砖街道4条(L2、L3、L5、L9),其中L2、L9呈南北走向,两路基本平行,相距约50米。L3、L5呈东西走向,与L2垂直交叉连接形成十字街口。支路4条(L4、L6、L7、L8),L4、L6分布于铺砖主道L2两侧,与L2直交,L7、L8为L3转弯处的两条分道。
L2为铺砖主街道,方向北偏东31°,宽2.1—2.3米,揭露长度约220米,其中仅南部长约53米保存较好。路面使用特制的细长条形砖竖砌而成,有“人字形”和“回字形”两种砌法。路面中间略高于两侧,路面有明显的车轮碾压痕和使用损坏后的修补痕迹。L2北段西侧F13与F17之间为支路L4,南段东侧F11与F18之间为支路L6,两条东西向支路距东西向的铺砖主路L5均约14米左右。
与街道、房址相配套的大小排水道16条,其中G2、G8、G9和G11为地下排水道的主道。G2起源处东与G11连接,北与G8连接,南与G9连接,除G11底部高于G2底0.5米外,G8与G9底部与G2同高,形成十字形地下排水管网。G11由东向西排水,G8由由北向南排水,G9由南向北排水,三条水道的水汇集于G2东部源头的方形水池后由东向西排水。其它的水道均为房址周边或与房址小天井连接的小水道,或道路两侧的排水道等。
G2为主水道,位于发掘区西部,为砖砌地下排水道,券顶,东西走向。G2方向与L2垂直,东部起源处距L2约13米;与L3西段平行,位于L3西段北侧,长度约45米,内宽0.5-1.02米,内高1.1-1.3米,由东向西渐宽渐低。水道东起源处为方形池,东西长0.9米、南北宽0.8米,深0.7米,北、东、南分别与G8、G9的G11相连接。
揭露唐宋时期的房址21间(套),主要分布在路两侧。L2东侧由南向北为F20、F11、F18、F19、F12,西侧由南向北为F14、F10、F16、F2、F13、F17;L3南侧为F24;L5北侧的F21,南侧的F31。F22、F23、F26-F28位于L2东侧临街房后。各房址大小不一,有单间或套间,不成院落,均面向街道开门,房址与街道之间的空隙处宽窄不一,均铺砖,每间房铺成不同的纹样。房址修建方式基本相同,用纯净的浅黄色土为室内垫土,部分房屋有平铺的砖面;竖砌一或两层砖为墙基,墙体应多为木或竹,立柱处下垫红砂石柱础。
遗址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遗物,主要为瓷器,以本地的青羊宫窑、邛窑的产品为主,也有龙泉窑、定窑等外地产品,其外来品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多于成都其他同时期的遗址,器形以一般生活用具碗、盘、盏等为主,出现较多贵重的外来瓷器可能也与这一区域较繁华有一定的关系。此外,遗址还出土了与佛教寺院相关的唐代晚期的佛教造像头部和一些佛经石刻的残片等。这些与佛教相关的器物可能与唐、宋时期大慈寺范围的变迁有关。
现揭露的唐宋时期遗迹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第6层层表的遗迹,主要包括房址F21、F25、F29、F30和F15,G2、G8、G6,以及与其相配套的L2、L3、L5下的泥土路(因只作了解剖故暂无遗迹号),时代为唐末到北宋。第二阶段主要为第5层层表的遗迹,房址有F2、F10-F14、F16-F24、F26-F28、F31等,与其相配套的道路8条,大小排水道16条;道路以铺砖路L2、L3、L5、L9为主,排水道以继续使用的G2、G8和G9、G11等为主,时代为南宋早中期。
G2始于东端,由东向西流,结合1995年修筑伊藤洋华堂所发现的一条东西向水沟来看,推测在两条水道之间应该有一南北向的大型排水渠,位置大概位于现成都市红星路步行街下。
L2大致呈南北走向(北偏东31°),根据发掘情况,通过对L2多处解剖,发现其经历了3个大的修筑阶段。第一阶段为黏土构筑,土质非常紧密坚硬,可能经过夯打,从出土的瓷片来看当在唐代末期;
第二阶段的路土系用碎瓦渣,瓷片和黏土夯筑,出土的瓷片为北宋到南宋初;
第三阶段,路面用小砖铺砌,砖有可能是修路专门烧制的,与同时期其他建筑或墓葬出土砖的尺寸均不同,从出土的遗物来看,其年代为当宋早中期。
L2第二、三阶段路面宽度比第一阶段略窄,体现了宋代以降街道向长巷制发展的过程。关于第三阶段道路修筑年代的判断同样得到了历史文献的印证。《全蜀艺文志》之《砌街记》:“天下郡国惟江浙甓其道,虽中原无有也。……大、少二城,坤维大都会,市区栉比,衢遂棋布.而苦地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胶漆,既晴,则蹄道辙迹,隐然纵横,颇为往来之患。绍兴十三年,鄱阳张公镇蜀,始命甓之,仅二千余丈。后三十四年,吴郡范公节制四川,为竟其役,鸠工命徒,分职授任,……率一街之首尾立两石以识其广狭,凡十有四街。”
从发现的道路、水沟、房址等建筑来看,遗址所处位置应该为成都城唐宋里坊内的一部分。清光绪五年的成都地图保留有与里坊有关的“大十字”、“小十字”等名称;(明)天启《成都府治图》、(清)光绪二十八年《成都省城内外街道全图》、(清)宣统三年的《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和民国二十二年《成都街市图》均可以较清晰的看到唐宋以降成都里坊布局的残迹。至今,成都市内环路内的东部、北部依然可以隐约见到当年里坊的方块格局,有如棋盘。宿白先生认为唐宋成都城内为十六坊,孙华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并考订了一些里坊的名称和范围,这无疑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利用古今地图的对比(包括街道名称的变迁),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同唐宋时期成都罗城内为十六的里坊的观点,而且江南馆街遗址当为富春坊的一部分(见后文),只是具体的范围与孙华先生推测的稍有差别(主要依据“大十字”、“小十字”的位置)。(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八:“成都富春坊,群娼所聚。”《岁华记丽谱》:“上元节放灯,旧记称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王文才先生根据道叶法善从唐玄宗入蜀,大慈寺有二人画像,大慈寺周围多倡优,娼伎,怀疑富春坊位置与大慈寺相近,此说可从。综上,我们认为江南馆街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与富春坊所在的位置吻合,江南馆街遗址当处于富春坊的东北隅“大区”内。
另外,遗迹出土了与佛教相关的器物则可能与唐、宋时期大慈寺范围的变迁有关。出土器物0现较多贵重的外来瓷器可能也与这一区域较繁华有一定的关系。遗址地处唐、宋时期成都城的东部,这一时期大慈寺区域是有名的庙会和集市地,《方兴胜览》:“成都古蚕虫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月鬻器用者,号本宝市。俱在大慈寺前。”
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是填补成都城市考古空白的重大考古发现,该遗址各类遗迹极其丰富,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成都在唐代经济十分发达,誉称“扬一益二”,成都在宋代诞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无不昭示成都在唐宋时期中国经济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是繁荣发达的唐宋成都城重要的实物见证。此外,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发现纵横交错长达数十余米的铺砖街道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在现代化都市中心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独一无二。
遗址核心区域将被原址保护。核心区域主要包括两条分别长52米和22米的南宋古街,一条晚唐到南宋时期的排水渠长约10米。
保护范围:现保存遗址占地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延5米。
延伸阅读: